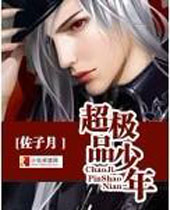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住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谴责这场“可恶的战争”。
“他最好小心点,如果纳粹党官员听见他的牢骚,他可能会被关进福伦森堡!”
“福伦森堡?”我还是头一次听见这个地名。
“福伦森堡是一个集中营,是用来关押所有叛徒、失败主义者和其他人民公敌的地方。”
我虽然属于国防军的编制,但是从来没有领到过军饷,安妮·玛利亚常常掏钱为我买杂志和报纸。有一次,她得到一份旧报纸,她确信我会对此感兴趣的,报上介绍了在布雷斯劳前线的战况。我一直盼望得到关于家乡的消息,我的同学和朋友们正在那里展开英勇的战斗,苏军还没能够攻下这座城市。护士们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我申请在安妮·玛利亚休息那天的通行证,这样我就可以离开医院一天,我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我脸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手臂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好,不过不影响我伸缩胳膊。医生清除掉我肌肉里的绝大部分榴弹碎片。但是我的体温在39摄氏度居高不下,仍然需要大量的药物治疗。
那几次我能连续几天偷偷溜出医院,是因为医院的守卫不在。其实我的室友和夜班护士都知道医院没有夜间卫兵,但是NCO主管后来决定告我一状,于是他们就加派了守卫。我们一早已经计划好在安妮·玛利亚休假那天到马科特雷维兹去玩,那是我祖母的家乡。
虽然我的通行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但是我仍然打算离开医院去玩。一位年纪稍长的病友支持我和安妮·玛利亚,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多享受生活中的乐趣,不过他还是劝我不要没得到批准就和安妮·玛利亚一道离开,“你们可能被拦住接受检查,而且你没有通行证,他们会认为你是叛徒,可以开枪打死你的!”他还说,我们不能在酒店登记入住,也不能租住私人出租的房间。无论是谁,只要收留了我们,都会因为“助人为恶”而被判刑。NCO还暗示说,我可能会被关进集中营。叛徒的最终结局都是被关进集中营,接受死刑处决,我不确信他说的是真有其事还是他杜撰出来的。
安妮·玛利亚和我开始觉得事态严重起来了。
我们没有离开城里,但是走出了学校的范围。在空袭期间,能够走动的人都不会呆在楼里,而是集中到附近一个中学的地窖中。那个地窖不仅是我们的藏身之地,而且还是储存甘蓝的菜窖。这所中学楼上的教室没有被占用,而且门都是开着的。在傍晚的时候,呆在这样的教室里让我们暂时避开了外界的干扰。
“我们爱着彼此,”她说,“我想为你生一个孩子,你很快又要上前线了。”
我们的感情迅速升华了,因为彼此都意识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虽然我的伤势在转好,但是安妮·玛利亚的工作量却增加了很多。
我新近在战场上的经验犹如幻影一般,噩梦一次又一次地侵扰我。被炸掉一张脸的死者的面容不断地在我眼前浮现,那张脸没有鼻子和眼睛,血肉模糊,白骨隐约可见,粘糊糊的液体从伤口慢慢地流出来。
我终于接到重返战场的指令,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个噩耗。安妮·玛利亚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也有想哭的冲动,拼命地忍住不掉眼泪。安妮·玛利亚看到我戴着母亲留给我的戒指,她除下自己手上的戒指,套在我的小指上,那是一枚带有珊瑚石的金戒指。我们发誓终身忠于对方,等战争一结束就再团聚。她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是“你不能丢下我!”但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不得不离开她。
安妮·玛利亚设法调了班,送我去火车站。行李自然不成问题,事实上,我根本没有任何行李。我所有的东西只是身上穿着的制服、一小袋漱洗用具、两个我用来记录写作点滴的笔记本以及一个装着我还在服用药品的药丸盒。安妮·玛利亚为我做了一些三明治,我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网兜里。
然后我们就出发去火车站,一个红十字的护士挽着一个年轻士兵的手走着,士兵的脚还有些跛,两个人都低着头默默地走着。安妮·玛利亚后来打破了沉默,她说:“你一定会回来的!”
“是的,一周以后就回来了。”我回答说,尽管我知道回来也只能呆几个小时。我们最后还是走到了火车站,安妮·玛利亚用手绢抹着眼角。
初恋(3)
我很想再次告诉她,我有多么爱她,但是我害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毕竟我们在一个公众场合,而我还穿着制服。我不得不克制住,“我们能笑着说再见吗?”我问她,捏了捏她的手,她和我都试图挤出一个微笑。
“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了,”她说,“在你还没有走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拥抱在一起。
“坚强一点!”她说完后就转身离开,手在空中挥舞着说再见,但是再没有回过头。
我挤进拥挤的车厢,靠在门边,等待她最后再回头看我一眼,但是她始终没有回头。我不停地挥手说再见,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视线外。我在看到她告别的背影时,突然想到以前学过的一句拉丁谚语,“命运总会找到它的方向”。
破旧的火车摇摇摆摆地从城区驶过,进入郊外后开始慢慢加速。我一直在想着安妮·玛利亚,想着她个性中的温暖和光辉,想着她明亮的眼睛和那头波浪起伏般飘散的褐发,她的动人不仅在于那妙曼的身影,更发自那张秀丽的脸庞。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爱的不同类型,并且发现不同类型的爱有着不同的情感表达法。
我回忆着,从我开始记事起,无论是在家,在学校还是在青年团的少年班,教育要培养的是我们对元首根深蒂固的热爱。我的确做到了热爱元首,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份很虚伪的情感,只不过是一个孩子对一个众人顶礼膜拜的领导形象的崇拜。
再大一些后,我也没有意识到男孩子之间的那种喜爱。我们的理解是,虽然我们只是一群孩子,却培养出了同志般的深厚情谊。我们相信,这种情谊比爱更牢固,结识一个同志意味着找到一个可信赖的人,战友的情谊则是更高层次的同志关系。我从未想过(或有过)爱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权威的形象,而我只能仰望他。我一直都很怕他,根本不记得是否对他有过一丝温情的表现。我想,父亲也不希望我婆婆妈妈的。在希特勒的设想中,下一代的德国士兵应该“冷酷如铁”。
我觉得自己对母亲的爱是一种自觉而长久的强烈情感。
但是现在,狂热的爱情占据了我的身心,一种新的力量点燃了我的灵魂,照亮了我的思想和身体。一个年轻士兵和一个红十字护士之间的爱情是否是混合了朦胧爱意的同志情谊呢?
我最后还是归队了。因为我的归来,部队还举行了庆祝会。库茨克说,他没有料到我会这么成功,所以他强烈要求霍夫的军事司令官为我颁发铁十字勋章。现在,他想在众人面前宣读那段引用的评语——“在受伤以后,他还将其他受伤的伙伴拖到雪沟里隐蔽起来,尽管流了很多的血,他还是冲在前面,是最先攻进村庄的勇士之一。”
台下一片欢呼和鼓掌声,人们在期待着我发表一段演说。我还记得将战场上受伤的战友拖到隐蔽的雪沟,不过,我在好不容易接近村庄边缘时就昏过去了,然后我只记得被装上那架装载着其他伤员和死者的马车。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当初一道上战场的120人的队伍,只有不到40人现在还坐在台下,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撤退或者退让。我们消灭了试图攻占布雷斯劳的苏军,依靠便携式火箭筒击退了64辆敌人的坦克。这是很了不起的战果,要知道这种便携式的火箭筒射程很短,我们只能在离敌人很近的距离开火,这显然不是适合胆小鬼的武器。
复活节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给安妮·玛利亚写了一封信。但是惟一能够写字的纸是带有希特勒青年团徽章(衔着HJ宝石的老鹰和纳粹十字标记)的信笺,不太适合用来写情书。不过,没有关系,那封信的内容洋洋洒洒,充满了我诗般的炽热情感,但是她没有收到这封信。我后来发现,我写给安妮·玛利亚、母亲或者姐妹们的信没有一封寄到她们手中,我也从未收到她们任何一个人写给我的信。据说,盟军的战斗机轰炸了邮车,但是我一直怀疑是否真的如此。
现在,我们将计划投入到法兰克福的战斗中。青年团的领袖亚瑟·阿克斯曼号召我们这群经过战争锤炼的老兵再次投入新的战役,鼓励那些少不更事的同志们。不久,传来了更为让人振奋的消息。
亚瑟·阿克斯曼是纳粹高级将领中较为年轻的一个,但是他迅速地成为了希特勒的心腹。亚瑟·阿克斯曼负责希特勒青年团,他成功地将男童子军运动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政治性和军事性组织。阿克斯曼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胜利或者毁灭,二者只能选择其一。” 他视斯巴达为偶像,经常引用斯巴达的生平故事。就像希特勒一样,阿克斯曼相信,血祭是光荣的,弱肉强食是天理,他本人自诩为战斗英雄。阿克斯曼曾经在东线战场上英勇作战,他的一只手也在战争中被炸掉了,后来安上了一只木头做的假手,而且在这场战争最后的血腥时刻,阿克斯曼更是坚定了决心,要让希特勒青年团为了元首和帝国战斗到最后一刻。希特勒昔日的无数同盟者正在离他远去,阿克斯曼的无比忠诚和誓死精神自然赢得了希特勒的青睐。他很快就成为了希特勒身边核心集团的一分子,这个纳粹的小圈子包括了约瑟夫·戈培尔和马丁·鲍曼。而其余的人,由于不赞同将少年们送上战场,被排除在希特勒核心圈子之外,并且因为怯懦而遭到控告。
初恋(4)
在得知我们将编入党卫军的消息时,我高兴得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父亲一定会为我骄傲的。我们上缴了民兵的军饷册,换领回党卫军的军饷册。我其实不舍得上缴旧的军饷册,因为那上面记录了我的荣誉:铁十字二等功勋章和黑色光荣负伤奖章。我记得,旧的军饷册记录了我在前线和军事列车上负伤的日期、地点和受伤的程度。上级后来同意,给我们检查身体的医生将重新记录有关情况,为此,我可以同时保留两本军饷册,直到医生检查那天为止。我们从未接受过全面医疗检查,自然也就没有刺身标记(党卫军每一个成员都要将血型刺在腋窝下)。
我们接受了一些关于党卫军的基本培训。我们被告知说,党卫军只吸收富有理想主义精神且才智过人的男人,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要求是要勇敢。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党卫军中有大批的人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纳粹民族主义分子。我曾经看过一份党卫军的名单,其中包括了不少自愿加入效忠的外国人,甚至还有法国和英国的分遣队。这让我感受到了国家大家庭般的手足情谊,我们都有共同的世界观,团结在一起反对敌人。培训老师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些照片,而且为我们读了一些目击报告,讲述了“入侵”的苏军施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的种种暴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我们阻挡他们前进的顽强决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培训是让我们更坚信,希特勒是德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人物,我们被挑选加入党卫军的精锐部队,我们和希特勒之间存在一种神圣的相互信任。我们的最高司令官有权要求我们保持最旺盛的战斗力,只要我们谨守神圣的誓言,效忠元首,在必要的时候为了捍卫元首而奉献自己的生命,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胜利。培训中没有问答环节,关于德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我们得到的惟一解释是,除了日本,德国的所有盟友都在决定性战役上失利,他们无法为我们提供军事支援。不过,培训老师向我们保证,局势会转变的。元首已经意识到,他只能依赖自己的部队,依靠久经沙场而且大无畏的党卫军来杀出一条血路。而现在,我们将加入党卫军!
此时,命运的大手再一次改变了我的生活。阿克斯曼出乎意料地检阅我们的队伍,我的铁十字勋章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用那只木头做的右手指着我的光荣负伤奖章说:“你已经重返战场了?”
“是的,长官。”我满腔热忱地脱口而出。
阿克斯曼徘徊了一会儿,他显然在思考一个问题,然后他问到我的战斗经历。当我告诉他,我曾经是一个信差时,阿克斯曼扬起了眉毛,“元首在一战中也曾经做过信差!”
“是的,我知道。”我回答说。
阿克斯曼毫不犹豫地说:“我要求你和另外两个同志后天去柏林,在元首的生日庆祝会上面见元首。”
我突然间哑口无言,太难以置信了!我?我将要去柏林面见阿道夫·希特勒?我就要见到这个我有生以来最敬畏的伟大人物?而且是在这个战争的关键时刻吗?这个伟人正要领导我们扭转战争的局势,赢得最后决定性的胜利。我只有16岁,而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现在,我将接受邀请参加他的生日庆祝会!不久,一家纳粹党的官方新闻机构采访了我和另外几个获得这一殊荣的士兵。我猜想,安妮·玛利亚一定能读到这段消息。
我的母亲、兄弟姐妹也会读到这一消息,还有那些活着的朋友和同学,他们也会看到的。当然,我的父亲也会得知这一消息。阿克斯曼提醒了我,希特勒在一战时曾经做过军队的信差,现在,我这个二战中的信差马上就会见到那个曾经的无名小卒,今日的帝国领袖。
多亏了阿克斯曼,他把我从自以为是的错误方向上拉了回来。不过,去柏林的旅途并不那么令人愉快。我们搭上了一辆军车,没开多久就陷在了难民和撤退军队的人海中。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接近了柏林郊区,一路上,降落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灾难完全呈现在我们年轻而闪亮的眼睛前:弹坑密布的马路像一张麻子脸,整条街的房子坍塌成一片废墟,缭缭烟雾漂浮在城市的上空。一些不屈不挠的人在他们房子的外墙上写下了英勇的口号——“敌人能破坏的只是我们的家园,但他们无法摧毁我们的精神。”但是,撤退的士兵和逃难的人群却揭示了故事的另一面。无数人的脸上刻着我从未见过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