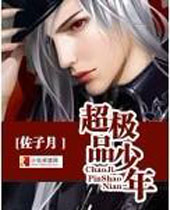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5月2日,当苏军的反间谍机构找到被烧焦的玛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的遗骸后,他们又在党总部的花园内有了惊人的发现。一个旧水箱装着收集起来的腐烂的尸体或肢体,据推测他们是炮轰的牺牲者或在战地医院里死去的病人,他们都被草草地装入水箱。在这些尸体残骸中有一具看上去可能是希特勒的尸体,沃斯元帅证实它是希特勒的尸体,苏联随后立即就把它放在了国会大厦的门廊进行展示(这正是希特勒所担心的事情)。
希特勒的幽灵(3)
接着在5月4号的时候;苏联反间谍机构的一组人员无意中在一个弹坑里发现了像是一双腿的东西。他们把它们挖了出来,发现是一对男女的尸体。当时这些调查者并不知道他们发现的可能是阿道夫和爱娃·希特勒的遗骸,因为他们认为希特勒的尸体躺在党总部的大厅里呢。直到两天后才有人发现了这一点,随后不久在党总部大厅里的被苏军认为是希特勒的那具尸体就被移走了。
很快,在5月8号那天,这些遗骸就被送到了柏林附近的布赫战地医院做初步的尸体鉴定。鉴定指纹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皮肤已经被烧掉了。当时还没有DNA鉴定技术,但是他们找到了颅骨中的牙齿,男性尸体有一副与众不同的齿冠。苏联人把这副齿冠放到了一个旧的雪茄盒里面,并且和其他几副混在了一起。随后他们找到了曾为希特勒的牙医韦戈·布拉希克 (Hugo Blaschke)医生工作过的两个技术人员。弗莱茨·伯特曼(Fritz Buchtmann)设计了这副牙冠,是凯特·霍厄塞曼(Kathe Heusemann)帮助布拉希克医生为希特勒安装的(布拉希克本人逃到了巴伐利亚所以当时没有被抓住)。苏联人让这两位技术人员凭记忆把希特勒牙齿的形状画了出来,随后他们被要求分别单独地从收集在雪茄盒里的牙冠中选出那个正确的。结果是明确的,两位技术人员所画的图与苏联人在总理论坛花园里发现的牙齿完全相同,而且他们两个人都选择了同一副牙冠。至此,元首临终的遗骸不是呆在瓦尔哈拉殿堂里,而是在一个便宜的劣质雪茄烟的烟盒里。
伯特曼和霍厄塞曼不久后就遭到了苏联人的逮捕,许多年以后他们的事情才被披露。据说希特勒、戈培尔夫妇可能还有克雷布斯将军的遗体都被埋在了马格德堡的一个不知名的地点。在第一次验尸1年后,苏联又展开了对希特勒之死的另一次调查,而且还指出了第一次验尸的不足之处。他们总结说:“我们不能只是说:这是希特勒。”后来,不知是他们自己的什么原因,尽管已有大量明显的事实和有根据的证据,苏联当局坚持认为没有希特勒死亡的确切证据。在冷战结束后,苏联档案的解密揭开了另外的一些事实,在这些事实中涉及到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命令克格勃在1970年4月4~5日的晚上掘出并烧毁埋在马格德堡的尸体残骸。他们是希特勒、勃劳恩和戈培尔夫妇的遗骸吗?很可能就是。
但是1945年5月1日从元首地堡中突围的其他人怎么样了呢?他们的遭遇如何?
在我最后一次见过格特鲁德医生之后不久,她就死掉了。她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努力穿过海军大厦外我被击倒的那条大街上。她是被炮弹或迫击炮击中的,她的双腿都被炸掉了。在我被击倒之后,我所在的那一组的其他人员在魏登戴姆大桥遭受到了重大伤亡,于是阿克斯曼决定和从党总部突围的第三组,也就是鲍曼所在的那一组合在一起,它包括斯达姆普菲格、 施瓦格曼和凯姆普卡。鲍曼的皮衣口袋里依然装着希特勒最后遗嘱的原稿,而且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到达石勒苏益格苏尔施泰因州。斯达姆普菲格最有用的东西可能就剩下隐藏起来的毒药了。
集合起来的大量的党卫军、国防军和平民继续试图越过这座桥。过了一会儿,一辆虎式坦克赶来了,还有一门自行突击炮和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当时的计划就是一队平民和士兵在装甲车的带领下,突破在大桥北端桥尾的防坦克障碍。重新组建起来的阿克斯曼和鲍曼所在的小组参加了午夜的第一次突击。他们和许多平民、士兵一起跟在一辆虎式坦克车辙的后面向桥对岸进发。这辆虎式坦克轻而易举地就冲破了大桥北端桥尾的障碍,但是遭到了远处火力的猛烈打击。它被一个随意发射的反坦克手雷击中了,爆炸使得整个小组和跟随这辆坦克的其他人都四处散开了。阿克斯曼受了重伤但是还是尽力使自己站了起来,凯姆普卡被炸得不省人事。
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还有另外3次突破这座大桥的尝试。他们遭受到的打击一次比一次更加激烈,但是这个小组仍然一起沿着去莱特大街车站的铁路线前进,混乱中他们在那个地方失散了。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沿着易万雷登大街往东,朝着斯特蒂弋车站走去。阿克斯曼和其他人向西走去,但是不久就在极端混乱状态下被打散了。阿克斯曼跑进了苏军的前沿阵地,他折回脚步想尽力寻找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在莱特大街车站他偶然发现穿着皮衣仰卧着平躺在那儿的两具尸体,他立即就认出了那是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但是他看不出来他们伤在哪儿。可是形势不容他有进一步的观察,他继续前进。
我后来也发现了那些选择从地铁隧道中逃跑的人的情况好得多。他们在隧道中没有碰到任何苏军士兵,只是碰到了许多想逃避苏军轰炸而把隧道作为地下避难所的德国难民。蒙克的人平安地穿过了威廉姆斯大街安全到达了法兰克福地铁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的是,在地铁站内他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德国平民的,而不是来自于苏军士兵的。他们排成了一列几百米长的纵队前进,一开始时有点急躁,因为虽然火车是停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地铁中的电是否停了。过了一会儿他们确信电已停了。蒙克将军走在前面,每个小组都缓慢地跟着在隧道中穿行。他们来到了腓特烈大街地铁站,在这儿蒙克和其他小组取得了联系,然后他们继续朝施普雷河前进。他们明智地绕开了魏登戴姆大桥而找到了离它300米远的一座人行桥。在河对岸蒙克爬上了一个车库的屋顶看到了魏登戴姆大桥上突发的激战。可能正是这次激战中的弹片把我击倒了,也可能是不久后又发生的一次激战加快了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的灭亡。蒙克的小组尽力保持在一起,而且是惟一平安越过施普雷河的小组。这个小组包括了甘什、拉登胡伯、葛达·克里斯蒂安、特劳德尔·琼格、爱尔斯·克鲁格和康斯坦茨·曼扎利。在成功越过施普雷河后,他们继续向东前进,进入了早已被苏军占领的斯根豪塞大道区。他们藏在一个地下室里,但是不久后就被发现了。反抗已毫无意义,所以他们投降了。男人们都被抓了起来,但女人们都被释放了。蒙克被苏军单独关押了起来,从1949年一直到1955年。他后来被以他参加帝国政府前就发生的战争罪起诉,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证实。
希特勒的幽灵(4)
妇女们很快就和希特勒的厨师分开了。葛达·克里斯蒂安最后一次看见曼扎利是在她们躲避大街上的一次炮弹袭击时,曼扎利冲进了一个地下室,她看到这个厨师消失在一个通道里。当她在后面叫她时,她没有回答。没有人再见过她,经常有传言说曼扎利在深夜的时候逃走了,而且在战后用伪装的身份生活。其他的秘书们都穿上了男人的衣服,以躲避苏联战士的视线,她们最后在一列难民的火车上到达了英国人控制的地区。
奥图·甘什被苏军俘虏后,作为希特勒最后日子的见证人很快被交给了苏联反间谍机构——莫斯科的情报部门。根茨·格雷姆和汉斯·鲍尔也被苏军俘虏了。格雷姆死在了苏联人手中。鲍尔受了重伤,但是在一段时间的囚禁以后,他被释放了,出来讲述了他的经历。元首地堡的卫兵哈里·门格撒森也参加了突围,但是被俘虏了。林奇被苏军俘虏后在1955年回到了德国。凯姆普卡穿过了易北河最后落到了美国人的手里。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几乎都在魏登戴姆大桥上被冲散了。
马丁·鲍曼发生了什么事?难道阿克斯曼1945年5月2日时在易万雷登大街看到的真是他的尸体?就像希特勒一样,鲍曼真正的命运从那时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这两个疑惑都是由于没有找到能够准确辨认出来的尸体而引起的,不过这不是巧合。只是因为每个事件中有根据的证据都被控制起来了,这才使得各种不同的推测在毫无事实根据的基础上滋生蔓延。
鲍曼于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被缺席判处死刑。他的妻子葛达没有按照他的指示把她的10个孩子杀掉,但是在那年她本人死于癌症。后来,传出了鲍曼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修道院里的说法,这种说法声称鲍曼和许多其他的人一样经罗马逃到了南美洲。据报道他曾在智利、巴西和阿根廷现身。最近的一种推测(还未发表)是,他在去南美洲的一队长途航行的潜艇上和几位纳粹高官一起葬身海底的。
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苏联记者发表了据他说是鲍曼的日记,这本日记是在一件被遗弃的皮大衣的口袋里找到的,这件大衣正是在阿克斯曼所说的他偶然看到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尸体的地方被发现的。它的真实性有所争议,但是随后在1972年,在一次日常的建筑作业的过程中,建设者们正是在同一地点挖到了两副人体骨骼。鲍曼和希特勒的牙医是同一个人——韦戈·布拉希克 。法医对牙齿的检查证实这副牙齿是鲍曼的,据猜测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有可能是服毒自杀。1973年4月,一个西德法院正式宣布了鲍曼的死亡。
戈林在5月9日被美国人俘虏了,次年他在纽伦堡受审。他积极地为自己辩护,常常否定对自己的指控。不过他被以4项罪名定罪:密谋侵略、侵略、指挥战争、残害人类。他被判处于1946年10月15日执行绞刑,但是他骗过了绞刑执行人,在绞刑执行前的2个小时,他躲过了看守的注意咬破了剧毒药丸。
希姆莱的死或许是纳粹领导人中最古怪的了。在最后的几天里,他继续在德国北部弗伦斯堡的指挥部里主持全体参谋人员会议。那些来自于徒有其名的部门的头头脑脑们还继续参加,其实这些部门已经不存在了或权力早就没了。汉娜·瑞奇和瑞特·冯·格雷姆离奇地从柏林飞回来以后,已把元首最近对他做出的背叛结论告诉了他。邓尼茨元帅也写信给他说自己放弃帝国元首的头衔。希姆莱仍然无动于衷,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向他的亲信寻求建议,但是令他困惑的是他们没有给他回应。他甚至给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写信,但没有得到回应。在2个星期里希姆莱过着一种毫无意义和友情的生活,最后他身穿一件普遍的陆军战士的军服在一副可笑的眼镜的伪装下离开了自己的房子。这副眼镜是那么的可笑,以至于他到一个英军的检查站时很快被认了出来。一位英国外科医生正要脱下他的衣服给他做身体检查时,他咬破了他嘴里面的毒药丸。
在所有的纳粹高级官员里面,只有一个人对布尔什维克做好了面对战斗的准备,只有一个人没有采取自杀的手段。在战争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亚瑟·阿克斯曼是希特勒的核心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虽然世界对他扭曲的价值观可能会有所评价,但是不能说他对他们不诚实。他从未考虑过要自杀,而且在战斗中从不害怕。阿克斯曼也是惟一一位逃出苏军铁桶般包围的纳粹高官。虽然他在魏登戴姆大桥上受了伤,但他还是设法找到了逃出柏林的路,到达了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他参加了重新组建起来的希特勒青年团,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的6个月里还一直坚持斗争。
阿克斯曼最后还是在英美情报部门精心设置的圈套下被抓到了。他的审问者发现他所做的供词除了在时间方面有点错误以外,在各个细节方面都是准确的。战后我去拜访了他,而且我们还做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承认“犯了错误”,但是他从未说过希特勒的坏话。阿克斯曼于1996年逝世。
后记(1)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是世界史上所犯下的最大、最邪恶的谋杀。我在上帝和这个国家面前是有罪的,我指引过许多年轻人追随希特勒,并认为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但最后他们成了杀害几百万人的刽子手。
——巴尔杜·冯·席腊赫
这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前任领袖巴尔杜·冯·席腊赫所说的话。他曾在1946年5月24日到纽伦堡法庭出席作证。那一天正是我刚过完18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刚刚成年,而且我也开始知道我的童年是如何失去的。巴尔杜·冯·席腊赫是我在战后开始钦佩的人。正是巴尔杜·冯·席腊赫在战前鼓励我去写诗,正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的证言把我引到了和平主义的道路上。在一个天主教的大学教授的帮助下,我开始探究德国在战争刚刚结束后那段时间里的真相。
阿克斯曼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回过头来看。他从未放弃对希特勒的崇拜,我拜访过他两次,而且我们也通了几次信并在电话中也交谈过几次。在他所愿意对我讲的事情中,我感到他对我是真诚的,然而,他总是为自己仍然保持对元首的忠诚而感到骄傲。我完全赞同忠诚,但是忠诚也必须有它的道德规范!促使我寻找非攻击性的解决方案并使仇恨永远消除的,是巴尔杜·冯·席腊赫的认罪,不是亚瑟·阿克斯曼的忠诚表现。
当苏联军医签署了我的释放令以后,他们禁止我到苏军的占领区。这之后不久,我决定尽力而且成功地越过了穆尔德河到达了美军占领区。由于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涉水,我的瘫痪症又复发了。幸运的是一个边境巡逻队救了我,而且把我带到了收容中心的一个医疗机构,在那儿一个美国情报部门的官员审问了我。在那个地方我也看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布亨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解放后命令制作的纪录影片。
我被极大地震动了,我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