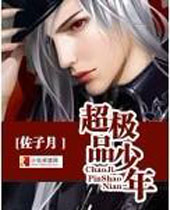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帝国最主要的军事组织以及实行纳粹主义铺平了道路。1936年,希姆莱成为了国家警察部门盖世太保的头目,在国内法律实施方面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恶兆(4)
希姆莱最臭名昭著的行动,就在于让党卫军担负起将纳粹种族主义理论转变到实际行动上的使命,换句话说,就是除掉德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让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种族。他推行《种族法》和《遗传法》,这两项法律都旨在确保优秀种族的生息繁衍,并消灭所有劣等种族。自1933年希姆莱在达豪成立第一个集中营以来,他不断扩大了拘禁到集中营的人种范围。希姆莱声称,集中营所拘禁的“残废人”和“劣等人”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纳粹《种族法》和《遗传法》的英明。
我十分畏惧父亲。当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父亲是家里最热情好客的一个人,但是单独和我在一起时,父亲就变得冷漠无情。他总是希望我无条件地听从他的命令,他不断给我灌输诚实的重要性,但是,我慢慢地发现,父亲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歪曲事实。
我的父亲不是一个高明的生意人,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追逐政治潮流的好处。父亲在备战时期加入了党卫军。根据纳粹政权新的种族教条,党卫军成员为了证明自己的资格,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有“纯正的”血统。种族主义在德国得到了普遍认可,并且很快演变成了民族主义。《纽伦堡法》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地位,只有德国人或者德国血统的人才能享有德国公民地位。第三帝国的目标之一就是鼓励对鲜血与祖国(纳粹口号)的意识。很快,确定自己的出身成为了德国人最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必须持有一份家谱记录卡。每个人都要根据所能获取的全部教堂和市政记录填写这份家谱记录卡。这份记录还必须得到官员签字确认,再盖上纳粹十字记号的印章。但是这套记录家谱的体系完全被滥用了,它的可靠性不取决于记录卡主人的祖先是谁,而是取决于记录卡的主人在纳粹党内认识谁。
我的父亲也下功夫追溯了家族的血统,不幸的是,父亲似乎忘记了一个略有不便的事实:他的母系血统不像他希望的那么“纯正”。家里每个人都知道,祖母是斯拉夫后裔(奇怪的是,慈祥的祖母却是家里北欧日尔曼民族外貌特征最明显的一个人)。我父亲的血统也值得推敲,他看上去并不像日尔曼民族的人,他的面貌特征非常像斯拉夫人,有着亚洲人似的颧骨,胡须不那么浓密,只在上唇上部和下巴上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根胡须。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认为,所有斯拉夫民族都是劣等民族。我的父亲也意识到了,可疑的血统是家庭的耻辱。事实上,我们家的血统比较混杂,甚至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血统。我们家的祖先中曾有人是都柏林的市长(他名叫丹尼尔·维博兰特,1599年出生在爱尔兰,他后来被教皇势力赶下台,于1657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逝世),但是,父亲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当局相信我们家是“纯正的”雅利安人。
我的父亲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他具备过人的“社会大学”才智。父亲非常善于判断形势,并且对新的制度和人物加以利用。父亲加入党卫军不久以后,曾经问过我长大后想做什么人,我回答说“伐木工人”,片刻迟疑后,我又改口说,“或者,当个诗人。”
“诗人?”父亲轻蔑地反问我。他看着我的眼神让我羞愧不已,活像自己是个低级动物。
几天以后,我们家收到一封厚厚的挂号信。父亲告诉我,他为我的将来做了新的打算。他认为,如果我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从精神上和身体上接受严格的训练。父亲事先根本没有知会我,就自作主张地替我报名参加国民政治训练军事组织(NAPOLA)的考试。这个军事组织是一个新近成立的寄宿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的纳粹领导人。学员需要接受传统普鲁士士兵的培训课程,该学校的宗旨就是为希特勒的新帝国选择和培养年轻接班人。该学校的学籍被认为是跻身纳粹最高统治阶级行列的敲门砖。离我们家最近的一所NAPOLA坐落于萨克森和哈勒附近的蓝堡安德萨鲁。那份标志着绝对重要性的挂号信注明了我具备参加考试的资格,并且解释了入学考试的一些规定。事实上,入学考试需要花费整整一周的时间。每个参加考试的申请人都必须接受严格的体能、智力和学业方面的测试。父亲党卫军成员的身份让我在申请中获得优先。
为了这次考试,父亲加强了对我的辅导。晚上,我们一起唱德国国歌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霍斯特·威塞尔是一名纳粹党突击队员,死于柏林的巷战。这首歌歌颂了他的英勇精神,成为了纳粹党的党歌)。当时父亲竭力向我灌输上帝的神威,后来回想起来十分可笑。如果我写错了一个字,唱错了一个音符,父亲就会咆哮着斥责我。父亲为我设计了一些考试论文题目,其中一个是:“我为什么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我写了洋洋洒洒的大篇文章,描述了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和茂密的森林。父亲对此大为光火,他将这篇文章撕成了碎片,然后逐字逐句地教我重新写了一篇文章:我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因为我成长在希特勒领导的时代,伟大的希特勒很快将带领德国成为世界强国。我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因为我是日尔曼民族的后裔,我拥有纯正的雅利安人血统。这篇文章简直就是他自己在自吹自擂,我暗暗地想,这样算是欺骗吗?
恶兆(5)
第二天,父亲送我去车站。在开车送我去车站的途中,他又教育了我一番。
“机灵点!”
“是的,爸爸。”
“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要努力啊!”
“我会的,爸爸。”
“记住,你是我的儿子,你一定要成功!”
“嗯。”
“这是你一生才能遇上一次的大好机会。”
“是的,我明白。”
父亲不断地提醒我,是希特勒一手促成了NAPOLA的成立。如果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我这次出人头地的机会。父亲让我牢牢记住这一点,用行动去证明。在火车站,父亲说,“再见。”
“再见。”我回答道。
父亲和我握了握手,然后他伸手从衣兜里掏出个小盒子,“祝你走运!”父亲对我说。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转身离开,开着车慢慢远去。
我打开了小盒子,让我万分震惊的是,盒子里装着一块崭新的手表——这是我少年时代收到的最贵重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不是母亲送给我的,也不是祖父母送给我的,而是父亲送给我的,是那个总是对我失望至极的父亲送给我的。一时间,我既高兴又困惑,我是走到了人生的转折点吗?我是否应该从此改变对父亲的看法呢?
我立刻把表戴在手上,反反复复地欣赏起来。和我同一个火车车厢的人都注意到了这块表,“是我父亲送给我的。”我解释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
我在NAPOLA接受了一周的密集考试和教育,自我感觉还不错。
等待考试结果的时间是那么漫长。当考试结果通知书邮到我们家时,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父亲迫不及待地撕开了信封,仔仔细细地阅读起来。从他脸上的表情,我都可以看出考试的结果不理想。父亲好像遭到当头一棒,在迟疑了一会儿后,父亲拿起电话拨了学校校长的号码,他在电话上称呼校长为“党卫军中尉先生”。我在门口等候着,浑身发抖。父亲一言不发,沉默地听着电话那头校长的谈话。似乎只有校长一个人在讲话,父亲非常安静,但是明显地十分沮丧。最后,他恭恭敬敬地说道,“向希特勒致敬。”然后放下了电话。他没有对我说一个字,走进了隔壁房间,母亲在隔壁等着,我能听见他沮丧地对母亲说,“我们的儿子是个软蛋。”他的希望跌到了谷底。
我自己也深受打击,而且迫切地想知道自己在哪方面没有考好。我问父亲,校长都告诉他什么情况。从表面上看,我缺乏精神上和体力上的持久力。(母亲后来告诉我,校长的原话是,我太弱不禁风,而且太容易生病了。我或许无法承受作为纳粹领导接班人必须接受的精神上和体力上的高度压力。如果和后来的实际情况相比,这个评语实在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不过,校长安慰父亲说,我或许可以就读新成立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他们接收年满12岁的孩子。父亲这次并没有打我,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臂,一把将那块他送给我的表摘了下来。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了,我不配拥有这么昂贵的礼物。
第二章 战争
战争(1)
不久,我们家就搬到了布雷斯劳,父亲则开始在德意志广播电台工作。这家电台是约瑟夫·戈培尔宣传网络的一部分,能够为德意志广播电台工作是很光荣的一件事。父亲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参加了纳粹党,自然,父亲是不会承认这种关联性的。显然,父亲根本不具备为电台工作的资质,也没有受过相关的培训,他在电台的职责就是做监察员,密切关注电台播出的内容,确保电台的宣传与纳粹党的纲领高度一致并且留意颠覆分子的行动,诸如此类。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住在城市里。布雷斯劳当时是下西里西亚的省府城市,它斜跨奥德河两岸。布雷斯劳的老城区还保留了许多狭窄的街道和旧时的教堂,有颇为浓重的中世纪城市风格。内城区的所有街道最后都汇集到市场广场,广场上坐落着哥特建筑风格的市政大厅,市政大厅最早于16世纪开始修建,从中世纪以来很多西里西亚的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圣诞节的时候,街道被皑皑白雪覆盖,整个城市显得非常美丽。不过,我们在这次搬家中无法带上家里的狗,我时常地会想念它们。很快,我就腻味了这种住在公寓楼二层的生活,而且附近也没有去处,只有一小块公共场地可供孩子们玩耍。
搬家后父亲经常早出晚归地忙工作,我不常能看到他,这是这次搬家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了。父亲现在挣钱比以前多了许多,但是他并没有多给母亲家用的钱。他把大部分薪水都用来购买漂亮的外套、和纳粹党内的朋友下餐馆,或者去参加周末狩猎活动。最让我母亲生气的是,父亲偶尔还会带一帮朋友回家吃饭。母亲往往会在开饭前1个小时左右接到父亲的通知电话,他要带客人回家吃饭,母亲得在他们到家前准备好一桌饭菜。母亲会抱怨说她没有足够的买菜钱,但是父亲根本不予理会。
常常来我们家吃饭的有弗里茨·瑙约克斯(Fritz Naujocks),这个人后来因为捏造进攻波兰的虚假理由而声名扫地(瑙约克斯将一群集中营关押的犯人穿上了波兰军队制服,上演了一出对格利维策广播电台的“进攻”。这为希特勒制造了借口,指责波兰挑起敌对行动)。父亲也开始接触卡尔·汉克(Karl Hanke),汉克是一名热情的纳粹分子,他当时担任着西里西亚纳粹党的党主席,曾经与宣传部长漂亮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有一段私情。当然,父亲从没有对我提过这件事,但是我经常能在起居室听到他对亲信的人谈起纳粹党新近的流言蜚语。
父亲对这份新工作很上心,一周总有那么一两次他会穿上崭新的黑制服和光可鉴人的大皮靴,兴冲冲地去上班。不过,公寓的管理员却认为父亲像一头蠢驴。公寓的管理员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有一次,父亲又穿上黑色党卫军的制服在她面前炫耀,父亲还对她抱怨公寓的一些问题。然后,父亲就离开了,恰好我还呆在大堂里,听到管理员说:“制服挺漂亮的,可惜连一枚军章都没有。”在纳粹德国时期,军章是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在战争时期,只要参与运动就能获得军章,连受伤的人都能得到奖励的军章。一个人受伤的次数越多,得到的奖章越多,就越光荣。事实上,父亲甚至都没有得过最起码的“运动参与奖章”,因为他连游泳都没有学会,而很多十几岁的小孩都能获得这枚奖章。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才意识到父亲在外面的形象有多么可怜。不过,公寓的管理员也是差不多可怜的一个人,她也没有什么好吹嘘的。她的丈夫是这幢公寓楼的“监督员”(一个地区负责向纳粹党通风报信的人),主要的工作就是监督大楼里是否有人造反和捣乱。他们家为此可以得到额外的配给量。但是,这个男人是个酒鬼,经常喝醉了和人发生口角。最讽刺的是,因为他就是这幢楼的监督员,没有人能够去告他的密,哪怕是党卫军的人也不能告他!
1938年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就是在这一年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那是在世纪大厅,大厅里挤满了希望得到希特勒接见的人,等候的人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记不清具体是怎么见到希特勒的了,或许还是和父亲在德意志广播电台的那份工作有一点关系——他们肯定要广播这次活动。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出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种狂热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离希特勒很远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种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欢呼着。
在那个时代,希特勒的成就让绝大多数德国人感到振奋,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慈善的独裁者和天才的形象。当时的经济处在繁荣阶段,几乎不存在失业的现象,每个人似乎都能得到一份工作。汽车高速公路的网络不断扩大,大众汽车价格低廉,受到人们的好评。希特勒许下的一切承诺都逐一实现了。
1938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班。德国的小孩只要满了10周岁,都可以加入青年团的少年班。加入仪式在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那天举行。现在,我获得了为社会工作的光荣角色,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荣誉。我们班共有48个人,每周三的晚上在当地学校集会,如果有特殊活动,也会在周末集会,我们还一道去郊外露营。希特勒青年团的一条原则是,青年人才是青年团的领袖,班上的成员也因此结下了同志般的友谊。田径比赛、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