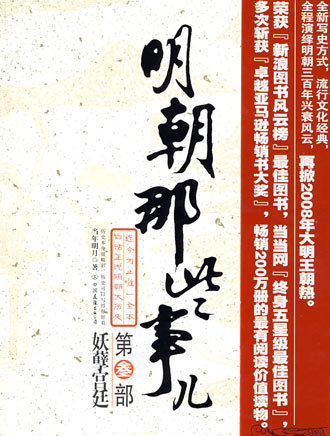成都--那些走远的人-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回信。一通车我就尽快回家接你们。准备好。
看完信,我笑起来,大声说我爸这家伙居然骗人。
我妈说,别管你爸叫家伙,太不礼貌。
我说,行呀,叫他老家伙吧。
我妈说,叫老家伙更不好听,还是叫家伙吧。
我说,管他呢,反正我才不上当呢。
我妈说,你不上当,那咋办呢?
我说,你就照我爸说的办呗。
我妈说,那不行,不能听他的。我马上给你爸爸写信,你不能留在京剧团老抢人,得一起去西昌。
我回到基地,梦想着高原上我爸说的那条铁路,常常为他说一块人和一条鸡,也为即将搬家到山里去兴奋不已。晚上无事可做,会有一些人在山野上和宿舍里练功,只不过练的是笑功和眼功。每当那时候,就能听见四面八方传来的各种笑声。一听就能明白的是大笑、狂笑、嬉笑、冷笑、谈笑、说笑、欢笑、奸笑、狞笑、惨笑和傻笑。难听明白的是阴笑、讪笑、赔笑、痴笑、苦笑、干笑、憨笑和失笑。最难辩别的是有些人在窃窃发笑、暗自发笑、似笑非笑,还有鬼笑。我去串门,看见一些师兄弟和师姐妹在练笑眼、定眼、狠眼、怒眼、白眼、瞪眼、泪眼、冷眼,还有醒眼、斜眼、贼眼什么的,练得最多的是京剧称为斗眼的对对眼。我去找小校花,在她屋里站了好一会,她不叫我坐也不跟我说话。
我不想再抢人了。我忽然对她说。
她侧身对着我,脸也不转一下。团里要派她去北京学戏,重点培养。
剧团领导要我跟你结婚,没门。我又说。
她仍不理我,只顾坐在窗前对着一面小圆镜发呆,准是又在想她爸爸了。看着她那副病兮兮的样子,我一声不响溜了出来。我才不去想她那个早已死掉的户籍民警爸爸,我只想我爸和他的高原。算起来,他独自进深山,已经有些年月了。
然而,铁路通车遥遥无期。
周末,我从剧团回来,大奶来到我家,我以为他又要来下棋,不想却是来告别的。他说他们一家人很快要跟着老包进山,去一个名叫普雄的地方。他说成昆铁路已经修到了那里,他父亲要留在那里工作。我说你不上学啦?他说普雄有学校,是专为铁路子弟修的。
我说,你妈也一起去?
他不情愿地点点头。
早就听说大奶的母亲一边脸上少了一大块肉,从不出门,怕被人看见。
当我再次从剧团回到家里,大奶一家人已经远去。大奶的普雄没有我爸的西昌远,我妈在日夜准备,要把小半辈子积攒下的所有东西统统带走。
离别的日子好像越来越近,我妈提出要带我进城再吃一次回锅肉,我想了想,没敢去。
终于有一天,我爸和大哥从山里归来了,我妈带着我们四个孩子老早就去了火车站。一列空空荡荡的火车缓缓开进站的时候,我们排成一行屏住呼吸。我看见车轮一停住,车门一打开,走下来了疲惫的父亲,又走下来了已经在大山里成为一名铁路工人的大哥。大哥一别多年,穿一身铁路工装,背一个鼓囊囊的帆布工包,一脸的肃穆与庄严,带来一种遥远山野的苍茫和一种遥远岁月的悲凉。
我们一接过他的工包就急着打开找吃的,有生第一次看见了石榴和核桃。
大山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别的什么吧?
一回到家,我爸和大哥就说,那条四十万人修筑的铁路于1970年7月1日在礼州接轨,在西昌火车站举行了十万人参加的通车典礼,北京来的吴法宪剪的彩。通车典礼那天,西昌火车站上人山人海,大汽球拖着老长的标语悬挂在半空中,一对披红挂彩的旅客列车从南北两个方向开来,头冲着头停在车站上,而在车站背后的一座山坡上,由万人举着红黄两色花朵,组成了黄底上的五个大红字:毛主席万岁!
几天后,一家人拉着两辆借来的架架车,把我妈早已准备好的东西拉往火车站托运。全部东西不过是两个原色大樟木箱、一个绛红色樟木箱、一张麻黄浅色书桌、一个吃饭的圆桌、一些炊具和一些衣服被褥打成的大包裹,以及许多烧火做饭用的木柴。途中,旧圆桌掉下车来,差点把我妈我爸心疼死。
告别成都那天,我妈挨家挨户跟街坊四邻道别。然后,我们全家人走出那幢红砖楼房,楼外站着一些送行的街坊四邻,孔立在自家窗外望着我。这次他没像以前那样玩鸡鸡,也没傻笑,脸上一片茫然。他忽然对我大声说:
我们家过不久要去乌斯河,就是成昆线最险的地方,然后也要搬到西昌去。
那一刻,我发现他跟我差不多大,只是不知是否已经上学念书。
孔又说,我爸爸在乌斯河打了几年山洞,用风枪打!
我忽然想起几年来一直没见过他父亲。
离别成都,连一丁点依念也没有。小校花去北京学戏还没回来,无法向她道别。去火车站的路上,我想着孔的样子,觉得他常常拿出来玩的的鸡鸡像一个惊叹号,还感觉出他很想有朝一日跟我一块玩。
第二部
第二十五章 拿出来玩的鸡鸡像惊叹号
在龙泉山顶的夜里,我想着我妈爬在饭桌上给我爸写信的情景,心想在剧团的日子,没完没了地练腿练腰练嗓子,成天都是人家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真没意思, 再也不想呆下去了。
我隔三差五爬汽车往家里跑,发觉我爸写信的时间越往后,写的却是越往前的事。我们一家人都在盼他传来铁路通车的消息,可他在最后几封信里却说起了成昆铁路勘测设计上的事,把人看得莫名其妙。他在信上说,到现在我才相信了,为了修成昆铁路,从1952年起就有好些中国最好的铁路专家带领一支支队伍翻山越岭开始了勘测,还有好些科研人员爬山涉水时死于悬崖激流和山里土匪的刀枪。苏修铁路专家却说,中国人要修成昆线简直是疯了!这些事,跟老包那天晚上在咱们家里讲的一样一样。
我爸写的那些事,的确是老包在武斗之夜说过的,只是当时我没怎么注意听。我不明白我爸为什么要在遥远的大山里津津有味地老是写这些东西,也不清楚他在每封信里夹带着寄来不少他们那边的简报资料,是何意图。
我跟我妈说,我爸写的不是死人就是导弹,老这样装神弄鬼,是不是想吓唬咱们?
我妈说,不会吧?是怪吓人的,啊?
我说,我爸在山里做啥事呢?
我妈说,发电报,还带了一大群女特务。
我说,你说什么?女特务?
我妈说,不,女徒弟。
我说,他咋还不叫咱们去西昌呢?
我妈说,快了吧。没准下封信就会叫咱们去。
二哥初中没毕业,要和铁中的九百多同学去远方的川黔线。他们要先去重庆小南海川黔线上第一个火车站珞璜,修车站、砌边墙、修山洞,然后去成昆线上参加大会战。二哥他们离别成都那天,通往火车站的马路上,灯火通亮照着冬天的夜晚,送行的人流像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二哥太小,背不了被包,我在前面背,背包底擦着路面,走一步打一下腿,二哥和四弟就一人抓一个角,把背包提起来推着我往前走。五弟和六弟抱脸盆和杂物走在一边,我妈则提着行包走在最后。我记得,二哥他们坐的火车,跟大哥他们去的地方是一个方向,听大人说要走一段才会分道扬镳。
我后来看出来,我爸寄来的很多信,我肯定有些没看到,而看到的都是我妈主动叫我看的。我估计有些信多半谈了不少自家的事,不然我爸不会吃饱了撑的老写人家的事。当有一天我爸的又一封信浮出水面时,要不是我眼尖手快,可能就永远也看不成了。当时,我跨进家门,一眼看见我妈正在藏一封信。
我说,妈,你藏啥呢?
她说,藏信。
我说,干嘛要藏?
她说,不让你看。
我说,我还不想看呢。
她说,那不行,得叫你看。
我说,我不看。
她说,不看咋行,快来看看吧。
我接过信,信上是这个样子____
最高指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孩子妈,成昆铁路大会战又掀起高潮了!到眼下,除去几十万块人正在拼命抢修铁路,还有上万块人在松林地区也大干起来了。因为人太多,集市上根本买不到吃的和用的东西,农民挑的菜一到路边上马上就会被抢光。星期天,我翻山越岭去地陷湖钓鱼,遇上一块人,那块人硬拉着我去他家里坐客,还杀了一条鸡。我跟那块人说,等铁路一修通,我们全家人就可以团聚啦。
孩子妈,最主要的是,我写的前几封信,你都照我说的给三儿子看了吧?要是还没看,马上找出来叫他全都看看。但这封信是专写给你一人的,可别叫老三那个贼小子瞅见了,不然准坏事。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别让老三离开京剧团,就呆在剧团抢人吧。他要是离开京剧团,以后就得下乡当知青,在剧团里虽说只能演个抢人的角色,但是吃穿有公家管,那就算参加了工作,这多好呀。你让他反复看看我写的那些信,让他明白我们这里要多可怕就多可怕,他要是还像你来信说的那样,老想着到我这儿来,你就多给他说说塌方!泥石流!导弹!爆炸!问问他想到山里来找死吗?我寻思这样一来,准把他猴小三吓个半死。好了,就写到此,你快回信。一通车我就尽快回家接你们。准备好。
看完信,我笑起来,大声说我爸这家伙居然骗人。
我妈说,别管你爸叫家伙,太不礼貌。
我说,行呀,叫他老家伙吧。
我妈说,叫老家伙更不好听,还是叫家伙吧。
我说,管他呢,反正我才不上当呢。
我妈说,你不上当,那咋办呢?
我说,你就照我爸说的办呗。
我妈说,那不行,不能听他的。我马上给你爸爸写信,你不能留在京剧团老抢人,得一起去西昌。
我回到基地,梦想着高原上我爸说的那条铁路,常常为他说一块人和一条鸡,也为即将搬家到山里去兴奋不已。晚上无事可做,会有一些人在山野上和宿舍里练功,只不过练的是笑功和眼功。每当那时候,就能听见四面八方传来的各种笑声。一听就能明白的是大笑、狂笑、嬉笑、冷笑、谈笑、说笑、欢笑、奸笑、狞笑、惨笑和傻笑。难听明白的是阴笑、讪笑、赔笑、痴笑、苦笑、干笑、憨笑和失笑。最难辩别的是有些人在窃窃发笑、暗自发笑、似笑非笑,还有鬼笑。我去串门,看见一些师兄弟和师姐妹在练笑眼、定眼、狠眼、怒眼、白眼、瞪眼、泪眼、冷眼,还有醒眼、斜眼、贼眼什么的,练得最多的是京剧称为斗眼的对对眼。我去找小校花,在她屋里站了好一会,她不叫我坐也不跟我说话。
我不想再抢人了。我忽然对她说。
她侧身对着我,脸也不转一下。团里要派她去北京学戏,重点培养。
剧团领导要我跟你结婚,没门。我又说。
她仍不理我,只顾坐在窗前对着一面小圆镜发呆,准是又在想她爸爸了。看着她那副病兮兮的样子,我一声不响溜了出来。我才不去想她那个早已死掉的户籍民警爸爸,我只想我爸和他的高原。算起来,他独自进深山,已经有些年月了。
然而,铁路通车遥遥无期。
周末,我从剧团回来,大奶来到我家,我以为他又要来下棋,不想却是来告别的。他说他们一家人很快要跟着老包进山,去一个名叫普雄的地方。他说成昆铁路已经修到了那里,他父亲要留在那里工作。我说你不上学啦?他说普雄有学校,是专为铁路子弟修的。
我说,你妈也一起去?
他不情愿地点点头。
早就听说大奶的母亲一边脸上少了一大块肉,从不出门,怕被人看见。
当我再次从剧团回到家里,大奶一家人已经远去。大奶的普雄没有我爸的西昌远,我妈在日夜准备,要把小半辈子积攒下的所有东西统统带走。
离别的日子好像越来越近,我妈提出要带我进城再吃一次回锅肉,我想了想,没敢去。
终于有一天,我爸和大哥从山里归来了,我妈带着我们四个孩子老早就去了火车站。一列空空荡荡的火车缓缓开进站的时候,我们排成一行屏住呼吸。我看见车轮一停住,车门一打开,走下来了疲惫的父亲,又走下来了已经在大山里成为一名铁路工人的大哥。大哥一别多年,穿一身铁路工装,背一个鼓囊囊的帆布工包,一脸的肃穆与庄严,带来一种遥远山野的苍茫和一种遥远岁月的悲凉。
我们一接过他的工包就急着打开找吃的,有生第一次看见了石榴和核桃。
大山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别的什么吧?
一回到家,我爸和大哥就说,那条四十万人修筑的铁路于1970年7月1日在礼州接轨,在西昌火车站举行了十万人参加的通车典礼,北京来的吴法宪剪的彩。通车典礼那天,西昌火车站上人山人海,大汽球拖着老长的标语悬挂在半空中,一对披红挂彩的旅客列车从南北两个方向开来,头冲着头停在车站上,而在车站背后的一座山坡上,由万人举着红黄两色花朵,组成了黄底上的五个大红字:毛主席万岁!
几天后,一家人拉着两辆借来的架架车,把我妈早已准备好的东西拉往火车站托运。全部东西不过是两个原色大樟木箱、一个绛红色樟木箱、一张麻黄浅色书桌、一个吃饭的圆桌、一些炊具和一些衣服被褥打成的大包裹,以及许多烧火做饭用的木柴。途中,旧圆桌掉下车来,差点把我妈我爸心疼死。
告别成都那天,我妈挨家挨户跟街坊四邻道别。然后,我们全家人走出那幢红砖楼房,楼外站着一些送行的街坊四邻,孔立在自家窗外望着我。这次他没像以前那样玩鸡鸡,也没傻笑,脸上一片茫然。他忽然对我大声说:
我们家过不久要去乌斯河,就是成昆线最险的地方,然后也要搬到西昌去。
那一刻,我发现他跟我差不多大,只是不知是否已经上学念书。
孔又说,我爸爸在乌斯河打了几年山洞,用风枪打!
我忽然想起几年来一直没见过他父亲。
离别成都,连一丁点依念也没有。小校花去北京学戏还没回来,无法向她道别。去火车站的路上,我想着孔的样子,觉得他常常拿出来玩的的鸡鸡像一个惊叹号,还感觉出他很想有朝一日跟我一块玩。
第一章 高原上的西昌我的第二故乡
第一章 高原上的西昌我的第二故乡
成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