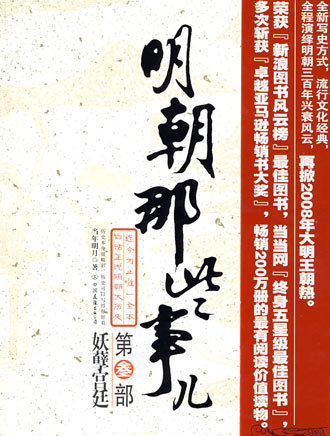成都--那些走远的人-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不满地看看我,不好再阻拦,叫我下午回医院替换他。
赶到学校时,校花她们一大群人已经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排练开了。我其实没事可做,找个角落坐下来,管事的老师在一旁走来走去只当没看见我。实在说,我跟校花的合作节目以及我俩各自的京剧清唱都不需要排练,只是她除了要继续充当被我抢的角色,还兼演了多个歌舞,有藏族舞蹈《洗衣歌》什么的。我知道自己饿着肚子辛辛苦苦地来学校,只不过是为了看看校花,而真的一见到她时心里却有些怕。
下午,师傅上班去了,我在医院帮师傅看护老古的老婆。有一阵门外响起纷乱的说话声,接着一群人从病房门口走过,领头的人是大奶的父亲老包,他无意间发现我,先是一惊,接着拐进病房,小声问我家里人谁病了。我把老古钓鱼被电死和他老婆夜里在坟坡遇狼以及师傅和我们父子相救的事简单说了一下,他一听完就俯下身去跟床上老古的老婆嘘寒问暖:
这位女同志,好些了吗?哪个单位的?
老古的老婆边轻声回答,边费力地想要坐起上身,老包忙伸出两手去扶,等她挺着老高的乳房在床头靠好后,老包对她说:
看你这位女同志,在深沟里那样偏僻的地方上班,出出进进可得当心,进沟里上坟更不能单独去。如今咱们马道的狼,早被开山放炮和来来往往的火车治得温顺多了,当年我们勘测成昆线的时候,不说在山里遇上的豹子、老虎、野猪,光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狼,那才够得上野狼。那些狼甚至包围我们的汽车,开枪打都不怕,有一次还把我家那位――当时,她勘测队的地质是工程师――差点要了命。
说完,他直起身,对身边的大夫嘱咐几句,要求精心治疗调养,最后走出病房离去。等到病房里没别的医护人员时,老古的老婆仍跟先前一样,不怎么理睬我,只是表现在脸上的态度要比那天当众扑打我时要好得多。
三爷,那个人是谁?老古的老婆隔不久问我。
他是分局领导,姓包,我家小时候的邻居,是我爸的老朋友。我说。
他说他家里那位差点被狼要了命,是不是指他爱人?她说。
是他爱人,我小时候见过几次,但从没看清楚过,她一出门就戴个大口罩。我说。
你师傅是个好人,那天我骂他,气昏头了。她说。
你也骂了我和我爸,没事,你只管骂就行了。我说。
我不再骂了。她说。
刚才你听见了,以后你再去深沟里,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我说。
我只有自己一个人。她说。
要是再去,你一定要找其他人陪你。不行的话,只管来喊我一声。我说。
你一个小娃娃,喊你陪我?她说。
小?你还信不过我的功夫?陪你去给老古大哥上坟,我也愿意。我说。
哼,我不要你陪我,我要你赔我娃娃。她说。
我又没把你的娃娃弄丢,你本来也没得娃娃,我咋个赔你?我说。
反正要赔。她说。
病床上老古的老婆依然是美丽的,看着她,我禁不住想起校花。似乎血管里堵了些东西,不弄出来就心发慌,从那天起,我开始写诗。三天后,老古的老婆出院了,是老包派来的一辆小汽车把她接回家的。
第二十章 从西昌化妆逃走的国军参谋长
第二十章 从西昌化妆逃走的国军参谋长
又一个新学年开始。
有人在学校主楼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学校图书室的阴影,责问学校图书室为何借不到《毛泽东选集》!不到半天时间,全校上千名师生都站在那堵墙下瞪大眼睛看了大字报。那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大字报,光是那么一个可怕的大标题,就能吓得人心直跳。中午放学前,学校在大字报旁边贴出了另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我们的罪过》。没等下午放学,学校就从城里运回一马车《毛选》搬进了图书室。事后不久大奶告诉我,他在暑假中一个风高夜黑的礼拜天破门砸窗,洗窃了图书室里的图书,用马车拉了一整车,到家一看全是《毛选》,气得不得了,才糊了大字报。
那时候,诗这个东西把我折腾坏了。我的大多数时间花在了从商店里买到的一本本工农兵诗集和散文集上。整个马道只有一个国营商店,两层的红砖楼,二楼住人,底层卖零七碎八的各种小东西。我要买的书放在香烟玻璃柜里,头几次我往柜前一站,看上两眼就叫喊买东西,同时手往玻璃里面一指。几个在旁边聊天的女售货员中就有一个冲我喊,票呢?烟票呢?7号票!
我说,买《放歌集》。
一个女售货员这才冲着旁边叫喊几声,接着,一个岁数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才从角落里走过来,把书扔给我。
另一次我看见玻璃柜台里有新来的诗集《车老板的歌》,刚要开口叫服务员,那个男孩自己主动走了过来。
他二话不说把诗集取出来,双手递给我。我被这份热情弄得很感动,抬头看着他,这一看不要紧,小时候给老保守送饭和在府河边上抢走我鱼竿的那个小男孩的样子在我脑海里一晃。
我说,你是从成都来的?
他点了点头。
我说,几年前的一个早上,你在成都西北河边上抢过一个小学生的鱼竿,记得不?
他盯着我没答话,两眼一眨也不眨。
我说,你爸呢?
他把脸转向一边,不理我。
我说,以后来了新诗集,你帮我留一本好不好?
他马上转回脸,使劲点头。
我每天读书那些书,我认为再读几本,差不多就破万卷了。后来,班上几乎人人都知道我在写诗,不少人也跟着写起来。科任老师大多是知青招工来的,可能觉得满教室都是诗人,一上课只好面带愧色,眼看着我们刚出笼的诗歌条子满教室传来传去。半期考试时,我在英语白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把普通话说得十分标准的女英语老师气得直抹眼泪。她在办公室当着我抽泣说,我真是倒霉呀,怎么刚教两天书就遇上你这么个大文豪呀。
一个偶然机会,我看见班上同学在传看一个本子,要过来一看,上面是大奶写的密密麻麻诗,再一看,发现他跟我写的完全不一样,可以说好得多。
约好以后,礼拜天翻过山岭,我来到地陷湖边。
大奶的家在湖边山脚下面,是一栋处在绿色树木中的独户平房,四面屋檐下有宽回廊。好像时隔不久,他的父亲老包显得越来越有派头了,一头花发往后梳,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智者的光亮,从头到脚散发出学问的气息。老包要我带话问我爸我妈好,然后被一辆小汽车接走。大奶带我在一间间房子里转了转,然后在他的屋子里坐下。我问他母亲呢?他支吾了一下,没直接回答。一会,他从枕头下取出一本硬壳笔记本递到我手上,我看见上面写满了诗,写得的确比我好,令人刮目相待。他看出这一点,高兴之下又取出一本旧书让我看,是《普希金文集》中的一本,全是诗。
我翻了翻说,这也叫诗?哪是什么诗呀!
他吓了一跳,不信任地看着我。见我一脸凶相,接过诗集小声说,这可能是诗,只是写得比咱们差罢了。
我又要过诗集翻了翻,用手指着说,你看看这首____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愤怒,不顺心时要克制自己,相信那快乐之日就会来到。这个姓普的写的啥呀,人家车老板写的我背给你听:那个长鞭儿耶,那个一呀甩哎,啪啪地响哎,唉唉嗨依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唉嗨哟。还有,还有好长,全国的人都知道,写得多好!
他不住点头说,就是就是,普希金不行,车老板还可以。
回家后,我耳边一直回响着他的这句话,觉得只有这句话还说得够意思。
高原的太阳落山很久了,还在天边放射着万丈光芒。
夜里,我爸躺在小屋里的靠椅上睡着了,我轻轻走进去,正想帮他关掉旁边小方凳上的收音机,不巧听见一个女人在电流杂音中妖里妖气地说西昌解放的事。女人说,1950年3月,共军共13个团从昆明和成都分两路主力南北夹击西昌,3月26日晚,共军挺进西昌之际,国军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携从员飞往海南岛转台北,参谋长罗列率部阻击,退至喜德甘相营与共军激战,至3月30日,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罗列施金蝉脱壳计,骗过战场验尸军官,遂以被击毙见报,新华社播发了战报。蒋总统在台获悉,以总统令宣布罗列为烈士,入祀台北园山昭忠祠。想不到,罗列化妆逃出大凉山,1952年辗转回到台湾,立即被蒋总统任命为国防部厅长,继升副总参谋长、第一军团司令,1954年升任陆军总司令、二级上将,1961年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女人说完后,收音机刚传出一个老年男人的讲话声,我爸忽然睁开眼睛,一把关了收音机。
你小子收听敌台,想找死啊!他惊恐万状地盯着我,一副要揍人的架势。
是你在收敌台,还怪我!我站起来叫道。
我在睡觉,还敢顶嘴!他说,样子有些气急败坏。
你说在睡觉,那怎么知道我在听敌台?我后退几步说。
他咬牙切齿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接着看一眼收音机,最后颓然坐下。
你呀,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连敌台也敢听。他说,口气变得有些无可奈何。
你咋知道是敌台,你说呀!我揪着他刚才的话不放。
我?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他有气无力地往后一靠,像是在对我说话,又像在喃喃自语。
你知道是敌台?我追着说。
是啊,那个罗列的事我早就听过八遍了。他低声说,显得越发垂头丧气。
原来收音机早就播过罗列的事?我说。
谁说不是呢,几年前就在播,刚才一听见那个男人的声音,我就知道是老罗。我爸说,声音更小了。
我爸管人家罗列叫老罗,口气像在说一个老朋友,真有点神经病。
电台专访老罗,老罗讲了从西昌逃走的好些事。我爸补充说,上眼皮往下掉。
我只是碰巧听见的。他又补充了一句,两眼已快闭上。
看着我爸那种梦颠颠的样子,我转身想离开,好让他一个人睡一会。但刚要拉开门,他在背后叫了一声先别走,我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说说,咱们这个地方怎么会出那种事呢?他睡眼惺忪地盯着我说。
什么事?我说。
就是那个老罗,他是怎么逃走的呢?从深山老林跑的?他两眼迷糊起来。
我咋知道呢,这个可以问问考古学家。我说。
还是你脑子好使。他说。
第二十一章 盼望火车早一天站起来跑
第二十一章 盼望火车早一天站起来跑
然而,考古学家一直没再来我家。我一次又一次去马道商店看看有没有来新诗集,发现很长时间没再见到那个男孩,一问才知他调到西昌城里的工农兵商场去了。再一打听,他的名字叫胡涂。
咋叫这种名字哦?我说。
我咋晓得呢,反正他就叫胡涂!女售货员说。
他是不是被他爸弄走了?我说。
这管你什么事!女售货员说,不耐烦地走到一边。
中午吃饭时,我刚一说完胡涂,我爸一下阴下脸来。下午上班出门时,神色也没好转一点。黄昏,我站在大院门口等他下班,想再跟他说说胡涂或者老保守,多少年来光是他一人常为老保守闹心,我已经长大,该帮他分担点什么。跟多年前刚来高原时一样,远方那片开阔地上的铁路厂房和住地,那些三五成群红砖红瓦的居住楼,那些各自成片机声隆隆的工厂,以及各在南北的学校和医院,全都遮挡在了被喇叭口两边的大山后面,更远更宽阔的安宁河河谷上空依然白茫茫的风季景像。对比之下,在数百米之内,山沟右边通往开阔地的土坡路边种着一排小树,残留着一些深秋的绿色。夏天的夜晚,我曾站在路边上,打亮电筒顺手在树上抓到过许多过夜的麻雀,带回家用电炉烤了吃。而在这条坡路下面不远处,西昌铁路分局机关大院的院墙修在两丈高的岩石堡坎上,从墙孔流出的水把墙下的土路拦腰冲成沟,我们一家大小每次从开阔地那边拉蜂窝煤回来,即使先拉上了校花家门前的大坡,最后无论如何仍过不了那道沟,只好连车一起抬过去。我爸就在那个大院里的电报所上班,路过那里时,老远就能听见里面传出来滴滴嗒嗒发报声和嘟嘟嘟的收报声。我爸说过电报所门上写着机密重地严禁进入八个字,言下之意是不准我们孩子到他那里去玩。而他常在下班时从分局食堂买一份炒菜端回家,菜里有零星肉片,一家人坐在桌边吃饭舍不得夹一筷子,三十年后我还能闻到那一股香味。
我爸那天很晚才回来,绷紧面孔跟我商谈了几分钟,夜里又大声说梦话。他那深更半夜断断续续突然间喊出的吼叫声,常把我妈吓得冒冷汗,也把爬上楼来的小偷吓失手,摔在窗户底下爬不起来。
第二天吃完中午饭,我爸一撂下饭碗就心急火燎地跟我一起从深沟里直奔开阔地,一进商店就跟那个女售货员打听胡涂的父亲。对方见家长找来了,态度好了些,但她说,胡涂的父亲死在监狱里了。
说这话时,她把一张脸从柜台里面伸出来,几乎要贴在我爸的脸上,声音也变得极小,像是两口子在说悄悄话。其实,商店里根本没几个人,而且都在远处。我爸被弄红了脸。
我爸低声说,他父亲被抓起来啦?
女售货员往两边看了一眼,虽然没直接回答,但也可以算是回答。
我爸又悄声说,为啥被抓的?
女售货员又把脸贴近说,嗨,还不是因为那个事。
话没说完,来了几个顾客,女售货员忙把脸缩回柜台,忙别的去了。
离开商店后,我爸迈着大步往深沟里走,嘴里哼着京剧调子,心气平缓下来。我跟在后面,看见他不时抬起头往两边看,猜想他可能在欣赏群山和篮天。至于他是因为胡涂父亲的下场还是女售货员那张贴近的脸才心情舒畅的,我则猜不准。
我跟上去说,胡涂他爹老保守死了,会是真的吗?
我爸说,到时候再问问考古学家,核实一下。
我说,你不是说找考古学家问那个老罗逃跑的事吗?怎么又扯上了老保守?
他说,都一样,你就别瞎操心了。
我觉得他把老保守与老罗两人搞混了,至少,我没法把那两个人想成一个人。因为很明显,两人不是一个时期的人,老罗早就跑到了台湾,而老保守,我还亲眼见过,就算他死在了监狱里,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