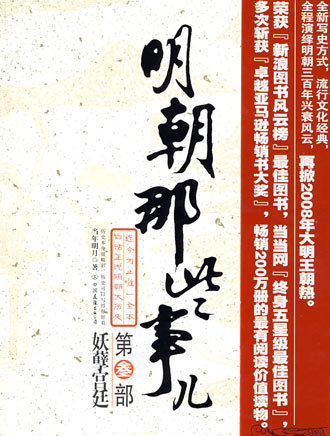成都--那些走远的人-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圈头脚相连的板架床,要是住的人多,还可以往上再搭一层,只需安上现成的活动架板拧上螺丝就行。接连数月又是外逃又是躲避却总也不震,住帐蓬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一夜因为那几个常跟我师傅练肌肉的单身汉互相打赌,其中一人裆部只勒一根布带就大摇大摆地闯进去睡觉,老古的老婆卷起被子就跑了出来。可能师傅知情后责难了对方,几人话不投机说打就打。一看他们总共有六人要跟我师傅一人对打,在夜色中的篮球场上正式动手之前,我问师傅需不需要我也动手。师傅大声嚷道:
这儿没你的事,靠一边站着。不是老想着看师傅的蛇拳吗?今天就是机会!
很快围满了人群的篮球场上,一场抛开哥们义气撕破脸,被行话称作抢手的对打开始了。群山之巅的上弦月不是很亮,只能望见一群对手和师傅的身影先是来回跳跃,接着快速穿梭散开又靠近聚拢,发出砰砰的击打声。一会,对手们被分别拉扯开距离,人影散落四边,师傅黑色的身影不时扑到地上飞快爬行,不时冲腾而起暴发尖厉的蛇叫声。如此三番五次追击,师傅的身影一会滚落地上成团,一会腾跃空中展开,蛇形手掌始终在眼前空中不停伸缩,每一猛烈前伸攻击,都会造成对手发出惨叫声。一场十来分钟的抢手,以对手全部倒地不起告终。除去开头的几阵打击声,围观的人们只见六七个人影满场舞动,一直没听见更多更响的拳打脚踢声,对结果有些不相信。他们不知道师傅的蛇形掌威力全在于不出声的点穴,自然也看不出更多的蛇拳妙处。但因老古的老婆及其引出的抢手事端,有人当即决定拆除那座军用帐蓬。
第二天晚上,老古的老婆把我叫到她家里,问师傅为何跟人打架,伤着没有。我看着桌上镜框里的老古遗像,一一告诉了她。从此后,她动不动就叫我去她家,直到有一天以开玩笑的样子又说出要我赔她娃娃,我才不敢再去。
几个逃地震的弟弟回来后,一家人仍对地震心存戒虑。开阔地那边不抵寒暑的地震棚歪外扭扭不成样子,但任凭天摇地晃也会岿然不动,留守在马道的人们和陆续回来的人们,对此都胸有成竹。然而,因跑地震人员一时减少,路人遇狼的消息不断传来。深沟里的人们都被反复告知,不论白天夜晚,路上一旦遇有东西从后面搭到肩膀上,万不可回头看,因为那是跟来的狼站立而起伸出的前爪,一回头狼就一口咬断人的喉咙。
冬春之交,我们几兄弟跟我爸从那边往回拉一车树杆和油毛毡的时候,又被刚走出楼外的校花看见了,但她没再跑来帮忙推车。想不到几天后,我正在大院一角为家里搭建地震棚时,校花走进了大院门。搭建地震棚跟干其他家务活一样,我仍没有长大以后才会滋生的那种吃苦耐劳的好感受,一见校花的影子就恨不能马上从棚架顶上溜下来藏起来。想必校花先找到了家里,跟我妈我爸说了一会话,只过了一会,就望见我爸带着她乐呵呵地朝我这边走来。
老三,看,谁来啦?我爸一到棚架前就乐得直嚷嚷。
伯父,你快回家忙你的,我在这帮他打下手。校花对我爸说。
那好,那好。我爸说,笑着转身就走,但马上又一回头,一边抬头望着我一边直冲我做一种难以理解的奇怪脸色。我往四周看了看,觉得没啥不对头,我踩在挺粗的树杆上掉不下去。我爸可能见我没懂他的意思,只好干着急,但再怎么做鬼脸也没用,干脆转身走掉。一直给我打下手的六弟见校花来了,又干了一会就没了人。搭地震棚很累人,我光着上身,下面穿了条练功时爱穿的短球裤,在离地一丈高的空中一会锯杆子,一会钉钉子,校花就在下面不停地往上递给我所需的每样东西。不多的几句话中,她回答说,在跑地震那趟火车上,班主任老师一到普雄就发作了,她和几个同学忙把老师弄下车,去了当地医院。
哎呀,你的那个都露出来了。她忽然朝我小声叫道,然后双手捂住两眼。
我低头一看,短裤太短,两条似有似无的裤腿又大又敞,连我从上面都看见了鸡鸡,别说在下面不停抬头往上看的校花了。这下,我才明白我爸刚才为何要跟我那样急迫地挤眉弄眼。手足无措之中,我抬起胳膊擦着流进眼睛的汗水,除了裆里面,浑身早已全是锯末面和灰,两手更黑。可能感觉出了我不自在,要不就是担心我会爬下棚顶不再接着干下去,校花忽又把两手放开,朝上看着我说:
你不好意思啦?
你回家算了。我说,仍叉着两腿踩在空中,暴露着下面。
在京剧团我就不小心扯过它,那次在路上我也帮你遮过它,有啥子嘛。你干你的,我不看就是了。她仰脸看着我说。
我心想,她说的也是,反正扯也扯过遮也遮过,再说附近又无人,她要再看管她呢。于是,只好又接着干活,两脚一踩在相隔一米来远的两根横杆上,想顾下面也顾不上,同样,校花要想不看也办不到了。
哎,它好像跟上次看到的不一样。校花仰着脸说,又一次举上来一根短木杆。
都过去三四年了,当然不一样。我说。
好怪哦。校花盯着我下面说。
我真没听出来,她是在说我怪,还是在说那个东西怪。
第二十四章 在偷看校花的日子里
第二十四章 在偷看校花的日子里
有一天很晚了,一身油污的大哥回家说他考上了司机,一家大小都围过来,我爸从梦里醒来,披上衣服下了床。大哥的样子很激动,说考司机的时候,他怎么驾驶着一列货车,考官们则在列车尾部的一节车箱上观察几根立在车箱地板上的木头棒子倒不倒。他说考完后,一个考官告诉他,他考的时候只倒了一根最长最细的木棍,还是在过道岔时太颠簸才倒的。当时刚下了千分之三的坡道,他看见有个人上了轨道,只好刹车,影响了考试成绩。
我妈说,是啥棍子呀?
大哥说,一会我再说棍子。
我妈一打岔,大哥忘了继续讲上轨道的那个人。接着,他讲起火车司机专业方面的一些事,大多是专用名词和数字,没一点故事,比我们班上数学老师讲的课还要枯躁,但一家人都假装很乐意听的样子。
大哥说,考司机操作只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考检车。我考的时候,有个考官突然叫我停,问我这个小部件是什么。
我妈又打岔说,你考上了司机,该多拿点钱了吧?
我爸抢着说,这还用问,肯定得涨工资!
我妈对大哥说,我记得你刚学徒那阵,每月工资八块钱,当上副司机后每月十九块,这下该涨个六块八块了吧?
我爸冲我妈说,你别老打岔,等他说完了再问。
我妈的又一次打岔,使大哥又忘了继续说那个叫他停的考官,转而讲起检车方面的事,越讲越来劲,直到把一家人讲得昏昏欲睡,忍不住打哈欠。
大哥二十来岁就当上了火车司机,我跟弟弟们跑到铁道边上,看有没有他驾驶的火车从远处开来。有一次,发现远远开来了1214号内燃机车,那正是大哥开的车。大哥坐在那么大的一个机车上,把一长列火车拉起来飞跑,我们只来得及看见一眼他脸部的侧面。那时候,我们真是高兴得想哭。
风季来临,马路上漫天黄土中飞扬着一张报纸。报纸在高空飘摇翻卷,最终落下来贴在我脸上。我闻出那是一张刚包过卤肉的报纸,一把扯下来扔到地上,但马上又捡起来带回家。报上登了整版的一首长诗,名叫《青春之歌》,署名北京大学集体创作,写的是有志青年男女志在广阔天地农村。开头几句是红日,白雪,兰天。报春鸟又怎么怎么了。我敢说,谁看了那么一首梦想狂一般的长诗,都打算扛上铺盖卷到农村种地去。
再过一年,校花就要高中毕业下乡当知青。学校宣传队依然隔三差五地排练节目,我想给她看我写的诗,但她总是跟一群漂亮的女同学一起满台子手舞足蹈,并且发出阵阵刺耳的歌唱和喊叫声。我看见,她在一排忽然前冲又忽而后退的队列里,不停地扭腰踏步又摆手,像一群被撵来撵去的快乐鸭子。特别是朝着演解放军战士的孔身上撩水的时候,那种欢笑的样子是最美不过的,一点看不出父母双亡在她身上留下了什么伤痛,也看不她的胸部跟孔有何不同。有点驼背的孔,胸部不是朝外挺,而是往内扣的,校花的胸部就那种样子。只是好几次,她的目光不经意间朝我一扫过,我脸上顿时发起烧来。我忽然发觉总想见校花,却原来已是这样怕她。更怕她万一对我笑一下,再问我是不是曾想约她一起上山晒鸡鸡,那样肯定会把我吓傻。
想来孔不会再敢有那种怪念头了吧?
不知从何时起,我已经羡慕起孔来,尤其羡慕他走起路来驼着背,搭拉着两只胳膊的样子,但他好像对校花不大感兴趣,一有时间就去操场上打篮球。而我由于校花,胆子越变越小,每当下课铃一响,只敢跑到她的教室门口或者窗外去看她。看情形,她挺用功,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做作业,当然,也跟女同学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在偷看校花的日子里,我注意到她的座位旁边的窗外地上,总有一些扔出来的碎纸片和别的一点垃圾,每天放学后就留下来,先磨蹭一会时间,等同学走光了就抓起扫把,悄悄跑到她窗外去扫地。一段时间以后,当校花换了座位,我停下来,当她再换到窗边时,才又去扫她的窗外。我心里说,她那么干净,窗外也该干干净净的。再说,我老抢她东西,还出主意导致广播室事件暴露,帮她扫扫地,就算给她赔不是吧。
有一次放学后,我看好四下没人正要动手扫校花窗外,忽听见她在教室里跟另一个女生在小声说话,就贴着墙立在窗边不敢动弹。
校花说,你看看我们全班的女生,哪一个像你。
同学说,我也没办法。
校花说,我这是在代表班委跟你谈话,你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
同学说,我这个地方长得太大,真的弄不平。
校花说,你看我,我这里还不是长得很大,咋就弄平了呢?你要像大家一样弄根长布带缠两圈,把那里捆住,就平了。
两人的谈话内容,跟那几堂生理卫生自习课差不多,我弄不懂。但听声音,另一个女生是校花班上长得又漂亮又丰满的那一个,她最引人注意的是鼓得老高的胸部,说不定校花说的就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校花的胸部变没有了,看来跟孔完全是两码事。
一天放学后,除了孔他们一群勾胸驼背的男生在篮球场上穷蹦傻跳,整个校园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我又偷偷去扫校花的窗外,发现校花一个人在教室里做作业,心里一阵慌乱。在她的窗外,我久久徘徊,胡思乱想,听见教室里板凳响,以为她要出来了,就赶紧溜走,逃到不远处的厕所里。本想等她走后再去扫地,但没过两分钟,她哼着京剧进了女厕所。隔着一堵没封顶的墙,校花解裤带弄得钥匙响,接着发出哗哗哗的撒尿声。那一刻,长长的一口气憋在我胸口不敢吐出来,惟恐她在隔壁听见。这一样来,更加重了对她的惧怕,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遇见她迎面走来,我就低着头像个罪人一般。
礼拜天,我钻进深沟里,倒在阳光下的草坡上,翻开刚从商店里买到的一本油画册。上面有一幅女裸体画,虽然被画画的家伙故意画得很模糊,特别是阴部被画得跟足球的一个局部差不多,但看着看着我想起了校花在厕所里的样子。我掏出翘得老高的老二,手一翻动包皮,就像触动了什么开关,突然迸发出一阵奇异的感觉。
很多年以后,在高原上的秋季里,当校花微笑着地听我用许许多多细节描述完当年我对她的情意,她感叹不已,连说相见恨晚,又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当她再静静地听我用一种抽像的方法,讲述完我当年对她的意淫,她就脱光了全身,露出了真正的她。那一次,我可能被她全身上下发出来的阵阵强化光照花了双眼,要不就是被记忆深处放射的道道绚丽弧光挡住了视线,狂乱的心跳中,我什么也看不清,只能感觉出我的老二比她的乳房要软得多,一点也不中用。
第二十五章 考古学家从坟墓带来的东西
第二十五章 考古学家从坟墓带来的东西
考古学家说话算话,隔不久就来我家,呆不上三分钟就走人。每回一身泥土,蓬头垢面,站在屋当中不坐下,一边说着话一边从鼓囊囊的牛皮脏挎包里掏出点东西来放在饭桌上,不是一颗老长的人牙就是一小块人头骨,要不就是一小把长头发,还有发绿的铜钱、一摸就碎的破书什么的,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
送给你作个纪念。考古学家每次都对我爸这样说,话中带着坟墓里的气味。
等他一走,我爸就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饭桌上那些可怕的东西,同样不用三分钟就会打瞌睡说起梦话来。醒来后总说,等哪天考古学家再来家里,无论如何也得把他留下来,请他坐一会儿。
我妈也说,就算留不住人家吃饭,也总得请人家多喝几口水。
二哥说,上次他还想把马给咱们家,人挺大方。
我爸说,可不是,每次都带坟地里的脏东西来吓人,多实在的一个人,又有学问。
就在叨念考古学家好处的时候,有一天他从深沟里出来,手上拿着一条大蛇,吓得我们全都尖叫起来。
他站在门里笑眯眯地跟我爸说,这条蛇是刚在坑里捉到的,留给你养吧。
我爸直往后退,急忙说,不要不要,你快拿走!
考古学家笑着说,你爱养鸡,养条蛇更有意思,蛇最喜欢鸡了。
一说起鸡,我爸睡觉的屋里马上传来一大群小鸡的叫声。
我爸大声说,我知道蛇喜欢鸡,我还知道蛇喜欢鸡是因为想吃鸡,你快走人吧!
我爸是个沉不住的人,说翻脸就翻脸。
考古学家连声说好,好,你不养我带回家养。
说完这话,我们都以为他马上会走,不想他反而进屋,到饭桌边坐下。他把拿蛇的手放在饭桌上,两个手指掐着蛇的脖子,让蛇身缠着自己的一只光手臂,同时看着我爸,一脸的高兴劲像有什么话想跟我爸说说。我爸站在床边不敢靠近,我妈和几个孩孩也都站在几米远的厨房里。那条蛇不时朝考古学家张开大嘴,亮出两排尖牙,吐出闪动的信子,实在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