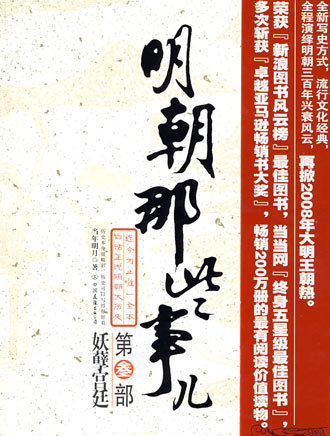成都--那些走远的人-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你说,我认不认识老歪?
算喽,你这个鸡八娃儿太瓜,不跟你说了。
雷巴走了,我下半夜没能再睡觉,往事如过眼云眼飘来又飘走,一个个面容模糊的人影摇摇晃晃地浮现,又消隐。
第四章 一根一根地拔光阴毛
第四章 一根一根地拔光阴毛
在抢收离公路不远的一片稻谷那天,一辆吉普车在公路边停下,从车里下来了我师傅,但他并没到田里来看我,而是站在路边高声叫喊大奶的名字。大奶扔下手里的活,朝吉普车跑去,田里的知青都停下来望着那辆吉普车,满以为车上会走下来大奶那个已经名声大噪的父亲,向大奶道出一个人们期待中的救援军列特大喜讯,再由大奶带到田里看看大家或者领到农场去看看大奶下乡新安的家。但事情全不是这样,大家望见大奶一到车边马上被叫上了车,车门一关就立即开动,朝马道方向急驶而去。
一身脏透的大奶突然被专车接走了,田里的人们顿时放下农活,聚在一起,被一种不祥之兆弄得炸开了锅。连正副场长也顾不上满坡遍野急待抢收的稻谷,立在一旁窃窃私语。当知青们把各种最坏的想法说了一遍又一遍,场长不得不发话要大家重新投入抢收时,雷巴暗使的几个知青把我围住了。
白娃儿,听说你要把我们舵爷摆平?一个光头知青笑着站在我面前说。
我虽姓白,但有名有姓不叫白娃儿。人们不管你姓什么,只把那种不懂事的人才蔑称为白娃儿,意思是白光光的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不过是个小孩。我打量了一下面前挑衅的光头,看见了十米开外嘴里叼着烟,虚着两眼静观的雷巴,知道他就是面前这个光头知青所说的舵爷。
我们无冤无仇,算了嘛。我对光头说。
算了?哼,说起来轻松。他说,朝前走一步,其他几个方向的也跟他一样。
啥子意思哦?不要惹我不高兴哦!孔站了出来,面对着光头说。
孔,躲远点,不要血溅到你身上。我说,孔听从了。
光头也听到了血字,装腔作势地低头看看自己,又抬头看看我身上,接着再前走一步,伸出老长一只手,用三根手指夸张地拈着我肩膀,像拈着一件破衣服那样往上一提,再一转圈,我顺势转了两转,让他前后上下看了个够。
哪有血嘛?他说,一脸看不起我的神态。
放手!场长喊着走过来,周围已站满观看的新老知青和一些农民。
听到没有?副场长也叫着奔过来,光头这才放开我。
关你们两个鸡八事!雷巴朝两个挡驾的场长喊了一声,仍站在十多米远,众人闻声看去。
你雷巴欺负一个新知青,要不得。你看这个白娃儿,瘦得像根包谷杆,风都吹得倒!场长看着雷巴说。
嘿,要不得?你问问白娃儿要不要得?雷巴回敬道。
光头好像听到了指令,又伸手用几指拈住我肩膀。我两手垂吊着一偏头,作出一副张嘴咬他又咬不到的架式,光头一边又扯又提,一边笑出声来。
你的手不要躲,只要你过一会打不死我,我就要咬你。我说。
这个样子还干不干活了嘛!副场长吼道,看着雷巴。
上!光头把我一推,朝另几个同伙抬手一挥,自己后退几步,几人围近要动手了。
住手!太不像话了!场长朝我跳过来,要保护我,又回头看着雷巴。
你插在中间,今天怕是就干不成活了。雷巴回应场长。
那你们也不能几个打一个嘛。副场长说。
要不然,一个对一个打两下,我一喊停就停,然后就马上开始干活?场长问雷巴。
行啊,你说了算。雷巴说。
于是,大家后退散开,空出场地,几个女新知青一跑就是老远。我提了下裤子,站在空地当中,看谁要跟我单挑。光头不想自己出手,他挥手让一个小平头上,好像不屑于多看我一眼。小平头眼光阴狠,看着我扳了几下自己的手指关节,连续发出嘎吧声响。我一副畏惧相,移到田埂上等待,像要随时顺着田埂跑掉。小平头一准备好就对准我冲过来,我来了个脚下一滑,两腿一软,身子一歪,让小平头越过我栽到了下面一级农田里。
重来重来,我还没站稳!我立即叫起来。
但小平头已经无法重来一次了,他重重地摔在田中,头倒栽在半干的泥里,脖子被扭伤,一爬起来就歪着脖颈喊遭了,一蹲下去就再也立不起来。
看到了嘛,喊你们不要打偏不听!场长喊道。
开工!开工!副场长也喊。
慢!白娃儿自己说的他还没站稳,要重新来。雷巴在远处说。
重来重来!几个同伙齐声喊。
那就最后一次。场长只好发了话。
先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副场长看着雷巴强调说,还抬手示我到田当中去,免得又站不稳被雷巴钻空子。
我搭拉着两条手臂,从田埂上移到了田当中,看见光头仍不想亲自上阵,而是打手势要另两个兄弟伙趁两个场长不备同时上。随着什么人凑热闹喊了一声开始,我就看出前后两个对手一阵急步猛冲而来,于是当即发出唉哟一声,忙蹲下去就地一倒,想让两个对手自己去撞自己,不料结果真是如此。旋即,我站起来一看,两人虽未头碰头,但脸撞了脸,身体更不用说,转眼间已经满面是血,各自双手捂脸蹲着,血还顺着手指直流。
让开!雷巴稳不住了,大吼一声几步跳过来。
我转身又去了田埂上,让他一把抓住。在两个场长和众人急切的劝叫声中,雷巴不管三七二十一,左手揪着胸口把我提起来,右手一收拳就要即将发力而出。我赶忙两手把他抓我的左手臂一抱,使他左臂受重,右手一时出不了拳。接着,他趁势松开抓我胸口的五指,让我双手吊在手臂上,同时几下调整好重心,又一次往后收回右拳。就在右拳猛然冲击而出那一瞬间,我双手一松,全身一下落地,把他两腿抱住。刹时间,只感觉他脚被绊住,上面整个人猛地朝出拳的方向扑倒下去,摔在田埂之下。我随即松开他,连滚带爬站起来,在旁边看着他,一副手足无措的害怕样子。刚才那几个受伤的雷巴小兄弟急忙跑来围着他,照样无能为力,而其他几个还没交手的小兄弟忙跳下田埂,又扶又抱地才把他弄起来。
行了行了!两个场长同样叫喊着跑过来。
好,可以,可以。雷巴词不达意地说着,怒不可遏地看我几眼,抬起衣袖不停地擦脸上的泥巴。
大家开始干!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不然今天收不成工!副场长对着大家喊。
遭了,老子的膀子脱臼了。雷巴低声说,
你也是,白娃儿都被你吓得滚到了地上,你还用那么大的劲冲拳,咋不脱臼嘛?咋不把你带倒嘛!场长扶着雷巴说。
你的手劲太大了,单手都把白娃儿吊得起来!副场长也讨好雷巴说。
我感觉后面有人踢过来一脚,身体一让,果然如此,踢在了副场长屁股上。
妈的批!还要打嗦?再不听再打,老人就把人捆到公社去!他吼道。
然后,他叫我滚蛋,和孔一起滚回农场去喝茶,以免留在田里惹事生非。我听出来,副场长这样做,是为了平衡一下雷巴那伙人,于是,我十分顺从地叫上孔马上顺着田埂离去,老远还听见场长在喊卫生员,去帮雷巴对膀子。
你狗日的太凶了,手都没动一下,他们就连遭了几个人,到现在还没摸到火门。孔边走边在后面说。
我告诉孔,那几招都是小儿科,是小时候在京剧团跟武功老师学的,现代京剧武戏里面有许多类似的小动作,我们男男女女每人每天都练,熟得就跟爹妈一样。孔听了,说我以假乱真出尽了洋相,又连骂了我几声狗日的。我叫他不要外传,以免露马脚,又问他想不想趁机去一趟火车站,打听一下军列的事。听我说了路程后,他想了想,最后说路太远,晚饭之前回不来,还是照副场长说的回农场喝茶算了。
果不出孔所言,等到下午一收工,陆续回农场的知青们老远一见我立在大房子门口,就觉得好笑,纷纷开心地高喊白娃儿,连一些女知青也跟我开玩笑,分不清是嘲弄还是亲热。怕她们心血来潮捉弄欺侮我,我只得回屋避开。但有几个大点的西昌女知青站在楼上一声声地不停叫喊白娃儿,直把我叫出大屋子,再喊上楼,叫我帮她们去伙房打饭,她们懒得动。
嘿,你们还会享福嘛!我站在她们门外走廊上笑着说。
少废话,快进来拿碗,当心马上就把毛给你褪掉!一个女知青从脸盆里抬起头来对我说。
我站着没动,一下想起西昌武斗时,一个著名的红卫兵女司令落到对方手中,被掳到礼州脱光绑在大桌子上,然后被众人一根一根地先拔掉腋毛,再一根一根地扯掉阴毛。
晓不晓得啥子叫褪掉你的毛毛儿?另一个拿毛巾擦脸的女知青说。
晓得一点,以前听说过,是不是那个哦?我说。
雷巴已经下话,随时要把你的神光先褪掉,然后再把你的毛毛儿全都褪掉掉!洗脸的女知青又说。
你们的西昌话好好听哦――毛毛儿,褪掉掉。我说,笑着学了两句。
要不是我们几个帮你说好话,你白娃儿现在肯定已经被他们打成扁扁,毛毛儿一根不剩了。另一个靠在床头上说,意思是要我识相。
我依然笑着,进屋在门口一侧地上拿走几个碗。从雷巴门口经过时,又瞥见屋内,光头正帮他弄膀子,小平头正歪着脖颈在一旁看,另两个脸上则擦满紫药水,还贴上了几块药布,都在帮雷巴忙。
我才不在乎雷巴他们会不会像那个女知青说的那样放过我,但有点怕她们几个女知青一根一根地褪毛。农场里的不少老知青会弹他,西瓜有一把,弹得非常好,我们已多次在梦里听见他在楼上自弹自唱。他在伙房门口见了我说:
你虾子打架太笨了,以后少惹雷巴他们,我来教你弹吉他。你这种瘦筋筋的人,正好是弹六弦琴的料。
雷巴隔壁住的那几个西昌女知青,是不是也惹不得?我请教道。
哦,那几个才更碰不得,两个场长都是她们的亲戚,公社也有。雷巴都被她们整过,后来关系才好的。西瓜说。
于是天一黑,我放轻脚步上楼走进他的屋子,开始跟他学吉他。
第五章 发生一场斗殴,梦见军列颠覆
第五章 发生一场斗殴,梦见军列颠覆
脸上爱笑的西瓜用满口很钢火的重庆口音开口就告诉我,舒伯特说吉他是一件美妙的乐器,可是真正了解它的人却廖廖无几。
舒伯特是不是我们场长?我问道。
就是,吉他是乐器王子,不是,乱弹琴!不要打断我讲话。他说。
又告诉我,吉他是一件非长古老的乐器,比小提琴、钢琴的历史还远久,要具体说清产生于何时简直不可能,有人说最早公元前三千年出现在古埃及的里拉琴是吉他的祖先,后来慢慢演变,传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到了二十世纪传遍世界,与钢琴、小提琴并称为世界三大乐器。在种类上,吉他又分古典吉他、民谣吉他、夏威夷吉他、佛拉门哥吉他和匹克吉他,最后还有电吉他。最高级的最难学的是古典吉他,最随便最普及的是民谣吉他。
西瓜说出来的东西,我发觉根本就不是地球上中国人说的话。他讲的那些怪话,我有许多从来就没听说过。我只晓得西班牙是外国,意大利是法西斯墨索尼里那一国的,但公元前是好多年,二十世纪是哪一年,我就不晓得。本以为舒伯特是我们农长场长的名字,但他又说不是,鬼晓得是不是在骗人。
我问他刚说的那些,是不是从哪个地方偷听来的,他看着我一下子不笑了。我深一步问他是不是从敌台偷听来的,他一张开嘴,但更加说不出话来。我说我读过那么书,从没听过他说的那些。
你读过哪些书?他说话了。
《工农兵诗选》、《高玉宝》、《虹南作战史》,等等一大堆。我说。
还有没有?他说。
有啊,《少女之心》手抄本。我说。
你说的都不是外国的。他说。
外国的也有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普希金的诗歌手抄本。我说。
我还说他讲的时候一直在笑,就发现上当了。西瓜不好再笑,歪着头朝别处看去,样子是在想什么,接着瘪了瘪嘴,又摇了摇头,样子又像在说完了,骗不了人。于是,不再动嘴东说西说,开始动手教我西班牙式民谣,从C调的哆来咪法嗦啦西哆。当我勉强能用左右手协调地摁住钢丝弦弹拨时,他留下我独自练习,自己去了隔壁那三个西昌女知青屋子。没过一会,就传来了一群男女的哄笑。我不知道那些人为何大笑,但猜想多半与我有关,也听出了西瓜跟她们关系不一般。半个来钟头后,西瓜回来,看我练了一会,说不错,还表示同意我把六弦琴带回大屋子去自己练。我刚要走,隔壁那三位就走进门来,我以为是冲我来的,结果不像。
西瓜,弹一曲来听嘛。她们中的一人说,另两个也一样的神态。
好,弹一曲。西瓜说。
他接过吉他坐到床边,把琴放在大腿上,然后自弹自唱,发出低缓沙崖的歌声:
金色的学生时代,
已载入历史的史册,
一去再也不复返。
沉重地修地球,
我光荣而神圣的职责,
啊拉的命运。
等我在一阵喝彩声中拿过琴出门,一回大房子就见孔坐在大奶的床上。他像是有急事要跟我说,但见我手拿了一把吉他,开口先问我跑哪里去了。
到处找不到你,他们要打我。他说。
谁?我说。
几个西昌知青,但带头的是光头。他说。
男的还是女的。我说。
当然是男的,莫非我还怕女的?他说。
因为什么?我说。
他们怪我今天白天在田里跳出来帮你说话,说你都服了,我还没服气。他说。
动手没有?我说。
他们说等一停电熄灯,就要我去晒场见他们,他们中间可能有人守夜。他说。
没事,一会我陪你一起去。我说。
孔放心下来后,我把西瓜交给我的一大厚本手抄歌曲集翻开,里面抄的大多是不准唱的黄色歌曲,其中不少是知青歌曲。翻了一阵,放在窗前箱子上,我照着他刚弹过了《金色的学生时代》开始练吉他。孔坐在一边看了一会,又出去了一会,等屋顶电灯泡突然自己一灭时,才又返回来。
我俩准时赶到了那个我看守过一夜的晒场,对方几个人已在等候。只是夜色中,看不清到底是几人,又是哪几个,就跟昨夜面对雷巴时一样只能辫出人影。等他们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