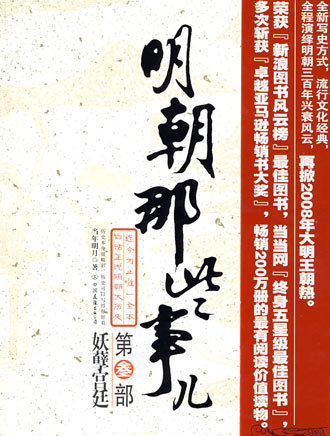成都--那些走远的人-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在学徒中最小,大家每时每刻都在埋头苦练,惟独我怕疼怕苦老爱找空子缩在一边躲着,这样就形成了每时每刻都有老师盯着我,挥舞着家伙追着我练,一偷懒就挨抽。那些都是眼急手快的师傅,一抽一砍一个准,一戳一刺疼死人。因而,两年练下来,除了少不掉的基本功,我恐怕练得最棒的就是怎样躲避挨打,练到后来别说老师追来,哪怕老师的气味还未到,甚至老师想打的念头刚冒出来,我就早已提前一躲了之,一缩了事。想想看,雷巴他们那种大不咧咧的样子,怎能奈何得了我呢?
孔的叫声又从林中传出来,听起来已不如先前那样紧急。既然雷巴不再理我,我也不想再理他们,索性寻着孔的声音走向树林深处。没走进多深,正好遇上那几个女知青懒洋洋地走出来,与我相错而过,人人挽起的袖口还没放下来,好像刚从田里收工回来一样。我又继续往里走,不久找到孔时,已经相隔很近。他先没发现我,正在林中一小块草地上系裤腰带,上身还光着,一旁草地上扔着他的一件上衣和一双塑料凉鞋。等我走到他面前时,他怔怔地看着我不说话,脸上和脖颈水淋淋的,头发也湿漉漉的,上面还糊着伙房稠米汤一样的东西,上身和头上粘着一些草。
是不是跟她们打了一架?我问道。
他声音含混地啊了一声,或者是哦了一声,然后皱起眉毛,苦着一张脸使劲嗅嗅鼻子,再之后就只顾抓起一旁的上衣往自己身上套,接着又蹲下去,一边埋头穿鞋系鞋带,一边不断往草地上东看西看。草地上有一根乱成团的红色细毛线,另有两张或者三张湿透的花手绢,角与角系在一起,扔在稍远一点的草里。
还去不去火车站?我说。
唉哟,我这个样子,哪里还走得动路嘛。他说,又叫了一声唉哟。
你是不是被她们打了?我又说。
嘿嘿,嘿嘿。他不回答,只发出几声怪笑,变得有点神经质。
又是喊唉哟又是嘿嘿笑,说嘛,她们到底把你咋样了嘛?我追问道。
说话间,他已经穿弄好,站直了身子,但一脸害瘟的神色,看着我摇了摇头。站了一会,他可能觉得裆里不舒服,往后撅了撅屁股,缩了缩下身,这才好了一些。临走前,他低头看了看脚下的草地,又四处打量了一番,像要找寻丢失的什么东西。看样子没找到,就发出几声很难听的苦笑,末尾还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狗日的不得了,连女知青都这么凶!
第十章 人民日报刊登军列救援结果
第十章 人民日报刊登军列救援结果
我不明白几个女知青用了何种办法把从前那个爱说爱笑欢蹦乱跳的孔一下就改变了。
从那天离开林中草地开始,他好像有了不可告人的心事,成天少言寡语,只用鼻孔发出哼哼声,一看着什么就两眼出神。我暗自记数了一下,发现他连着数日只对我重复说过一种话,就是一句:唉,完了。此外就是一两下无言词的哼哼声。
问他是不是在想那几个女知青?
他只哼一声,不再多说半句。
问他还出不出工?
哼。他说,往床上一倒。
问他傍晚出不出去散步。
哼。他坐在床边仍这样回答,接着继续吃饭。
就在那些天中,对面楼上的外走廊栏杆处,常常站着几个在山坡上露过几手的男知青,或者那几个改变了孔的女知青,要不就是几男几女都站在那里,闲了没事干的样子仿佛在看天井,但不时也朝我的破窗口张望。他们多数时候默默无声,偶尔会突然嘻哈打笑一通,还会忽然间吹口哨。传说附近一个半老的中医每天要上楼去为两个受伤的男知青换什么药,同时为其中一个推拿。还听说肛门受伤的那个男知青,耍的女朋友是不远处某生产队的女知青,每天黄昏都会专程跑来看望。而伤了雀雀的男知青,耍的女朋友就是那天叫我上楼取饭盒,帮她们几个女知青去伙房打饭的那个。她给我留下过挺深的印像,那天在山坡上没见到她,那几个在林中玩孔的女知青中自然也没有她。我没事就坐在床边练吉他,练累了才从破窗一角朝对面望几眼,看的次数一多,才看出她比其他几个女知青好看得多,一头黑发不是妈妈式,也没编辫子扎究鬏鬏,而是披肩长发在后面随便捆扎了一条蓝花手绢。
孔不偷看窗外,特别是女知青们站在那里的时候更如此。
几天后,我们又在靠近公路的大田里抢收,孔埋头苦干闷声不响,间息时也不再去跟别的知青打打闹闹,一遇见那几个女知青就一躲老远。到了中午,我们曾经见过的那辆吉普车又悄然出现在远方,很快在我们下方的路边停住,发出的刺耳刹车声引起了不少人注意,田里马上就有人喊叫:
大家快看,吉普车又来了!
坡地里劳作的上百号人立即停下手里的活,纷纷直起腰朝路边小车望去。车门打开了,从车上先下来了我师傅,接着是大奶,最后还有个上岁数戴口罩的女人。几人站在车旁朝我们望过来,一边远望一边比划着手说话。看了一会,几人又面对面交谈,仍然比比划划。接着,女人把大奶招到面前说话,说了好一阵才又抬起头,最后朝我们望了望。而后,我师傅手扶着那个女人请她先上车,自己随后也上了车。
等吉普车一开走,大奶提着一大网兜东西,踩着纵横交错的田埂朝我们走来,场长喊了一个新知青跑去帮忙拿东西。等大奶空着手一来到大田,两个场长带头迎上去,人们很快把他围起来,七嘴八舌问那趟失控遇险的军列。
军列?又有什么军列?大奶在人群中反问道。
嘿,你咋啦,就是那趟军列,拉火箭和卫星的军列!场长大叫道。
就是那躺拉导弹的军列!副场长也高声说。
哦,是那趟军列嗦,我还以为又有一趟军列出事了。都过这么久了,你们怎么还不知道结果?大奶问道。
不晓得!你快说!快说!人们一齐喊起来。
我带来一张人民日报,马上就拿给大家看。大奶说着,没了声音,仍也不见了。
我站在人群外围,看不见他,估计他弯下腰正在地上的那个网兜里取报纸,果然不一会,场长手拿着一张报纸举得老高,但翻来找去不知该看何处。于是,大家急了,要大奶赶快直接报告军列救援结果,喊叫声响成一气。场长也不再看报,催大奶快说,还叫大家不要讲话。等大家一静下来,大奶一字一句说道:
好,我说,我说。那趟军列没出任何事,最后安全到达了马道!
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哦哦哦的吼叫声,转而又变成一片乌啦声!场长更是兴高采烈,他偏头跟身边脸上乐开花的副场长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转着方向对纷纷狂欢着跑开去的人们喊道:
现在我宣布,现在大家加油干,争取提前收工,开个庆功会。副场长马上带两个人回去,杀掉农场的大猪,晚上全体吃回锅肉!
场长本想还说几句,但倾刻间又爆发的一片欢呼声淹埋了一切,他只好自己跟自己笑了一阵,接着又把一张几乎笑烂的脸转向背后的我,又转向我旁边的孔,最后转向孔旁边仍立在原地的大奶,不停地问寒问暖。但大奶精神很差,显得疲惫不堪,一问才知已经接连多日熬夜看护住院的父亲,没怎么睡好觉。
你爸爸病了?场长问,格外关心。
那天铁路来汽车接我回去,就是因为我父亲住进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大奶说。
他老人家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救援那趟军列?副场长说。
大奶想说什么,好像又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让人觉得他那种难言的神情后面有一大堆不好说出来的东西。场长见此,叫我马上送大奶回农场休息。但大奶不要我送,说他自己能走。副场长见大奶不要我送,就叫孔送大奶回农场,大奶有气无力地笑了笑,仍坚持不要人送,还补充说他母亲刚才在公路边再三叮嘱他,要好好劳动,别给农场添麻烦。
你是说刚才那个戴口罩的太太是你的妈妈?场长又问起来。
是我母亲,专门来送我。大奶说。
那你怎么不把她老人家请上来?副场长说,神情很急切。
是啊,你咋不跟我们说一声嘛?看我们连口水都没请她喝上一口!场长批评大奶。
你该叫你妈到农场坐一下嘛,反正农场又不远。孔也说起话来。
说来问去,谁也没问大奶他母亲为何夏天还戴个口罩,大奶也没再说什么,但糟糕的神情像是已快要挺不住了。我心想,大奶是领导干部子弟,他母亲之所以来看儿子既不下车又没去农场,多半是为了不耽误儿子劳动,那样也会影响不好。况且,我妈说过大奶的母亲成天老戴着个口罩不说话,让人挺害怕。要是她那种样子在田里和农场到处转来转去,人家会说她怕脏怕臭,就更成问题了。不过,我一直不记得从小到大何时亲眼见过大奶的母亲。
大奶提着网兜顺田埂离去,颇显神秘的背影渐渐变小。两个场长目送完大奶,又掉头四处望了望,田里的知青们东一片西一片,已经干得热火朝天。从两人的谈话中,我和孔听出来,与那趟军列丝毫不挨边的农场,之所以要庆功,是因为在我们这批新知青来的时候,铁路方面已经答应要送给农场一部手扶式拖拉机。同样在这时,场长好像才发现我和孔没事干,于是大叫一声:
你们两个还不赶快去干活!
第十一章 我听说我的爱人流浪到台北
第十一章 我听说我的爱人流浪到台北
军列成功救援和一顿回锅肉鼓起的冲天干劲,让我们不仅超额完成全天的抢收量,而且不到下午六点就已返回农场,坐在了那间大屋子里等着开庆功会。一阵掌声中,两个场长挺胸走进门来,跟我参加的头一次会一样,场长开口就问大家:
唱个歌怎么样?
结果众人大叫先开会,开完时再唱。场长挺爱听取群众意见,于是改先唱歌为讲话,要讲讲为何要开这个庆功会,不料大家又喊叫说不用讲,以后开会再讲。场长无奈,连说几声好好好,接着拿出那张《人民日报》,说先给大家念念上面的消息,念完就散会。但大家还是不干,喊叫说回锅肉都快弄好了,先去吃了再来开。见身边的副场长咧着大嘴直笑,场长干脆朝大家摆手说道:
好好好,以后再开庆功会,只唱个歌怎么样?
好!大家齐声叫道。
来,西瓜,你起个头!副场长点西瓜的名。
唱哪一首?西瓜站起来问。
哎,不说上次说好了,就那首《流浪到台北》。上次没唱成现在补唱。场长对西瓜说。
接着,西瓜用一副烟熏坏的破嗓子起了头,全体开始大合唱:
我听说我的爱人流浪到台北,
只是因为爱人流浪我的人儿碎。
我怀着一线希望跟随到台北,
希望她回心转意和我并飞,
啊,我的爱人流浪到台北。
悲凉哀怨的知青歌曲,歌词共有两段,我听得不很完整。但一首与开会毫无关系的知青歌,为什么包括两个场长在内,上百号人唱得整整齐齐又情真意切,我真是搞不懂。台北,就在台湾,那是不共戴天的国民党的地盘,仅仅台北二字听起来就叫人不寒而栗,毛骨耸然,居然还唱得如此纵情有气势。然而听着听着,我的心不再害怕,旺旺泪水不禁流淌下来。我看见斜对面席地而坐的雷巴和孔,以及打过交道的那些男女知青,也个个满脸悲哀,唱得很卖力。
会没开成,但唱了首歌,也挺不错。散会回到大房子里,大奶仍在床上酣睡,全身只穿了条内裤,裆部顶得老高。我在自己床边坐下,翻开西瓜的歌本一字一句地细看《我的爱人流浪在台北》,想再等一会才叫醒大奶。一会,孔轻手轻脚进来坐下小声说,他刚去伙房看见回锅肉已煮熟切好,但这个季节没有蒜苗,炒回锅肉没蒜苗又不香,伙房的人只好跑到附近农民家买其他菜去了,还要等一阵。
孔身上带着一股煮肉的香味,一顿尚未进嘴的回锅肉让他重新开口讲话,又把他变回了以前的活泼样子。窗外响起了乱糟糟的铝勺敲瓷碗声,孔站起来看了看窗外,忽然转头小声对我说,他看见校花上了对面楼上。
是不是真看准了?我一惊,低声说。
没看走眼,真的是校花,进了女知青屋子,雷巴也跟了进去。孔说,又直起身看窗外。
如果说校花的忽然到来让我深为惊喜,那么雷巴跟她混在一起,又让我格外惊谔。孔说他要出去转一转,再上楼去看一看,然后悄声离开。我看着歌本直发呆,想着校花为何不来找我,知不知道我就在农场,知不知道她已来到我的身边,但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大院里的敲碗声此起彼伏,楼上楼下的知青们开怀说笑,其中也夹杂着农场技术农民的当地土语,声音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农场的黄昏沉浸在一片自由欢乐的炎热之中。平躺的大奶翻了个身,把两眼依然紧闭的脸转向我,翘着的雀雀从短裤里露出来,粗壮红润,无比自在。这时候,虽然早已日斜西山,但天气依然火热,恐怕高原河谷平原上除了大奶,没人能躺在床上安然入睡。要是另还有人的话,对面楼上那两个受伤的知青可以算在内,但两人顶多正躺着,要么在小心轻轻地走动,不会酣然大睡。
孔又悄悄摸回来了。说校花的确在楼上女知青屋里,正跟女知青们玩,是她们带话叫她来吃回锅肉的,还跟他说了几句话。
我还看到外面来的一些知青,都不认识,也都是来吃回锅肉的。孔说,在我身边坐下。
校花问没问我?我说。
没问。孔说。
你没跟她说我就在农场?我说。
那些男女知青都在场,有两个还被你打过,没好说。孔说。
你跟那些知青还不是一样,特别是几个女知青,咋又好跑去呢?我说,没把话说太透。
嘿嘿,这个你就不懂了嘛。孔说,低声笑起来。
孔那种深不可测的笑法使我想起那天在山林中,那几个女知青走后,他一人在草地上系裤子时的样子,又感觉事有蹊跷。当时,他头上脸上和脖子上水浇过一样湿,头发上又粘着米汤状的白色东西,加上草地上那团红毛线,还有那两三张显然是女知青扔掉不要的花手绢,同时一连多日孔的一反常态,那一切,孔还一直没说出是怎么回事。
我看着孔,把这些疑惑跟他合盘托出,要他道出实情。
他又嘿嘿笑了笑,表示以后一定说给我听。
以后是多久?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