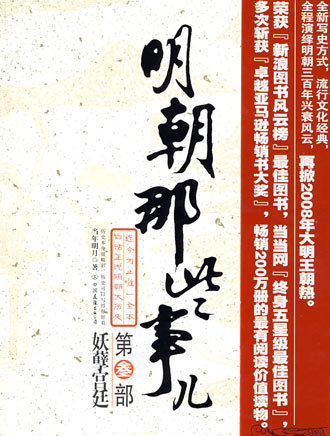成都--那些走远的人-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看着孔,把这些疑惑跟他合盘托出,要他道出实情。
他又嘿嘿笑了笑,表示以后一定说给我听。
以后是多久?我说。
反正要给你说嘛。他说。
看来那天在山林中,你跟她们还真出了什么事?我说。
他点点头。
这时大奶终于醒了。他翻身坐起来,问我跟孔在叽叽咕咕说什么,吵得他做恶梦。我和孔问他军列救援的具体情况,他想了想说道:
那趟军列于当日早上七时四十分如期而至,从马道火车站的侧线冲上了新开辟的上山坡道,接着冲上高地,像摇篮中熟睡的婴儿那样,在一段凹型线路上来回滑行,速度一次比一次减慢,最终稳稳地停下来。听说那趟军列一共挂了三十多节车箱,刚冲上新建的避难新线时,上千名筑路铺轨的人员中,有许多抡着大锤砸道钉和舞动扳钳上配件的抢险人员没来得及撤出。
你父亲怎么了?我说。
过度紧张劳累,等军列一停稳,他就栽倒在地,心脏突然不跳了。他说。
好没有?孔说。
大奶没立即回答,起身下地穿上外衣又坐下后,才慢慢告诉我俩,幸好当时铁路医院早有准备,出动了大批医护人员到现场参加军列救援,当场就把他父亲抢救了过来,但后来送进医院后又反复休克了几次,大奶走的时候,飞机已把他父亲送到北京治疗去了。大奶最后说道:
我爸在病床上对我说,他在拿救援方案的那一两个小时中,一下子把毕生的知识技术经验全用了出来。
大奶对我和孔讲的他父亲指挥的军列救援抢险行动,让人惊喜万分,更让人对老包充满无比敬仰之情。我看着大奶,把说过多次的话又重复对他说,我当时亲眼看见你爸拿救援方案时,站过一会的地上,流了一地的汗水,你爸的头发就是在那一两个小时中变白的,但没想到到后来,他差点崩溃。
大奶想了下崩溃这个说法,忽又想起什么,忙从床下那个还没打开的大网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说是我爸妈在医院看护他父亲时叫他转交给我的。我拆开信一看,我爸那种与当年一样奔放而钢劲的字体突现眼前。信上说,铁路上发生的那件事情真是惊天动地,老包凭着无人比拟的才干,成功设计和指挥了即将颠覆的军列抢险救援,受到军委通令嘉奖。同时,他自己以一流的电报技术参与其中救援,我妈那天夜里正巧也当班,赶上了人生中工作最紧张忙碌的一夜,同样功不可没,受到表彰。我师傅他们那天半夜护送我爸奔赴重要岗位,与狼群搏斗,也有功。但救援死伤人数保密。
看完后,我把信又给孔看。
人民日报登没登救援死伤人数?我问大奶。
哪里会登这些嘛,连军列二字都没提,需要保密。报上登的那篇长消息,写的是中国西南地区科技创新惊天之举,不怕牺牲敢于战斗和重大贡献。大奶说。
那还不等于没写。我说。
不一样,我父亲他们那些人说,知情者一看就懂文章的份量。大奶说。
国外会不会看出什么?孔说。
肯定会,但只能猜测。军委来的人在医院对我父亲说,帝修反一直在密切关注西昌那一片深山里的动静,你们千万别对其他人说。大奶说。
看表情,大奶本不想对我和孔说这些,而他带来那一大网兜东西,有不少他母亲为他弄的好吃的,我们三人则可以同享,其中就有他偷父亲的几桶好烟。那是用烟斗抽的烟丝,装满了茶缸大小的圆纸桶,也可以自己用纸卷了抽。我和孔没烟票买烟,从家里带来的烟早已抽完,大奶分给了我和大奶一人两桶。他虽不抽烟,但自己留了一桶。孔一接过烟就忙撕开封皮,里面的烟丝金黄喷香。
窗外楼上传来了校花发出来的阵阵笑声,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带着青春美丽感和京剧嗓音穿透力。我禁不住一下站起来,朝窗外对面楼上看去,但只闻笑声不见人。不远处伙房炒回锅肉的乡味飘进了破窗,孔可能早已饿慌了,撕下一张作业本上的纸,急着裹起烟来。在知青语言中,有一句叫饱吃冰糖饿吃烟,意思是吃冰糖消饱胀,抽烟能止饥饿。大奶看着孔抓烟丝的动作,好像忽又舍不得宝贵的烟丝起来。校花依然在一声声笑着,她为何而笑,在对谁而笑,我坐回床边,抱着吉他一句一句地练习弹唱我听说我的爱人流浪到台北。
我恍然感到,知青生活仿佛已走进练习爱情寻找所爱的苦闷荒野。
第十二章 校花被几个男人摁在地上扒光
第十二章 校花被几个男人摁在地上扒光
农场的千亩水稻,开镰不久进入梅雨季节,我们每天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全是雨水和汗水,一脸一身都是稀泥巴,眼睫毛上也成天挂着脏东西。最紧张的日子里,一日三餐都在到田里吃,哨声一响就狼吞虎咽,然后躺在雨淋淋的稻草堆上抽烟,不一会冷得发抖,赶紧干起来。
每到晚上,孔就跑到楼上的老知青屋里去,不时发出被捉弄的喊叫声。大奶没事就倒在床上吹口琴,每一吹起我们儿时唱的那支《不忘阶级苦》,外面远处就有人跟着哼唱。大奶已知道他离开的那些天,我和孔跟雷巴那帮男女知青之间所发生的种种不快,但跟我一样,不清楚孔跟那几个女知青之间出了什么事,不管怎样问,孔都闭口不谈,只说到时候再告诉我俩。吹口琴的大奶也怀有心事,他父亲的事,可能也包括他母亲的什么事。没人可以谈心,我独自来到山坡上练一会功,然后抱着西瓜的吉他弹知青歌曲,打发时光。夜里,孔还没回来,屋里也不见大奶,我望着窗前的油灯胡思乱想,最后只想校花。我不敢爱谁,更不敢爱她,但因为那颗纽扣,我已连着许多天梦见她,更因为那天她忽然现身却又不来看我,我就已经想她想得不行。然而想来想去,不管是儿时的校花还是长大的校花,我好像根本就没啥好想的,但在农村的夜里,任何一个知青都会鬼使神差地想起一个女人来,并且好像爱上她已经多年。
她记得钮扣吗?给她写封信倾吐一番该不成问题吧?
想好以后,我趴在箱子上,铺开信纸拿起笔来,心里立即涌起一股热流。那可能是一个戴罪立功的士兵,临上阵前有千言万语要说出来的那股热流,也可能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哀的那种热流。在信中,我先把自己抛出来,说自己是个历史的罪人,身上有多少修正主义流毒,再批判反省一番,发誓诅咒一番,保证要甩开膀子大干一番社会主义,彻底改造世界观。又写再见吧金色的学生时代,那战斗的岁月。别了荒凉的家园,埋葬火红的青春。
写来写去,字老是写不好看,也不大容易看懂。
第二天早上又下起雨来,全农场一时出不了工。听见雷巴在对面楼上跟人说,他马上要赶马车去公社办事,我忙把信交给孔,让他出面去转托雷巴把信扔进公社门口的信箱。不想就差多叮嘱孔一句话,结果他交完信回来说,他把信是谁写的告诉了雷巴。怪孔已无用,怪自己也来不及。就像担心的那样,只过了一会,雷巴就来到我窗前,大叫了一声包谷杆,我从床边慢慢站起来,看他眼看干什么。对面楼上好几个男女知青正站在栏杆里,静静地望着我的窗口。雷巴拿着那封信看了下信封,接着对窗户里的我说:
你这个瓜批,校花离得又不远,两个钟头的路,写信多没劲!
你不帮忙交就算了。我说,孔和大奶都从床边站起来看着窗外的雷巴。
你鸡八太小气了,我先去公社,正好还要去校花生产队办事,帮你当面交给她,这总该对了嘛?雷巴说。
你也认识她?我说。
全公社最漂亮的操妹,哪个不认识?哪个又不想上?他说。
雷巴说这话时,脸上现出一种别有滋味的怪笑,我的脸上立即发起烫来。不管是在生产队还是在农场当知青,凡是想有点好表现的知青,没谁会公开耍女朋友,充其量只敢偷偷摸摸地耍。但雷巴对我给校花写信,却好像在故意大声要说破什么,特别是哪个又不想上校花那一句,已是十分露骨。说完这些,雷巴冒雨走了,我一生中第一次给一个女人写的信被带走了,写信时的那种神圣感很快变成干了什么勾当的心情。我知道,虽说那种恐慌是自己的事,但我更怕吓着了校花。
我的心里跟天气一样阴雨绵绵,还夹杂着丝丝寒意。孔看出了这点,自言自语地自责了几句,脸色不大好看。大房子里出不了工的知青们,全都在各玩各的,聊天下棋打扑克,吹拉弹唱举哑铃,干什么的都有。内心不安的孔又裹起烟来,动作熟练麻利,转眼就卷好一支,为表欠意先递给了我。用烟丝手工卷烟想裹多大都行,孔裹的要比卖的香烟长一些,也粗许多,一头大一头小,扯掉大头端拧紧封口的纸尖,倒放起来就像一个尖塔。或许是为了进一步表示愧疚,孔点燃自己的烟后,对我和大奶,主要是对我,讲起了他从老知青那里听来的一些事。
自然是关于校花的。
孔说,校花下乡一年多,早已是个威风八面的女知青。明里暗里去找她耍朋友的知青,全公社五个大队十四个小队到处都有,还有外公社的,但她一概拒绝,只跟追求者保持一般关系。时间一长,有的知青不甘心,跑去找她挑事骚皮,有的还想对她下手。结果,没想到她会武打,把惹她的人打得再也不敢去找她,后来大家才晓得她是成都京剧团出来的,从小就练过。她跟公社当官的关系好,公社领导也看好她,帮她扎起,去年还隐瞒下乡时间年限,破例推荐她参军,但最后政审没通过,说是她母亲有历史问题,她父亲丢过一支手枪,问题更大。
我插话问孔,那么多人怕校花,她又敢那么凶,是不是她哥哥在帮她?
孔说,我正要说她那个哥哥。我们三个从小都见过她哥,小个子,不爱说话,只是斗鸡有点凶,雷巴都斗不过他。但他下乡当知青,干活就不行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早先做活路的时候,队长只能把他安排到跟老妈子一起干轻松的,像什么锄锄草啊,松松土啊。后来的新知青干一天都能挣十工分,他一个老知青只能挣几分。但他野起来比任何人都不要命,几次越境去缅甸都没成功,所以知底细的老知青都不敢惹他。
我又插话问,就他那个样子,我在马道还见过他一面,是不是真敢去什么缅甸哦?
孔说,这个我也不晓得,楼上那些知青东说西说,好象也说不清楚。
我说,插队知青首先要会自己做饭才行,他恐怕连他妹妹都不如,从小就看不出有出息。
孔说,这点你说对了。楼上的几个女知青说,几个月前,有几个外公社的知青,大概下乡没两年,跟校花她哥因为赌钱输凶了,又输不起,就找她哥还钱,一直追到了校花的队上。那天,她哥的确就在她屋里,刚吃完饭正要离去,就遇上了那几个知青。他们人人手提菜刀,扬言眼是拿不回一部分钱,就刀不留人。校花她哥哪里是对手,根本就不敢说话,趁校花队上的另几个男知青和一些农民出面解围,就赶忙溜了。那几个知青发现后,就一直追到火车站,校花和队上的一些人也跟了去。几个要钱的知青晚了一步,追到火车站时,校花他哥刚好跳上了一躺过路的货车。几个外地知青无法,扭头就找校花要人,要不就帮她哥出钱也行,否则就怎么样。校花一个女的,更惹不起对方,但又交不出人拿不出钱,于是那几个知青就把她扭住,按倒地上脱衣服。刚脱到只剩下一条内裤和一条胸带,其他人赶来了。校花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几掌就把对方几人推开,跳起来一闪身就从队上其他人手上扯过一根扁担。她向对方说,老子看你们可怜,一直让你们,你们得寸进尺,敢把老子衣服垮了。妈的批。老子现在不认黄了,你们几个虾子一个也不准走,跟老子马上过招!
孔说到这里没了话,我以为他想卖点关子,但一追问,他说楼上的女知青也没讲完,真不知道后面的事。不想大奶说了话:
我没事跑到西瓜屋里玩,也听他讲了这件事。西瓜说,后来,就在火车站下面那一小块平地上,十几个校花队上的知青农民亲眼目睹了校花独自一人打对方四人。整个过程就是她一根扁担打四个提菜刀的男知青,打了十多分钟,没一人帮忙,也不能帮,不需要帮。结果是那四个男知青全被砍翻,弄到公社医院一看,两个头上缝了十多针,另两个被打断手和腿,粉碎性骨折。
校花呢?没事?孔说。
她只是打的时候,胸带断了,那两个东西甩来甩去,被在场的人看安逸了。大奶说。
大奶可能不想有辱自己的别名,偏偏不直说校花那两个奶奶。
第十三章 高原古城的诗歌朗诵会
第十三章 高原古城的诗歌朗诵会
星期天,农场的马车要去高原古城买化肥,场长叫我去帮忙。
天不见亮上路,中午时分才到城里。趁马车师傅装货的当口,我去了县城书店。正在翻看一本诗集时,旁边有个素不相识的中年人问我是不是喜欢文学。没说几句话,我明白了对方是县文化馆馆长。分手时,他给我一张盖着印的通知单,要我自己填一下姓名。返回农场后,我模仿别人的笔迹在通知单左上方印的同志两字前面的空白处,填上我的名字,然后找到场长请假。
看嘛,县文化馆要我去开会,好麻烦嘛。我说。
场长反复认真地看那张油印的通知书,我忽然担心万一被他看出什么破绽,伸手就想要回通知单,但他头也不抬紧抓着不送手,用非同小可的口气说:
不得了啊,了不得啊!
算了嘛,我不去就是了。我说,抖着手又去夺通知单,惟恐留下把柄被场长捏着。
不想他猛然抬头打量着我,用更加意外的浑厚中音叫道:
不去怎么行?去,要去!太好了,你去县里开诗歌朗颂会,这是我们整个农场的光荣,我要派马车专门送你去!
说着伸出手来跟我握了又握,把我吓得出不了气,那劲头就像我一下子成了他的领导。
几天后,场长果真派马车把我送到进古城。下车后,马车师傅说他先回农场,第二天下午开完朗颂会再来县文化馆接我。还说这是场长安排好了的。送走了马车师傅,我穿过街道,走进工农兵商场,去找那个在马道商店呆过一阵的胡涂。说不定,那个胡涂真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