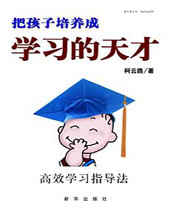失火的天堂 1046-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秦非往办公厅外面就走。宝鹃伸手一把拉住他:“你要去哪儿?”
“去找出那个魔鬼来!”秦非咬牙说:“我要把他找出来!在他继续摧毁别的孩子以 前,我要把他从人群里揪出来,我要让他付出代价!我要送他进法院!这种人,应该处 以极刑,碎尸万段!”
“我看,”章主任拦住了他。“今天大家都累了,医院里还有上千个病人呢!不如大 家都休息一下,说不定等会儿,那父母会出现,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你知道吗? ”秦非瞪大眼睛说:“这孩子身上,绝不可能有”合理的解释“!每个孩子的生命中,都可 能会碰到一两件意外,但,不可能碰到一百件意外!你们没有目睹那孩子全身冒烟的在 街上狂奔,没有听到她惊恐的呼叫魔鬼… ”
“对了!”俞大夫打断了秦非。“如果要彻底检查这孩子,我们还需要一个精神科的 大夫!”
秦非住了口,大家彼此注视着。在医院里,你永远可以发现一些奇怪的病例,但是, 从没有一个病例,像这一刻这样震撼了这些医生们。
豌豆花在第二天的黄昏时才清醒过来。
睁开眼睛,她看到的是白白的墙,白白的床单,白白的天花板,白白的橱柜… … 一切都是白。她有些恍惚,一切都是白,白色,她最喜欢白色,书本里说过,白色代表 纯洁。她怎么会到了这个白色世界里来了呢?她闪动着睫毛,低语了一句:“天堂!这 就是天堂了!”
她的声音,惊动了守在床边的宝鹃。她立刻仆下身子去,望着那孩子。豌豆花的头 发,已被修剪得很短很短,像个理了平头的小男生,后颈上和肩上,都包扎着绷带,手 腕上正在做静脉注射,床边吊着葡萄糖和生理食盐水的瓶子,腿上、腰上,到处都贴了 纱布。她看来好凄惨,但她那洗净了的脸庞,却清秀得出奇,而现在,当她低语:“天 堂,这就是天堂了!”的时候,她的声音轻柔得像涓涓溪流,如水,如歌,如低低吹过的 柔风。而那对睁开的眼睛,由于并不十分清醒,看起来蒙蒙然、雾雾然。她那小巧玲珑 的嘴角,竟涌出一朵微笑,一朵梦似的微笑,使她整个脸庞都绽放出光采来。宝鹃呆住 了,第一次,她发现这女孩的美丽。即使她如此狼狈,如此遍体鳞伤,她仍然美丽,美 丽得让人惊奇,让人惊叹!她俯头凝视她,伸手握住了她放在棉被外的手,轻声的问: “你醒了吗?”
豌豆花怔了怔,睫毛连续的闪了闪,她定睛去看宝鹃,真的醒了过来。
“我在哪里呢?”她低声问。
“医院。”宝鹃说:“这里是医院。”
“哦!”
豌豆花转动眼珠,有些明白了。她再静静的躺了一会儿,努力去追忆发生过的事。 火、燃烧的头发、奔跑、厨房…
记忆从后面往前追。鲁森尧!魔鬼!小流浪… 她倏然从床上挺起身子,手一带, 差点扯翻了盐水瓶。宝鹃慌忙用双手压着她,急促的说:“别动!别动!你正在打针呢! 你知道你受到很重的灼伤,引起了脱水现象,所以,你必须吊盐水!别动!当心打翻了 瓶子!”
豌豆花注视着宝鹃,多温柔的声音呀,多温柔的眼光呀!
多温柔的面貌呀!多温柔的女人呀!那白色的护士装,那白色的护士帽… 她心里 叹口气,神思又有些恍惚。天堂!那握着自己的,温柔而女性的手,一定来自天堂。自 从玉兰妈妈去世后,自己从没有接触过这么温柔的女性的手!
有人在敲门,豌豆花转开视线,才发现自己独占了一间小小的病房。房门开了,秦 非走了进来。豌豆花轻蹙了一下眉峰,记忆中有这张脸;是了!她想起来了!那脱下西 装外衣来包裹她,来救助她的人!现在,他也穿着一身白衣服,白色的罩袍。哦!他也 来自天堂!
“怎样?”宝鹃回头问:“打听出结果来了吗?”
“一点点。”秦非说,声音里有着压抑的愤怒。“有个姓曹的老头说,那人姓鲁,大 家都叫他老鲁!至于名字,没人叫得出来,才搬到松山两个月,昨天半夜,他就逃走了! 我去找了房东… ”他蓦的住口,望着床上已清醒的豌豆花。
豌豆花也注视着他,她已经完全清醒了。她的眼睛又清澈,又清盈,又清亮… … 里面闪耀着深刻的悲哀。
“你去了我家?”她问:“你看到小流浪了吗?”
“小流浪?”秦非怔着。
“我的狗。”豌豆花喉中哽了哽,泪水涌上来,淹没了那黑亮的眼珠。“它还好小, 只有半岁,它不知道自己那么小,它想保护我… ”她呜咽着,没秩序的诉说着:“我… 我什么都依他了,他… 他不该杀了小流浪!我只有小流浪,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小流 浪… 他杀了小流浪!他… 他是魔鬼!他杀了小流浪!”
秦非在床前坐下了,一瞬也不瞬的盯着豌豆花。
“哦,原来那就是小流浪,”他轻柔的说:“我和房东太已经把它埋了。现在,你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你的事呢?我今天去了松山区公所,查不到你的户籍,你们才搬来, 居然没有报流动户口。”
豌豆花双眼注视着天花板,似乎在努力集中自己的思想。
泪痕已干,那眼睛开始燃烧起来,像两道火炬。秦非和宝鹃相对注视了一眼,都发 现了这孩子奇特的美。那双眸忽而清盈如水,忽而又炯炯如火。
“他连搬了三次家。”她幽幽的说:“我想,他是故意不报户口的。”
“你指谁?姓鲁的?他是你爸爸吗?”
“我爸爸… ”她清清楚楚的说:“我爸爸在我五岁那年就死了!”
“哦!”秦非盯住她:“说出来!说出你所有的故事来!只要是你知道的,只要是你 记得的!说出来!”
说出来!多痛快的事啊!把一切说出来!她的耻辱,她的悲愤,她的痛苦,她的恶 运… 如果能都说出来!她的眼光从天花板上落到秦非身上:那来自天堂的男人!她再 看宝鹃:那来自天堂的女人!于是,她说了!
她说了!她什么都说了!杨腾、玉兰妈妈、光宗、光美、煤矿爆炸、乌日乡、阿婆、 玉兰再嫁、秋虹、水灾、弟妹失踪、鲁森尧认了玉兰和秋虹的尸、离开乌日乡、卖奖券、 被强暴的那夜……她说了,像洪水决堤般滔滔不绝的说了,全部都说了。包括自己是鬼、 是妖精、是扫把星。包括自己克父、克母、克弟妹、克亲人、克自己,甚至克死了小流 浪。
她足足说了两个小时。说完了“豌豆花”的一生……从她出世到她十二岁为止。
秦非和宝鹃面面相觑,这是他们这一生听过的最残忍最离奇的故事。如果不是豌豆 花就躺在他们面前,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这个故事。当他们听完,他们彼此注视,再深深 凝视着豌豆花,他们两人都在内心做了个决定:豌豆花的悲剧,必须要结束。必须要结 束!
(第一部完)
失火的天堂(2)洁舲 1一九七五年,夏天。
植物园里的荷花正在盛开着。一池绿叶翠得耀眼,如盏如盖如亭,铺在水面上。而 那娇艳欲滴的花,从绿叶中伸出了修长的嫩干,一朵朵半开的、盛开的、含苞的、欲谢 的……
全点缀在绿叶丛中。粉红色的花瓣,迎着那夏日午后的骄阳,深深浅浅,娇娇嫩嫩, 每一朵都是诗,每一朵都是画。
展牧原拿着他的摄影机,把焦点对准了一朵又一朵的荷花,不住的拍摄着。他已经 快变成拍摄荷花的专家了,就像许多画家专画荷花似的,原来,荷花是如此入画的东西。 你只要去接近了它,你就会被它迷了。因为,每一朵荷花,都有它独特的风姿和个性, 从每个不同的角度去拍摄,又有不同的美。
他看中了一朵半开的荷花,它远离了别的花丛,而孤独的开在一角静水中,颇有种 “孤芳自赏”的风韵。那花瓣是白色的,白得像天上的云,和那些粉红色的荷花又更加不 同。
他兴奋了,必须拍下这朵荷花来,可以寄给“皇冠”作封面,每年夏天,就有那么多 杂志选“荷花”来作封面!
他对准了焦距,用ZO#M镜头,推近,再推近,他要一张特写。他的眼光从镜头 中凝视着那朵花,亭亭玉立的枝干,微微摇动着:有风。他想等风吹过,他要一张清晰 的,连花瓣上的纹络都可以拍摄出来的。他的眼光从花朵移到水面上。
水面有着小小的涟漪,冒着小小的气泡,水底可能有鱼。他耐心的、悠闲的等待着。 他并不急,拍好一张照片不能急,这不是“新闻摄影”,这是“艺朮摄影”。见鬼!当初实 在该去学“艺朮摄影”的,“新闻摄影”简直是埋没他的天才……不忙,可以拍了。水面的 涟漪消散了,静止了。他呆住了,那静止的水面,有个模糊的倒影,一个女人的倒影, 戴了顶白色的草帽,穿了件白色的衣裳,旁边是朵白色的荷花。他很快的按下了快门, 拍下了这个镜头。
然后,出于本能,他把摄影机往上移,追踪着那白色倒影的本人,镜头移上去了, 找到了目标。那儿是座小桥,桥栏杆上,正斜倚着一个女人。白色的大草帽遮住了上额, 几卷发丝从草帽下飘出来,在风中轻柔的飘动,这发丝似乎是她全身一系列白色中唯一 的黑色。她穿了件白纺纱的衬衫,白软绸的圆裙,裙角也在风中摇曳,她的腿美好修长, 脚上穿着白色系着带子的高跟鞋。他把镜头从那双美好的脚上再往上移,小小的腰肢, 挺秀的胸部,脖子上系了条白纱巾,纱巾在风中轻飘飘的飘着;镜头再往上移,对准了 那张脸,ZO#M到特写。他定睛凝视,有片刻不能呼吸。
那是张无懈可击的脸!尖尖的下巴,小巧玲珑的嘴,唇线分明,弧度美好。鼻梁不 算高,却恰到好处的带着种纯东方的特质,鼻尖是小而挺直的。眼睛大而半掩,她正在 凝视水里的荷花,所以视线是下垂的,因而,那长长的密密的睫毛就美好的在眼下投下 一排阴影,半掩的眸子中有某种专注的、令人感动的温情,白草帽遮住了半边的眉毛, 另一边的眉毛整齐而斜向鬓角微飘。柔和。是的,从没见过这种柔和。
宁静。是的,从没见过这种宁静。美丽。是的,她当然是美丽的(却不能说是他没 见过的美丽),可是,在美丽以外,她这张脸孔上还有某种东西,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思索着脑中的词汇,蓦然想起两个字:高贵。是的,从来没见过的高贵。不过,不止 高贵,远不止高贵,她还有种遗世独立的飘逸,像那朵白荷花!飘逸。是的,从没见过 的飘逸……还有,还有,那神情,那若有所思的神情,带着几分迷惘,几分惆怅,几分 温柔,几分落寞……合起来竟是种说不出来的、淡档的哀伤,几乎不自觉的哀伤。老天! 她是个“奇迹”!
展牧原飞快的按了快门。偏左,再一张!偏右,再一张!
特写眼睛,再一张!特写嘴唇,再一张!头部特写,再一张!
发丝,再一张!半身,再一张!全景,再一张!那女人的睫毛扬起来了,他再ZO #M眼睛,老天!那么深邃乌黑的眼珠,蒙蒙如雾,半含忧郁半含愁……他再按快门! 拜托,看过来,对了,再一张!栽栽栽栽糟糕,快门按不下去,底片用光了。
他拿下相机,抬头看着桥上的那个女人。她推了推草帽,正对这边张望着,似乎发 现有人在偷拍她的照片了。转过身去,她离开了那栏杆,翩然欲去。不行哪!展牧原心 里在叫着,等我换胶卷呀!那女人已徐徐起步,对小桥的另一端走去了。展牧原大急, 没时间换底片了,但是,你不能放掉一个“奇迹”!
他追了上去,脖子上挂着他那最新的装配Nikon,这照相机带上ZO#M镜头, 大概有一公斤重,他背上还背了个大袋子,里面装着备用的望远镜头、标准镜头,足足 有两公斤重。
他刚刚在匆忙间,只用了ZO#M镜头,实在不够。如果这“奇迹”肯让他好好的换 各种镜头拍摄,他有把握会为这世界留下一份最动人的“完美”!
他追到了那个“奇迹”。
“喂!”他喘吁吁的开了口:“请等一下!”
那女人站住了,回眸看他。好年轻的脸庞,皮肤细嫩而白晰,估计她不过二十来岁。 那大大的眼睛,温柔而安详,刚刚那种淡档的哀伤已经消失,现在,那眸子是明亮而清 澈的,在阳光照射下,有种近乎纯稚的天真。
“有什么事吗?”她问,声音清脆悦耳。
“是这样,”他急促的招供:“我刚刚无意间拍摄了你的照片……哦,我想,我还是 先自我介绍一下。”他满口袋摸名片,糟糕,又忘了带名片出来!他摸了衬衫口袋、长裤 口袋,又去翻照相机口袋。那“奇迹”就静悄悄的看着他“表演”,眼底流露着几分好奇。 他终于胜利的叫了一声,在皮夹中翻出一张自己的名片来了,他递给她。“我姓展,很怪 的姓,对不对?不过,七侠五义里有个展昭,和我就是同宗。我叫展牧原,毕业于政大 新闻系,又在美国学新闻摄影,回国才一年多。现在在某某大学教新闻摄影,同时,也 疯狂的喜爱艺朮摄影,帮好几家杂志社拍封面……”他一口气的说着,像是在作“学历资 历报告”,说到这儿,自己也觉得有些失态。适适适是的,从没有过的失态。他停住了, 居然腼腆的笑了。
“名片上都有。”
她静静的看着他,又静静的去看那名片。展牧原,某某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名片很 简单,下面只多了地址和电话号码,事实上,他说的很多东西名片上都没有。教授,她 再抬眼打量他,笑了……
“你看来像个学生。”她说:“一点也不像教授。”
“是吗?”他也笑着,注视着她的脸庞,真想把她的笑拍摄下来。“能知道你的名字 吗?”他问。
她很认真的看看他,很认真的回答:“不能。”
他怔了怔,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一生,还没有碰过这种钉子,以至于他根本不相信 他的听觉。
“你说什么?”他再问。
“我说,我不想告诉你我的名字。”她清清楚楚的回答,字正腔圆。脸上,却依然带 着个恬静的微笑。
“哦!”他呆了两秒钟,勉强的挤出一个笑容。“你妈妈说,不能随便把名字告诉陌 生人,也不能随便和陌生人讲话。因为,这社会上坏人很多。”
她看着他,微笑着不说话。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