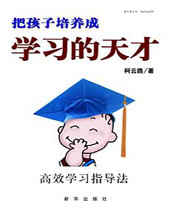迷失的病孩-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抛物线,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最标准的坐标。瞬间,我再也不厌烦我的小学数学老师了,甚至开始怀念他。
乐队停止,解下乐器开始走向台下,一些POGO的人们将啤酒洒向舞台。鼓手将鼓槌一根一根的扔向观众,引起一阵又一阵的轰动。我退缩到一个角落里,点上一只烟,看不清人们的表情。仿佛生命在悄然化为重复着疲惫的姿态,无声,像玩偶僵死的侧影。
我等待着青春在昏暗的灯光下灰飞烟灭。骤然发现,永恒中没有时间,永恒只是一瞬间。将手指间的烟头熄灭,想象着也许一切该散场了。
2
羊君终究没能逃脱物质的诱惑,离开了北京,用十七天的时间完成了结识并嫁给了一个意大利男人的全过程,而后定居罗马。她选用逃避的方式去寻求内心里的那片艺术净土,童年里的伤害不再需要艺术的解脱,因为她看淡了这个世界里的真诚。也许,只有物质能解决一个业已麻木的灵魂。
G:伤花盛开(7)
那个意大利男人大她三十岁,可以做她父亲的年龄。他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是在罗马为她举办一次画展。画展上,展览着我的那幅裸体。我不知道羊君什么时候复制了那幅画,也许她一直复制在心里。或许我也可以把她对我的那次艺术献身看作是一场善意的欺骗。和我的初衷一样,她仅仅只是想从我身上证明她童年的存在。
3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阳萌会在监狱里渡过他的下半生。
而我和田树连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知道他入狱是通过一则晚报的消息。他涉嫌参与一宗大型的毒品走私案,并在逃窜越南的路上被抓。
指正他的是程嘉禾。
他的酒吧早已倒闭,那是阳萌最后的栖身之地,而这一切随着阳萌的离去而离去。敏感之花的招牌上还有一些日光灯在闪烁,酒吧门外的宣传栏上依然贴着这个城市今冬的最新摇滚演出信息,只是门面已开始被改装成一个拉面馆了。几个兰州人穿着白大褂在里里外外的忙碌着,时常会督促着装修工人快点儿将那些摇滚演出的海报清除干净。
在这个城市里,再也没有人提到田树的摇滚音乐节。我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发在一个地下杂志上,题目叫《越乌托邦就越现实》。很多人写信骂我,说我写东西太主观太极端,还告诉我说其实中国摇滚乐环境并没有我说的那么坏,因为他们知道很多摇滚乐手可以同时泡五个妞儿,可以到三十岁时不找工作依然长得健壮,可以穿常人没见过的衣服,还说“摇滚乐有什么用,唱流行歌多好听”。
紧接着那本地下杂志也被查封了,我和几个主办杂志的朋友被请到了文保局关了一天。在反复地盘问里,我渐渐懒得回答,与那些人的谈话内容在我心目中已经生成了固定模式。我们并不想反抗什么,只是我们的思想需要寻求表达。
4
乳房乐队寄出的小样被某音乐节的主办方否决了。但后来乳房乐队还是签约了,真真实实,法国一家唱片公司正在筹划着他们乐队的专辑。
签约的那天晚上田树带着一大群朋友在夜市上喝酒,老板抬了两箱啤酒来,但不够。喝到最后所有乐手都哭了。
但田树一直沉默。我知道签约并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他只是在帮助他的乐队完成一个梦想。买了一包又一包的烟,他一支也没有抽。这一刻,只有田树是清醒着的。
肖强在酒桌旁边吻着荀沫,我转过脸去,想象着又一个单纯气泡的破灭。
我的脑海里再次闪过很多很多的人和童年往事,但仅仅只是闪过,我再也记不住它们。
在太阳升起之前,他们的庆祝仪式即将结束。我再次相信,哥特的华丽只不过是生命里一场美丽的厄运。
我拉着田树的手,告诉他什么是旋转的墓地。田树依然只是笑,笑得很诡异。
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发现大家都是睡在街道上的,清洁工人扫地的沙沙声很动听。对街已经有人开始忙碌着早点摊的摆设,也许对于他们来说,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5
又回来了,我迫不及待地奔到那面墙前。意外的,我的字还在,甚至还有人附和地在旁边涂上了一些图画,有啤酒瓶,有无政府主义标志。我在他们的旁边接着写道:
你阳台上是一棵生命树。开放的不是花,而是欲望。
在每一个季节,它都在枯萎。在属于它的轨迹里,让世界静寂至死。
你也知道在这个哥特的时代,世界存在着太多的肮脏与不确定。真实的只有欺骗与自我主义。狭隘,无知,愚昧,懦弱,自私,暗潮以及被毁灭的城堡。
你唯一栖身之地被女人改装成了婊子牌坊,并用你的电脑视频拉客。你轻轻的过去摸了把那女人的脸,然后将身上所有的钞票丢在了她的身上。她说怎么这么少?
你低下了头,想像着这个冬季应再也没有什么可收获的了,于是非常自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进入那个迷宫要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
女子开始收拾东西了,她想出门去干活,出门时不经意的踢倒了你阳台上那盆花。你瞬间张大了嘴吧,可是没有说出任何话来。你心想,也许上辈子欠她的。
后来你走到阳台上,用口水在那块玻璃上写字:美女的下体很松散。再后来,你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同时玻璃中的你也破碎了。
你一直在努力的寻找你的新体。其实我就是你的新体。——11月11日,冬天,依然是武汉。
6
十二月的时候,苏娅来到了武汉,她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们的再次见面也没有浪漫的情节。那天阳光不错,但是有风,我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带着她朝我租住的那个小楼走。看着地上两个移动着的影子,我能分辨出头发散乱的那个是我。这注定又是一场光荣而可笑的爱情葬礼。
在一个有些寒冷的上午,邮递员送来了一个包裹。那上面没有寄件人的任何信息,可我知道里面一定是牵扯着我曾经的某个女人,因此我一直不敢也不想去开启它。我带着那个包裹走过了很多条街,明亮的、阴暗的、潮湿的,但我就是不打开它。
苏娅不只一次地问我包裹是谁寄来的?你为什么不打开?我的回答只有沉默。我以为沉默可以让我一辈子不揭晓真相。
G:伤花盛开(8)
但有一天当我和苏娅路过江边的轮渡去河对岸的时候,一个乞丐过来硬扯着我的衣服乞讨,并撕破了我的包裹。我看到里面露出刺眼的红色,那是一双红鞋子。
瞬间,苏娅放开我的手,向前奔跑。
还是没能逃过夏天,苏娅就脱离了我。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她一直把我当别人的替代品,她用伤害我的方式去刺激别人。她想在所有人身上找回她十六岁就已失去的一切。她只是固执地按她的方式生活,感情不再是她停留的理由,谁限制了她的自由,她就会决然的走开。
秋天,我去了那条种着高大梧桐树的马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弄那些不太熟悉的拍摄设备,终于开始拍了。三分钟以后,镜头中映射着一具血淋淋的凌乱身体以及散乱在马路中间的一双红鞋子,只留下大片大片梧桐树叶飘落在身体上以及救护车尖叫的声响。
H:生命之树(1)
没有生活中的绝望,
就没有生活中的爱。
If there is no despair ;
then no love in the life
一 。关于自己
1
写完这本文字的时候,离我的二十三岁只差一天。
我并没有刻意选择这样一个日子结束,只是纯粹的巧合,就像我写完曾经被我烧掉的那本小说时刚好是二十岁的生日一样。三年的时间值得缅怀的东西很多,可是我已经没有更多的力量去记录下它们。
我再次想起了我的青春,我的那些关于记忆的碎片,但似乎心里已不再有激情,对很多事情开始变得淡然而冷漠。于是在无数个深夜,我都是独自坐在电脑前抽烟,喝啤酒,然后大声地放着摇滚乐直到天亮。
在网络这个虚幻的世界里,我一直潜付着存在。但我不知道一个虚幻世界里存活的人,在没有爱情的时候会否还相信欲望。
我一直不太习惯这个喧嚣甚至浮噪的时代,所以一直也在努力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呐喊方式,但我又总是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迷失在无边的焦虑中,常常在潮水的人群里寻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我是一个有着浓重童年阴影的孩子。在我出生的那一刻,已遭遇了一场生命的劫难。童谣的意义,是儿时在农田里快乐的奔跑,在物质与文化的滞后中成长着自己注定被固封了的身体。所以在后来的每一个树叶落地的季节,我都不由自主的陷入童年成长的河流及迷失在时光里的残灰余烬。
随着青春的远去,家园的概念也成为一道残酷的空白。几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家,不因别的,只是家对于我来说只是作为一种童年文化片痕,它不再是我的最终归属。
好孩子注定是属于远方的,故乡就是永远回不去的家园。
2
在成长的废墟里面,我是一个被隐藏的人,无数次地被击垮。
尽管存在着的时候,我努力而虚伪地表现着自己的坚强与勇敢,但在时光车轮的前进中,我却看不到自己影子的移动。终于我明白,我只是一个娇嫩而无能的人。我跑不过青春,跑不过苍老。我的头发剪了一次又一次,可它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固执地遮住了我并不明亮甚至有些渴望的眼睛。从我眼里深处,你可以发现对于希望的乞求,那些深层的骨子深处的脆弱永远无法抵挡。
在荒漠里用一种荒谬的方式旅行,生活中不再有具有真正意义的信仰,这让我很痛苦。即使跪倒在教堂里,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内心里的虔诚与清静。
为什么一切都变得这样虚伪呢?
当一个朋克乐手在舞台上像小丑一样跳着低级的舞蹈时,我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的肤浅与人们审美意识的世俗。为什么非要选择哗众取宠的方式?为什么不能像一个孩子那样天真?为什么摇滚成了一种消极时尚而不是一种文化?
在每一个慢慢转换的季节里,我都去酒吧看各种各样的摇滚演出。偶尔也会带着自己的乐队。
当我们乐队在一些商场门口唱着自己听都没听过的流行歌曲时,内心里的那种违背意识也变成了一道浅浅地对于金钱的渴望,曾经坚持的理想也在瞬间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
不知从何时起,我知道,人最本质的追求是生活。而生活不再是苟活,不再是得过且过,而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
其实生活就像一部记录片。记录着热血与青春,幻想与躁动,爱与被爱,性与政治。应该大声呐喊,不再用一种形式主义去标榜潜藏心底的爱。
3
我的左肩缝着一个切·格瓦拉的头像。
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所以我们的英雄情结只能是在胸口里游荡。理想主义在茫然盛放过后得到的依然只是枯萎,一切关于解构的思想都破碎在了我啤酒喝多后的桌子下面。
常常是夜里三点,你可以在某个夜市摊上看到我和一大群做摇滚或写作的朋友在那里大声地说着话,桌面上堆放着各种各样的空啤酒瓶。
也只有在啤酒喝到五六瓶的时候,我们才清醒地知道城市的终极是毁灭,人生的终极是死亡。当我们明白我们得了集体阳痿症的时候,这个时代早已精尽人亡。摇滚不再重要,写作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活出自己。
如果平庸无法避免,冷静或许真的能成为美德。与自甘消沉一样,物质欲望的澎湃已成了这个社会少女的破贞美梦。
现实中的自己一直很安静。从小缺钙,长大缺爱。
很多朋友常常告诉我说,你开始变得阳光了,开朗了,不再是阴郁的笑。
或许他们不会知道,并不是我变得阳光,而是我对很多事情更淡泊了,于是在时间的沉淀中,它们成了一种用微笑去抵抗的消极思想。
我不再去追求一件事情的终极意义,因为我知道那样只会让人更绝望。更何况意义之花在它们那冷峻清寒的音河中却总是萎缩着无法盛放。所以我宁愿让自己麻木地快乐着。
4
遗忘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并没有必要试图那样强求自己。
在垂死太阳王国的内部,青春成了一场葬礼。惘然地进入一次生命的迷宫,让一个灵魂的捕获者在玻璃上绘画人生的旅程。就像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玛朵尔之颂》,作者在散文诗一开头便告诫读者:亲爱的读者,别再前进,Moldoror将如水溶溺蜜糖般,舔噬你的灵魂。
H:生命之树(2)
是的,别再前进。生命将带你接近永恒的死亡。
当我将一些记忆变成文字的时候,我发现它们不但没有超越相反是远离了我心目中那些关于记忆的本质。
它们像一场垃圾电影一样缠绕着我,让我无法不在回忆中沉痛。然后听着幻想绽放的声响,疯狂地暴露自己的无知与缺陷。
还记得,流着热泪在深夜中茫然地奔跑在校园里,想起一场温暖,然后焚烧自己的梦想。在一切甜蜜的疯狂的都远去的今天,记忆只是一种本能。
在这样一个时代,有物质的人都去娶了人工美女,有思想的人都进了监狱,有自我主义的人都进了政治圈。也许只有我这种光脚的波希米亚小孩子才会再去谈论着什么乌托邦与终极自由。
5
从大二开始,我组建过无数个乐队。
但每一个乐队从成立到最后解散都很少有真正的演出。所以它们更像暗室里的花朵一样,绽放着自己对生命的热情。这中间进进出出过这些乐队的乐手如今我已记不清名字,但我要感谢各个乐手以及支持过我的人。
现在又有一支乐队,并有些成员不固定的各种自由组合乐团。
葵花是一种艺术和希望的象征。朵朵葵花向太阳,一种特有的政治意味。
这是我离开大学后组的一支乐队,真正的地下乐队。乐手都是较职业化的,设备也在不断更新。偶尔会在酒吧或是其他地方演出,但我们是在真正的静下心来做我们喜欢的音乐。不受风格或流派限制,尽管我个人更偏向于硬摇滚或是GRUNGE、OLDSCHOOL、POSTPUNK、实验摇滚、噪音摇滚。
乐队能坚持多久我真的无法预料,因为经历了很多事后,我开始变得更加现实。但对于我来说,解散不再意味着放弃。我的琴头上贴着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