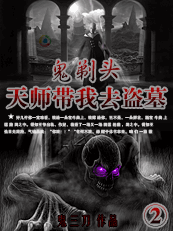带我去阿尔泰(全本)-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安静一定会像他的妻子一样,扑到他的身上,为他伤心,为他流泪,这就足够了,做人不能太贪心。
他真的不贪心,只是理想太多,从小就是这样,十来岁时的理想是开火车,跑京广线,轰隆隆从首都一气直达广州;二十岁时的理想是当作家,要么写一本《悲惨世界》那样的巨著,要么写一堆杨朔和秦牧那样的散文;三十岁时的理想是当藏书家……现在,他的理想变了,变得简单了,只要死在安静的前头就行,不然,安静没了,剩下自己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受不了,别说真的那样,就是让他想一想,也足以令他不寒而栗的了。
一想到这,他就特想亲她一下,甚至还有了做爱的冲动,可惜,这冲动来的不是时候。在化疗室接待他的是一个年过半百的留着李时珍式胡子的老家伙,姓徐。万喜良每次跟他攀谈,他都说哦,小伙子,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万喜良以为他对自己的话题总是很好奇,所以才这么说,后来才知道,他是半个聋子,起码拿耳朵当摆设的时候居多。
徐医生酷爱的是X光片,而不是人。据说,根据X光片他能判断出对方的年龄、身高、体重、脾气禀性什么的,可跟人打交道就笨拙的多了,他说人太复杂,年轻时,他的一个朋友结婚三年也没生育,急,找了很多的名医,也不见效,他实在不愿看到朋友这么辛苦,就帮了一下忙,只帮了一下就让朋友的妻子有了身孕,结果朋友不但不感激他,反而跟他反目为仇,其他人也谴责他不道德,这让他悲痛欲绝,从此离群索居,独身了大半辈子。
许是万喜良对他比较友好的缘故吧,所以才偶而会跟万喜良说上一两句话,给万喜良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是,看这张光片,这就是你,这是最本质的你,甚至比你本人还要真实。万喜良就久久地凝视着自己的 X光片,扪心自问:是这个只有内脏器官和骨骼的我真实,还是有鼻子有眼有表情的我真实?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徐医生所说的真实的自己,有一天贸然走到街上去,不吓倒一片才怪。
今天我要让你领略一下什么叫美,什么叫迷人,这天,从化疗室一回来,安静就对万喜良说。
她把她全套的化妆装备都倒腾出来,一一摆在桌上。这个是睫毛卷,知道吗?这个是眼影,这个是唇膏……她一边讲解着,一边开始操作。她的架势很自然地让万喜良想到了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只是讲解员一般都是站着的,而她是坐着的,且双脚跨在桌下的横杠上。安静先是描画眼线,然后上睫毛膏,然后拿着粉饼沿着双颊自下而上地扑上一层粉,然后才是腮红。整个过程烦琐而又漫长,漫长得几乎用掉了唐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的时间,方初具规模。万喜良以为总可以告一段落了,她却说还要精加工。因为角度的问题,他只能看到安静的侧面,侧面的她让他觉得很陌生。
万喜良觉得女孩子化妆应该妩媚和娇羞才对,当然还少不了一种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安静却不是这样,怎么形容她呢,她似乎更像即将爆发的火山口,随时都会有岩浆喷发出来。
化妆看来是个体力活,比想象中的劳动强度大多了,半截,她站起来还伸了好几个懒腰,试着做些医生叫她做的运动,然后,接着忙。她说,化妆时没有镜子照,质量不可避免地要打些折扣。
他知道她是在埋怨他,因为他把所有的镜子都涂上了油漆。
谢天谢地,万喜良几乎等到最后一个皇帝退了位,安静才化好妆,婀娜多姿地转过身来,面对着他问道效果如何?万喜良的表情简直可以用惊艳来形容,他坐起来,张大了嘴巴,眼球不断地调整着焦距,好半天才用英语说了句天哪。安静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她看出此时此刻的万喜良已经完全沉溺在她的迷蒙的眼神里不能自拔。她耳语似的问道美不美?他说美。她又问迷人吗?对万喜良来说,似乎这时候周围的一切都远离他而去,包括时间和空间,他的眼里只有她的那张俏丽的脸,你真是迷死了人,他说。
她的身子倾向他,离得很近很近,知道就好,她说,说得特铿锵。不过,万喜良的心里还是有点怪怪的感觉,他犹犹豫豫地问道,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她说NO。他不得不承认,虽然在病中,化过妆的她依然魅力无限,脖子依然挺拔,胸乳依然浑圆,腰身依然具有曲线美,很容易招惹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意志薄弱的男人犯作风问题,以前他总把这样的女人叫做“公害。”他问她突然打扮得如此光彩照人,是何居心,总该有个原因吧?她却说原因你知道。他一脸的疑惑,原因我知道?她说是的。他突然想起来他在化疗室里夸过一个病友的女儿长得又美又迷人——原来问题的症结在这里,面前所有的一切的起源就是因为那句话。
他想说她是个小气鬼,可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你太女人了,什么美,什么迷人,我是随便说说的,我甚至连那个女孩的模样都没看清。你确定?她说。他说我确定。你真的确定?她又凿补了一句。他说我真的确定,去化疗的时候我的眼镜忘了戴了。
她打了他一巴掌,说我还以为你移情别恋了呢,让我担心了半天。他说怎么可能。你这个大坏蛋,安静骂了一句,手臂紧紧地箍住了他的腰,脸颊贴在他的后背上婆娑着……
都怪你,害我一通乔装打扮,像个小丑一样,她说。
这样能让人肾上腺上升的小丑也实属难得,他说。
渐渐的,温情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欲望,安静急切地拉起万喜良的睡衣睡裤,他要帮忙,她不让,我忙得过来,她说。终于她把他的毛重都减去了。他捂着要害部位,问道你呢?我好办,她先拿两把椅子顶在了门上,又把自己的牛仔夹克草草地绑在腰际,这样一来,有人来她用被子把万喜良一蒙,而自己仍旧衣衫齐整,避免了让人家捉奸在床的尴尬。
他们搂在一起的时候,他身上有一种浓浓的福尔马林的味道,而这味道她身上也有,不过,已经顾不得这个了,他们迷失了。
她亲了亲他的额,问道这是谁的?
他说是你的。
她又亲了亲他的唇,问道这呢,是谁的?
他说也是你的。
接着,按照顺序,她依次又吻了他的喉结、胸口、肚脐以及其他说不出口的零部件,亲一下,问一句,这是谁的或那是谁的。
在她亲过的位置上,都能清晰地留下一个红色的唇印,那种红通常被叫做玫瑰红。
她的吻很柔,像漂浮的云彩落在裸露的皮肤上,而他却觉得火辣辣的烫,仿佛是篝火晚会上飞溅出来的火花灼得慌,一阵红潮从他的耳后蔓延到他的脸上、颈上和胸上,连他沉睡了许久的小弟弟也苏醒过来,一个劲地伸懒腰。直到她把他从头吻到脚,才抬起头来,如释重负般地说好了,有这么多属于我的地方,足够了,余下的谁要拿走就拿走。万喜良差一点没笑掉大牙,经过你这么一番洗礼之后,我身上还能有什么余下的东西?安静一本正经地说有啊,新陈代谢掉的那些,比如汗液什么的。万喜良说你好慷慨呀。她说人家倒都是这样评价我。
然后,她把耳朵贴在他的胸上,倾听着他的心跳,在她听来,那心跳既像放慢了速度的爵士鼓鼓点,又像雨点拍打在铁皮屋顶的声响,她一下子湿润了,如果性感也可以用来衡量女性美的话,色咪咪的安静这时候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漂亮。
不知为什么,她总能在他身上闻到一股麦片的清香味,她对这种清香很迷恋,差不多迷恋到病态的程度。她曾偷走过他的一件浅色衬衫,晚上睡觉时就穿在身上,只为能闻到一丝他的味道。不过,这是个秘密,她一直都没有告诉过他,怕他笑话。
最让她感兴趣的,当然还是他本人。他有一颗黑痣,像黑米粒一样,不过比黑米粒稍小一点,就坐落在他的小腹上。她似乎对那颗黑痣情有独钟,一遍遍地吻它,还说它是她的小乖乖,可爱死了,简直可以做他的注册商标。万喜良故意逗她,你真的只觉得它可爱吗,那么它的邻居呢?
安静似乎很不屑地瞟了一眼他的小弟弟,说我不太喜欢它。
为什么?万喜良很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偏偏不喜欢它?
安静说它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杀气腾腾,情绪总不稳定,显然缺乏足够的修养。
它的情绪都是因你的变化而变化,万喜良声辩道,毛病在你身上,它是无辜的。
好吧,随你怎么说,我不玩了。说罢,安静就想溜掉,可惜,晚了一点。
万喜良一翻身将她压在身下,想跑,没那么容易,刚才是男生生理课,下一节该是女生的了,他说。安静把手指竖在唇边,嘘,说你听外边。外边怎么了?万喜良问道。安静一骨碌爬起来,说外边下课铃响了,借机跑掉了。
这天早晨,下了这个秋天的第一场雨,它似乎是在宣告,夏天走了。同一天,范冰冰来了。范冰冰是冒着雨来的。她打了一把伞,一双鞋的鞋尖和鞋跟都湿漉漉的,在病房的地下留下了串串脚印,那脚印怎么看怎么像锚,就是帆船上的那种锚。哦,我们的天使来了,一看见她,万喜良高兴地招呼了一声。范冰冰却说这话听起来可不大像恭维。她更喜欢他叫她是朋友。
万喜良问外面的雨下得大不大,他真的想知道。范冰冰说不大,也不小。万喜良又说不大不小的雨最容易叫人伤情。范冰冰歪着脑袋问道你不想亲眼看一看吗?安静以为她是跟他开玩笑,所以一笑置之,范冰冰却觉得自己是认真的。
安静赶紧插了一句说笑而已,他不会去的。万喜良突然说为什么不呢,我要去。安静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安抚了一下,天凉,又有风,怕你受不了。范冰冰说人就是要经风雨见世面的嘛。说完,还冲万喜良挤挤眼,万喜良会心一笑,瞬间他们就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
好吧,安静拗不过他们,只好妥协,不过,仅限十分钟。
万喜良披上毛毯,让她们把他搀到阳台上,在躺椅上躺了下来。许久没有透空气了,稀罕,虽然是淫雨绵绵,可在他看来比晴空万里、阳光明媚还令人心情舒畅。
秋雨把树叶都打落了,他说。
范冰冰说你看,还有最后一片叶子。
万喜良用手指碰了一下范冰冰的鼻子尖,调侃道不会是你悄悄画上去的吧?
当然不是,范冰冰说,因为我不是个画家。
秋天的雨就这样,总是淅淅沥沥的,多少有那么一点神秘感,很容易将人带入某种情绪当中,就像他们现在这样。
从某些方面讲,范冰冰和安静有些相象之处,就多愁善感而言,只不过范冰冰的水平是业余的,而安静绝对够得上专业了。
他们开始沉默了,开始浮想联翩了。
阴雨时,天空就显得很矮,仿佛爬到五层楼的楼顶,伸手就能够着似的。安静托着腮,望着天,突然冒出来一句,生命里的东西不是你想要就可以得到的,你能得到的只有生命给你的东西。范冰冰天真问道这是诗吗?安静摇摇头说不是诗,是小说。范冰冰觉得很经典,就记在了本子上。
乌云越来越多,浮动着,狡黠地荡来荡去着,成为视觉上最占地方的东西。安静这时候才意识到他们在露天里呆了不止十分钟了,也许是二十或三十分钟也说不定,慌忙地将万喜良送到他的床上去,盖上了被子。万喜良把护士长扣押的那些书全部赠送给了范冰冰,至于怎么跟护士长交涉,他相信安静会有办法。范冰冰临走,万喜良对她说以后你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呀?范冰冰问道。万喜良就是不说。
他是不愿给她留下一个病鸭子形象。的确,自从他躺倒以后,他的体重急遽下降,减了八公斤,瘦的像一片空空的贝壳。
一觉睡到大天亮,是万喜良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幻想,这次他终于做到了,不过,是在舒乐安定的帮助下。醒来之后,却没有发现安静,平时她总是在那里的,等着他醒,等着给他各式各样的惊喜。安静是个制造惊喜的大师,仿佛她只须眨眨眼,惊喜就会从天而降,对此,万喜良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有安静知道,制造这些惊喜损失了她多少的脑细胞。
万喜良一边把手放在额头上遮挡着阳光,一边开动脑筋判断着安静的去向,他一下子罗列出大约一百种可能性,要不是突然被李萍干扰破坏的话,他很可能还会罗列出一百零一种来。李萍说安静让她来告诉他,她在药房,要耽搁一阵子,所以他只好一个人吃早餐了。万喜良问李萍安静到药房去做什么。安静说不知道。万喜良双手合十说上帝,还是不要让我一个人吃早餐吧,一个人吃早餐是最凄凉的事情之一了。李萍说对了,安静还叫我嘱咐你,多吃点。
吃药的时候,通常是吃完早餐的一个小时之后,安静竟还没回来。以往,他们总是开展吃药比赛的,比赛谁吃药吃得快,奖品是一个吻。到目前为止,他的成绩还不错,赢的时候多,输得时候少。赢的滋味很好。如果此时此刻安静在这就好了,他想。这时候李萍又来了,催促他别忘了吃药。安静呢?他问。李萍说还没完事,完事就会来,另外,她还叫我告诉你,这次算你赢了,奖品加倍。万喜良笑了。当李萍问他安静给他的奖品是什么时,他却回答这是绝密。李萍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这个一个上午,安静始终没露面,中午,还是一样。万喜良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不过的动物了,关在笼子了,自己出不去,其他同类也不进来,除了李萍来传达安静这样或那样的指令而外。万喜良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他要去找安静,李萍要拦也拦不住,这时候安静才出现。她在主任和护士的陪同下,频频向万喜良招手致意。他发现她的脸色居然跟纸一样白,不,甚至比纸还要白。你没事吧?万喜良忧心忡忡地问道。没事,我挺好,安静笑着说。可是她的笑一点都不真诚,像是假面具上画着的那种笑。
你跟我捣鬼,万喜良说,我知道你是在跟我捣鬼。与其说是他从她身上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到不如说是他的直觉在起作用。
我没捣鬼,我只是稍微有点不舒服,安静嬉皮笑脸地说。
怎么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