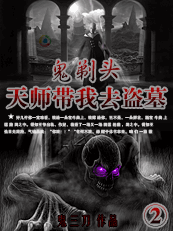带我去阿尔泰(全本)-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安静说也是,病房就仿佛是用来上演生离死别戏剧的大舞台。
接下来的几天里,万喜良试图劝她施行化疗,化被动为主动,跟病魔作顽强的斗争。可是,安静对他这一番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全然听不进去,甩打个手溜达来溜达去。他让她坐下来,听他说。她却跟孙猴子似的哪高往哪坐,一会儿是窗台上,一会儿电视上。说多了,她还会烦,说难道你非得让我饱受折磨,然后再像遭了干旱的花一样的死去?
他说我就是为了让你好好的活着嘛!
安静歪着个脑袋,说得了这个病,活着,可能吗?任凭他说得口干舌燥,她就是刀枪不入。他只好像一只飞得精疲力竭的鸟似的,收拢了无力的翅膀,停歇在一边,喘大气。他还从没见过这么顽固不化的人呢,更别说是女人了。
他只好放弃了,再也不劝她了。
不知为什么,安静这一阵子突然间变得漂亮了,不是一般的漂亮,而是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漂亮,一张鹅蛋脸,犹如含苞待放的百合,眼睛则像珍珠一样的闪亮,真让他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他甚至都不敢长久地注视她,怕电着。有一次,他对她说你真像个美丽天使啊。她说我也觉得是,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我只是个丑小鸭,不知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
他怀疑这是化妆的奇异功效。
她用毛巾使劲擦着脸,声辩说我绝对是素面朝天,天然去雕饰。还模仿着葛优的腔调说这是爱情的力量。
他取笑说你这样光彩照人,走在街上,一定能让那些帅哥们倾倒一大片,连北都找不着。
她说那好,我们就到街上去,测试一下我究竟有没有这么大的杀伤力。他们怕医生阻挠,从后门溜出去,眨眼之间就手牵着手出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
他问她他们的目的地是哪,不会是像拉兹一样到处流浪吧?她说目标是照相馆,她要照好多好多的照片,把自己最美好的面影定格下来,留给后人瞻仰。
照相的时候,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猫着,她拉他合影,他拒绝,说他对镜头敏感。
最后,好说歹说,他才答应跟她合照一张。她嘱咐摄影师照好一点,说是他们俩的情侣照。
一句话,把万喜良说得居然难为情起来,长这么大,他还从没跟女孩合过影呢,以前跟他来往的那些女孩仅限于拥抱接吻什么的,没想过要留下些永久性的纪念。安静是个例外。
摄影师一说准备,她就把头枕在他的肩膀头上,做出一副甜哥哥蜜姐姐的表情来。
一刹那,他竟砰然心动。不过,他还是吃不准自己该不该真心去爱她,这个世界太过肮脏了,只有单纯的爱情是惟一的一片净土了,千万别把它也玷污了……这么想着,他不禁将身子跟她贴得近一些,再近一些。他们两个人一派亲密无间,很有点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意思。
从此以后,安静就像上了瘾似的,一得空,便吵吵着要去照相,每次路过街头拍大头贴的地方,她都要进去拍上几张,越拍越多,越拍越来劲,到最后,竟频繁得像一个偏执狂,一天不拍问题多,两天不拍走下坡,三天不拍没法活。洗出的照片就贴在墙上,贴了整整一屋子。
他不禁替她犯起愁来,说再这么拍下去,非得把这些照片挪到中国美术馆去,才搁得下。
她说你以为我会公开去展览吗,不会的,要是搞个小沙龙什么的倒是可以考虑。
他问她准备给这个沙龙起个什么名字。
她说就叫回光返照吧。
他狠狠瞪了她一眼,提醒她要慎言,孟浪总是不明智的。
现在,每天早上,万喜良都要早起,叠好被,拉开窗帘,迎接安静来做内务大检查。
接下来,他们就到阳台上去喝他们一天中的第一杯咖啡,槐树的枝桠和树叶可以做他们的华盖。遗憾的是,咖啡只能喝速溶的了,这里没条件煮那种又香又浓的咖啡。
常常是一杯咖啡尚未喝完,主任就来查房了,他就得躺到床上去,而她则隐蔽在阳台上扮演一个偷窥者。
主任不是一个人来,而是带着一群随从马弁,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所谓的随从马弁其实就是一些实习医生。通常都是主任简单问患者几句,患者一一作答之后,主任就开始给实习医生讲课,在患者身上指指点点,有时候还要患者做几个动作,给实习医生做示范。
万喜良倒没觉得什么,安静却看不下去了,这天,她实在忍无可忍,从阳台上闯进屋里,指责主任说我们到这里是来治病的,不是来给你做人体道具的,你们治不好我们的病也就罢了,干嘛还来折腾我们?太过分了,每次给患者检查只用五分钟,而讲课却要用十五分钟!主任吓傻了,面对着嘴唇抖个不停、眼冒凶光的她,居然哑口无言,匆匆离去。也许在他从医的二十几年里,还是头一次遇到如此尴尬的局面呢,自然抵挡不住了。
安静的抗议果真见效,以后主任再来查房,随从少多了,对待患者也像对待陈设在珠宝店橱窗里的展品一样,小心翼翼。以前他的白口罩总是耷拉在胸前,而不是戴在嘴上,现在则是全副武装,口罩上方只露出一双战战兢兢的眼睛。他是怕患者投诉他,那样的话,全年的奖金就泡汤了。
安静似乎得寸进尺,在她卓有成效地对付了主任以后,又想掉转枪口来对付护士长。护士长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发现一点问题,就会对患者大喊大叫,声调要比一般人高八度。万喜良觉得护士长不是好对付的,难度极大,劝她罢手。她却说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她跟护士长谈过几次,焦点就是围绕着关于护士长声调高低的问题,但每次都谈不过五分钟就谈崩了。几个回合下来,安静终于败下阵来。护士长“涛声依旧”,而安静则垂头丧气,说话也像快僵死的蝉所发出的微弱而嘶哑的哀鸣,她说万般无奈,护士长改不了她的大嗓门,她原来是歌舞团唱花腔女高音的。她的那腔调,还有那表情,都是典型的残兵败将所独有的,逗得万喜良不禁哑然失笑。
呆久了,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某种依恋感,仅仅白天在一起是不够的,晚上还想在一起怎么办,他们就在熄灯的时候,各回各的病房,等夜班护士巡查一遭之后,走了,又凑到一块。不过,得“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通常熬过漫漫长夜的最佳方式就是听音乐。
一个CD机,一人一只耳脉,背靠背,坐在用锯末擦洗过的地板上,听着歌,陶醉在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沉静之中。可惜,也有一个小麻烦,他最拥趸的是披头士,而她最欣赏的则是仙妮亚·唐恩,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听一首披头士,再听一首仙妮亚·唐恩,交叉着来,和平共处。
临睡前,两人还要合听一会儿亚瑟小子,因为,他们对那个黑小子都不反感。
一天,有个病友走错了门,一下子闯进来,看见他们俩背靠着背都紧闭双眼坐在地板上,不禁惊叫起来,撒腿就往外跑,还是万喜良抢先一步拦住了他。他急促呼吸了半天,才说我的妈呀,我还以为是一对徇情的恋人呢。是,两年前这个医院里发生过这样的悲剧,据说。
这个病友原来是个水手,经常跑新港到阿姆斯特丹那条航线。虽然常常嘴里哼着“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而实际上却天天眼神暗淡,无精打采。病友都叫他小炉匠栾平,因为他矮。
小炉匠栾平给这个科起个绰号叫“等死号巡洋舰。”
小炉匠栾平有一双鸽子般的眼睛,却大而无神,是个模范的悲观主义者。
他的悲观情绪是放射性质的,具有传染性,常常能影响到其他的病友,以至于伤感成风。安静对万喜良说你给劝劝他看看电视,看电视能开阔眼界,他就会知道在这个世界比我们更不幸更倒霉的人有的是,像索马里的难民,像印尼风暴中的那些罹难者,还有伊拉克战争的遇难者,多看看那些人的遭遇,心胸就宽广多了。
万喜良觉得这倒是个比较好的合理化建议,就跟她一块挨个病房去游说,劝他们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看电视,起码“新闻联播”是必看的。死也死个明白,他说。一天下来,说得他们嘴干舌燥,到晚上,果然,各个房间都传出了邢质斌的声音。有的人把音量放得超大,那是因为放疗损坏了他的听觉器官,耳背。他和她很有成就感,成就感是一种温柔甜蜜的东西,它使人安逸、舒畅。为此,他们跑到酒吧偷偷喝了一杯,以示庆贺。
病友们的精神开始由阴转晴,以前大家见面聊得都是哪种自杀方式更便捷,痛苦少一点;现在谈得却是国际新闻,特别是天灾人祸,光是费卢杰人质事件就让大家担了好几天的心。奇怪的是,本来该十二小时就打一针镇痛剂的病人,居然也忘了催护士来给自己注射,连护士都挺纳闷;这些人的癌细胞是不是已经扩散到脑子里面去了,自己还危在旦夕呢,又去关注别人的生生死死!
万喜良却发现,安静虽然鼓动别人去看电视,她自己竟然始终跟电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几乎看也不看。
他问她原因。她告诉他好几个电视主持人她都讨厌,一个是曲苑杂谈的汪文华,半老徐娘,捏着嗓子装嫩,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另一个是梦想剧场的毕福剑,胡子一大把,竟还在台上装疯卖傻,不懂得什么叫自重。更夸张的是只要看见蔡明出镜,她就吐,真吐,蔡明那一副矫柔造作的作派让她恶心……
既然这样,他建议她去看凤凰卫视。她又说她讨厌“李敖有话说”,一个整天自吹自擂又自恋的老家伙,他最大的能耐就是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说这些话时,她的脸上还带有青春反叛少女的一种生涩劲,万喜良不禁暗暗为她高兴,这起码说明病没有磨去她的棱角,她的骨子里还是一个愤怒的青年。
这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了一条离开小河的鱼,在沙滩上扑腾。醒来之后,他种种不适的感觉一涌而上,沉甸甸地压迫着他。他突然决定去看母亲,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父亲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以后,他一直跟母亲相依为命。两年前,母亲才改嫁,嫁给了她的一个老同事。他也跟母亲的来往少了点,但是,这并不说明他对母亲有什么不满,相反,他还是很爱她的。
母亲见到他,喜出望外,她还不知道他得了病,他也从没打算告诉她他得了病。继父不在,母亲给他张罗早饭,他看看表,正好也是医院供应早餐的时间,不知安静吃了没有,他想。
他跟母亲谈了很多,把想对母亲说的话几乎都说了。说话的时候,母亲一直温情地握着他的手,还不住地扶摸他的脸,让他差一点流下泪来,好在他还是忍住了。不知为什么,母亲微笑的脸总是使他联想到安静,一联想到安静,他就仿佛闻到了她身上的那股紫丁香的香气。也许他真的爱上她了吧?
离开母亲,他搭个车匆匆往医院赶,他要立刻见到安静,是的,立刻,短短的一个上午没与她见面,对他来说,仿佛太久太久。
他恰巧在医院门口碰到了她。
她慵懒地背靠着门口,东张西望,当她的目光和万喜良的目光撞在一起的时候,突然亮了一下,但很快掉转开,回身径自向病房走去,连招呼也不打一个。
万喜良紧紧跟在她的身后。
跟进她的病房,她关上门,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说你抱住我,紧紧地抱住我,什么也别说。
他抱着她,就像抱着一团跳动的火苗,烫得慌,灼得慌,烤得慌。
偎在他怀里的安静,宛如一只小猫,温顺极了,她怪他没打招呼就自己溜出去玩了。他赶紧跟她解释了一番。之后,两个人似乎无话可说了,就这样你看我,我看着你,互相对视着。
他们终于吻在了一起。
他奇怪地发现,她的动作虽然笨拙,虽然生涩,却是最令人迷醉,以致于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直到她求饶为止。
我的妈呀,她说你是想把我憋死呀。她的脸颊真的一片嫣红,呼吸急促,好像刚从急流中挣扎着爬上岸。他说我想你一上午了。她说我也是。
接着,他们又热吻起来。她和他的嘴唇都是对方的罂粟,有着挡不住的诱惑。她的舌尖越来越灵巧,显然已经成了一个熟练工,能很快地将万喜良的身心俘虏了,他也只好随着她吸吮的节奏,将热吻进行到底了。趁着喘息的间歇,他说我再也离不开你了。她说我能相信你吗?他就模仿着《黑客帝国》里的台词说你以为我是谁;人类?
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就像刚刚跑过了马拉松,两条腿都软了。
安静仿佛突然意识了什么似的,猛地捶了他一拳,说见鬼,你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拿走了我的初吻!
他说难道还要举办一个盛大的仪式不成?
从此,在他和她的日常生活中,接吻就成了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早上一醒来,要接吻,午休时间要接吻,晚上临睡前也要接吻,已成了雷打不动的规章制度。接吻的时候,她的眼睛总是闭着的,而且总是要反复地问告诉我,这就是爱情吗?他回答说我想是吧。她深呼吸一下,又说我们还能吻多久?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吻到死,吻到我们一道死。
渐渐,安静开始不满足他们局限在嘴与嘴的接触了,她说别人接吻的同时,是要拥抱的,是要用手抚慰对方肩背的,还要吻脖子,吻耳垂,吻肩胛,总之,特激情才对。她还给他背诵阿根廷小说《唐·拉米罗的荣耀》中的片段:拉米罗用两只胳膊如痴如醉地用力搂住她的脖子,一阵强烈的冲动,驱使他想把自己的嘴对在姑娘的嘴唇上,用它们来吞咽和咀嚼爱慕、淫欲和痴情,疯狂地吞咽和咀嚼!最后,他发疯般地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
后来,他就像中了病似的,到处搜罗爱情小说,将有关接吻的描写抄录下来,读给万喜良听,让万喜良如法炮制。万喜良说她病态。她说她只是追求完美而已,尽可能地把接吻做到极致。他说我们已经堕落成色情狂了。她天真地说那有什么不好?
他说别费劲了,在漫长的接吻发展史上,没有谁比我们的吻更经典了,相信我。她说英雄所见略同。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但是万喜良明显地感到,过去了的每一天都在变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