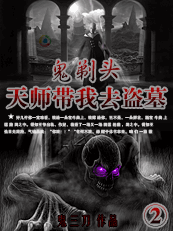带我去阿尔泰(全本)-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但是万喜良明显地感到,过去了的每一天都在变化着,这种变化就是他和她的两颗心越靠越近,最终将会合在一处。
李萍说他的眼睛更平时不一样了,特别有神,就像遭遇了激情似的。他笑而不答,心里却在说干嘛还好像啊,根本就是!假如李萍继续追问下去,他可能就招了,能与人分享快乐是更大的快乐,可惜,李萍没再问。
其实,万喜良身上所发生的变化不止是眼神,就连表情、声音以及肢体语言都有了化学变化,甚至包括睡觉,以前他睡觉时,从来不关灯,他怕黑,黑暗在他看来简直是可以用手摸得到的具体物件,特别恐怖;现在他已经适应黑暗了,在黑暗中他的大脑皮层更兴奋,他可以静静地幻想着病好以后如何带着安静去阿尔泰,明知不可能,但短暂的想入非非也是对几近干涸心灵的一种慰籍。
随着他和她的亲密接触,两个人的关系已然不是什么秘密了,差不多所有的病友都知道。一个自称会看手相的病友还给他们看了手相,说是郎才女貌,一对绝配。连医生和护士也开始在他们的背后指指点点的了,好在,他们也从来没打算保密,爱就爱了,一切无所谓……
有时候她会天真地说要是我们早几年相爱该多好啊。他嘴上骂她傻瓜,心里又何尝不这么想!
连他们自己都奇怪,他们俩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如果没人打扰,他们甚至可以一说就是一天。这天,他们俩聊得正起劲的时候,一阵嘈杂声从对面的病房传出来,好像是在吵架。对面病房住的是个大学教授,不到六十岁,因为谢顶,大家都叫他葛优或葛大叔。万喜良和安静过去看看,原来是葛大叔的两个儿子为房子的产权而大吵大闹,万喜良劝了半天也劝不开,安静急了,说你们的爸爸还没死呢,未免太操之过急了吧。两兄弟掉转枪口,一齐冲着他们俩开起火来,一边骂,一边还推推搡搡的,葛大叔吓坏了,赶紧从病床上跳下来,张开胳膊拦着,警告他的两个儿子说混蛋,你们真是吃了豹子胆了,竟敢跟他们大动拳脚,他们俩的病比我还重呢,除非你们钱多的没地方花了。安静也挑衅说动手啊,快动手吧,我还愁没人替我掏医药费呢。万喜良更是火上浇油,拍着巴掌说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享受公费医疗了,终于有地方可以报销了。那两兄弟愣了半晌,一甩手,悻悻而去。
葛大叔气得直掉眼泪,一个劲说家门不幸。他们俩劝了他半天,还一块出去散了步,葛大叔的沮丧情绪才有所缓解。这一天,两个人少吻了一次。
安静把眼睛眯了,结果让万喜良吹了半天才好。他说这就是眼睛太大的的害处,眼睛太大就容易眯眼,他当书商的时候,认识重庆一书店的女老板,就是总眯眼,每次见她都是被吹进眼眶里的尘沙磨得眼睛通红,他管她叫兔八哥,她则管他叫88号,因为他带眼镜。从他病了以后,他们就断了联系。
安静说这还是第一次提到他当书商的事。他说是吗?安静说她一直想问他一个问题,担心他不愿回答,所以迟迟没有开口。他说有问题尽管问好了。她问他当初从商的动机是什么,是为挣钱吗?他点点头。她又问他挣那么多的钱做什么。一句话竟把万喜良问得哑口无言,沉吟半晌,才说当初挣钱,恐怕就是为了现在付医药费吧。安静拍打了他一下,说少来啦。
两人逗了一阵子嘴,累了,安静就把脸贴在他的胸脯上,他抱她坐到他的膝盖上,有一种把整个世界都揽在自己怀中的男人的那安详、自信、甜蜜而懒散的感觉。安静咬着他的耳朵用法语说je rous aime (我爱你)。可惜,送药的护士把他们的美好感觉破坏了,她推着个药车,挨门叫着病床的号码,跟牢房里的狱卒叫囚犯差不多。
安静忿忿地拉开门,闯了出去,对护士说请你们有一点人情味好不好,不要总是用那些冷冰冰的阿拉伯数字来招呼病人,什么72床吃药了,什么85床打针了,把活生生的人整个物化了。护士笑嘻嘻地问安静,应该怎么招呼病人?安静说叫名字就可以了,当然最理想是根据年龄多少、辈份大小来相互称谓,爷爷啦、叔叔啦,或是姐姐,哥哥什么的,就跟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因为我们大家总是要相伴着走过这最后一段路的。护士说要跟护士长商量一下才能决定。
又是护士长,安静就像一个人患了牙龈肿痛似的努努嘴,护士长几乎成了宇宙中心,一个独裁者,换个被单要找她,开两片舒乐安定也要找她,总有一天,病人们要不要说话,该不该倾听,能不能眨巴眼睛,怕是也得由她来决定了。
眼下,就有一件事耽搁在护士长那。
再有四天就是五一黄金周了,健康的人可以去旅游,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主题派对,或去唱歌,泡吧,而病人能干什么呢?什么都干不了,唯一能干的,就是看场电影什么的。于是,安静就去找护士长,提出这么一个要求。
为了表示她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安静还写了个书面报告,挨个叫病人签上名,按上手印,整得跟请愿书差不多,交给了护士长。
护士长先是不同意,说是史无前例。安静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护士长说没地方放映,资料室太小,大食堂五一那天又要会餐。安静说可以在草坪那,跟我们小时侯一样,放一场露天电影。护士长不言语了,像是在考虑。安静趁热打铁,又说生活少不了合乎人性的精神乐趣,我们的身体跟植物一样,会发芽、开花、枯萎、死亡,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不朽的灵魂……
护士长说要我再想想。
一连三天,护士长那都没动静,安静嘀咕起来,她对万喜良说护士长不会把这件事忘了吧,听说她丈夫正在跟她闹离婚呢。万喜良让她静下心来再等等,明天才是五一哪。她撅着个嘴说只好这样了。
转天安静去找护士长问个究竟,护士长淡然地问她要看什么电影。她惊喜地说是不是院方同意了?护士长点点头,说已经跟电影放映公司联系好了。也许满意的结果来得太轻而易举了,她竟毫无思想准备,用手搓着赤裸的两条臂膀,半天说不出话来。
护士长拉起她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手里,说要看什么电影,得提前通知电影放映公司,他们好从资料库里去找。安静强忍着不让自己兴奋地跳起来,她尽可能平静地说她要跟病友们商量一下。护士长依旧板着个面孔说那好,我等着。
关于看什么电影的问题,病友们形成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是要看国产的老电影,另一派则要看好莱坞的新电影。
安静为难了。幸亏,万喜良给她一个合理化建议,一口气放两部电影,一部老电影,一部新电影,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安静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抛了一个媚眼给他,就跑去找护士长了。回来,她挨门挨户通知,晚上将放映的是《小兵张嘎》和《凤凰劫》。安静出来进去的就像一只快乐的小燕子,唧唧喳喳没个完,整个走廊都听得见。
这一天,仿佛是病友们盛大的节日,好多人都在掰着手指计算,自己究竟有多久没看电影了,三个月?半年?或者更久一些?
天还亮着,夕阳正红的时候,就有病友和病友的家属拖着躺椅板凳到草坪上占地方去了。
就连黑桃K也来了。他从住进医院,一天到晚没干过别的,就是从事各种自杀方式的尝试,跳过楼,触过电,服过过量安眠药,都没死,也算是福大命大。他是医生眼里的一级保护动物。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喝完酒之后,就打架,他也曾跟万喜良打过,打过之后反而成了好朋友。
这天的天气也真好,空气里散发着一种湿润、清新、沁人心脾的味道。黑桃K对万喜良说这时候还能看上一场电影,死也值了。万喜良冲他笑一笑,心说常把死挂在嘴边的人,反而不容易死,这家伙就把许多看起来比他健壮的人都熬死了,自己却依然活着,活得有滋有味,虽然面黄肌瘦。他是这个科里的元老。
电影放映的时候,安静拉着万喜良跑到幕布的后面去看,看着比正面还清楚。周围海棠树沙沙作响,像是窃窃私语,那么温柔,那么缠绵。此时此刻,要是再有一两声犬吠和三四声蛙鸣,就跟小时侯看露天电影的情景一模一样了,而且空中飞舞着的萤火虫也四处点起一星星的火光,特有怀旧感。
安静得意地说怎么样,这样的露天电影是不是挺棒?万喜良点点头,说不错,你真不简单,人才呀!
他和她一边看电影,一边享受着夜吻的甜蜜,她甚至还允许他的手钻进她的上衣里抚摸。这时候的她,已经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成了罗马。欲望的小火苗遽然袭上他的心头,他俏声说什么时候能让我瞻仰瞻仰它。她羞怯地明知故问道瞻仰什么?他按了按她的乳房,他想象它一定是玲珑剔透的。她翻翻上眼皮说那要看你的表现了。
老电影里的每一句台词,他都烂熟于心,都能背,用不着再看,他就躺在草坪上,枕着两手,眺望着夜空,他觉得那些晶莹眨动的星星,在用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跟他讲话,在强化着他的激情。
安静问他为什么不再对她性骚扰了,是不是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他冲旁边努努嘴,这时候,安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有好几个病友也都跑到幕布后边来了。安静悄悄牵着他的手,溜掉了,径直跑回病房里。两个人摸着黑呆在那,面对面,喘个不停。过一会儿,安静怯生生地问他,是否真的想看她的乳房。万喜良咽了一口唾沫说真想。安静说那就来看吧,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看过它的人。
她洁白一身地站在那里,酷似一尊圣母像。淡淡的橘黄色的光线透过窗户映进来,她的两个乳房宛若两只小鹿,恬静而又柔和。他的脸色和夜色交融在一起,但眸子闪着奇异的光,他感觉得到,她正在瑟缩发抖,显然她比他还紧张。
这个丰润嫣然的乳房,闪烁着月亮一般清冷而又神秘的光辉,距离他是如此之近,它仿佛在对他说:它是你的禁果。他的血液沸腾了,犹如一群蚂蚁在他的心上爬,痒得难受。他忍着,木然地站在那。
他竭力把渺茫的充满了欲望的心从幻境中拉回来,面对现实,想象着这样美丽的神迹,这样圣洁的造物在不久的将来,会枯萎,会随着生命的消失而消失,不禁黯然神伤,总觉得命运之神对她太残酷了,他发誓他要好好爱她,好好疼她。
这时候,安静的嘴靠近他的唇,给他一个热乎乎的吻,说演出到此结束,闭幕了。然后匆匆穿上衣服,拉着她又回到草坪上,继续看他们的露天电影。万喜良却很久很久没清醒过来,仿佛还在梦中。
还是老电影更受欢迎些,新电影上演不一会儿,就有许多的病友开始退场,万喜良问安静我们怎么办?安静说我们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分钟。万喜良说是不是散场以后,我们还要义务劳动一下,把草坪收拾干净?安静说义务劳动的不是我们,而是你,我只是监工而已。万喜良说我怎么这样倒霉呀。安静说活该。
电影结束,已经是很晚了。
简单收拾了一下,回到病房的时候,他浑身跟散了架似的,瘫软无力,走起路来俨然一叶扁舟,悠悠荡荡。他知道,他是累了,体力有点透支。他赶紧到卫生间冲了冲凉,之后,躺下,点上一支烟,歇着。最近,他闹牙疼,一抽烟,就牙疼,最可怕的是,他的牙齿完全糟了,用手轻轻一拔就掉,不知道是放疗惹的祸,还是缺钙的缘故。
一想到自己的牙都掉了,张开嘴,就像一个黑窟窿,他就禁不住惶恐不安,毕竟他才刚刚三十来岁呀!
这时候,有人敲隔壁的墙,不用说,那是安静。这是他们的暗号,如果敲一声,是问早安,敲两声则是问晚安,现在她敲的是三声,意思是问对方睡着了没有。万喜良赶紧也敲了三下,做了回应,告诉她还没睡呢。
不一会儿就听见有悉悉索索的声音。
安静鬼鬼崇崇地钻进他的屋,万喜良发现,她居然光着脚丫,他说你不怕着凉么?她竖起了一只手指放在唇边,嘘,这样走起路来没动静。
他以为她太兴奋了。所以睡不着。他们的生活太沉闷了,有如一潭死水,随便丢下去一颗石子,都会荡起一阵阵的涟漪。他让出一块地方,让她坐。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睡衣,睡衣上绣了一只大个的米老鼠,他知道,那是她的手艺。睡衣穿在她身上,特像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他刚想逗她两句,却发现她有点不大对劲,她耷拉着脑袋,脸色苍白,额角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仿佛晶莹透明的雨滴。你怎么了,他问。
疼,她说。他问那里。这,她按着肝区。从什么时候开始疼的?他问道。她说就是刚才。他要去找医生,她说用不着,过一会儿就好,我们随便聊聊天,转移一下注意力就可以了。他的手有点抖,也许是过分担心的缘故,他担心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他把她搂在怀里,用手抚摸着她的额角。
两腿屈着,她那他的枕头顶在肚子上,问他我是不是教科书似的女人啊?他说不是。她追问道不是教科书似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他说是性感小猫。她嘻嬉笑了,又问道看见我的身体,你会想到那个吗?他明知故问道想到哪个。她把身子朝他靠的更近一些,说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温存地说了一句。他们靠得如此之紧,以至于他都能闻到她呼出的气息,那气息是甜的。
我说的是性,她说。
他故意说我想不到那个,我还小着呢。她就笑得更欢了。他感到她的手在寻找他的手,很快,她的手指就和他的手指交叉在一起,牢牢地握着。后来,她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上。他说你这不是要我当流氓吗?她说我就是要你只当我的流氓。
他说无论如何,她也要把病情告诉给主治医生。她反问道告诉他干吗?他说让医生调整治疗方案,免得病情进一步恶化。此时此刻的他,真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挽救这个可爱的女孩,如果可能的话。她却毫不在乎地说怕什么,若真的恶化了,实在疼的受不了,就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