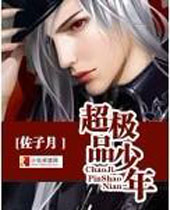极品男保姆-第6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剥好了嫩玉米,揪好了嫩好花生,我们正择毛豆角子,翠儿过来了,进门儿就给老太太要手机。
老太太说:“你不是有电话吗?”
翠儿用眼白瞪她:“欠费了,再说啦,给恁(你)儿打电话当然用恁(你)嘞的电话啦!拿来!”
翠儿从老人手里掠过手机,按通了,就大声嚷上了:“喂,我说你今年秋收要是再不回来我死巴死嘞给你离婚!一年给我寄几千块儿我都满意啦是咋!我是活人,不是存钱罐儿!……啥,你说啥你说啥?我啥时候夜里睡觉不关好门儿啦!你瞎哇哇啥!”
翠儿骂着挂断手机,冲老太太一瞪眼:“你搁(在)电话里边给恁儿说啥啦你?他咋忽晃得(突然)说起睡觉的事儿啦?”
老人看看我们,惶恐地说她啥也没说。翠儿骂骂唧唧地走了。
老汉冲着她的背景吐了一口唾沫,唉了一声。
晚饭我们也没在翠儿家吃,讨厌她那种对老人的态度。
我们的晚饭挺好,嫩玉米、红芋、毛豆还有花生,四样儿,一块儿在大铁锅里煮了,那种混合的香甜,是在北京永远也吃不到的。小语吃得直叫哥,笑得好甜。
同时来了个就地取菜,就在墙头摘了一大把紫梅豆,抽了细筋,热水一焯,切片,炒了个清香爽口,就着大个儿的卷子馍,小语吃得比今儿个上午的酒席还美呢。
吃的时候看一台黑白电视,一看新闻才知道,今天是西藏解放五十周年庆典,新闻联播因此长达50分钟,礼炮二十一响。我看得直到小语感慨:和平真好啊,大到一个地球,中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微到一对男女组成的看起来象家的东西,都需要啊。
小语却佯装没听见。
小语累了,吃了晚饭就说回去睡。
我们的屋里只有一张大床,一个蚊帐。秋夜蚊子数量并不见少,咬人好象更执着。
我本来想要一个小床的,但翠儿家时偏没有,她还笑着说,你们两口子还不睡一个床啊。
吃过白果仁儿,简单洗了,小语就上床了。
我心里很不安,虽说以前我和小语不止一次地在一张床上睡过,但这一次,因为和蔷薇的那一夜,我
的心一直在反复地徘徊不定,小语还是小语,我却已不是我了。
小语在蚊帐子里叭叭地追着蚊子拍打:“贪婪的男人就象蚊子,从不满足吸一个人的血。”
我说:“聪明的蚊子不应该到蚊帐子里去吸血,太危险了,吸了血之后更危险。”
小语坐下来,看着手掌上的血迹:“怪不得佛说有些生命永远也无法成佛。”
“为什么呀?”
“佛把所有的生命叫做众生。众生中又分为人、天人、阿修罗、畜牲、饿鬼和地狱。前三者为三善道,后三者为三恶道。天人和阿修罗居住在天界,志趣高尚;而三恶道则趣味低下。”
“那人呢?人的趣味呢?”我追问。
第131章 小语: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
“佛经上没说,可见人的复杂连佛也拿不准呢。”
我说:“这是佛在暗示人,要是朝好了走,那就能上天,成为天人,要是朝下走,那就得入地狱。”
“你挺行的。哦,扯远了,我说有的生命修不成佛,指的就是那三恶道,他们缺少智慧,依本能做事,比如蚊子,就知道吸血。”
“你的意思是,就是佛手把手地教它们它们也听不懂佛在讲什么?”
小语:“是这么个理儿。所以,佛没有专门为三恶道说法。”
“这就是佛的不对了吧?他不是说众生平等吗?为什么轻视三恶道不为它们说法呢?它们就象穷人,你越不扶持他们他们就会越穷,非穷死不可。佛为什么这样做呢?”我有意刁难小语。
小语笑:“你真行。别说我,只怕佛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说着,她挺了一下腰,说累了。
看着她弧度优美的腰肢,我心一动,扒天蚊帐子:“想迅速消除疲劳吗?请跟我学站桩。”
“快合好,蚊子要进来了……站桩?象你那么傻地往那儿一戳吗?”小语笑。
“不用,这大成拳其实分三种,一种是站的,一种是坐的,一种是躺的。其中坐的最适合你,你又是读佛经的,要是来个莲花打坐,离菩萨真的不远了。”说着,我身子探进蚊帐,“就这样做……”说着,我伸双后,把住小语的肩,轻轻一磨,她的整个背就都是我的了,我的身子轻轻贴上去,小语轻轻地哦了一声,头乖乖地贴在我的胸前,但马上又极快地用头向后猛地撞在我胸口,身子前倾,离开我的抱,回头嗔我道:“人生最大的债务是人情债,人生最可恶的是淫乱。”
我说:“停停停,你这么教导我,我欠人人情还是乱搞男女关系了啊?”
小语也不禁笑了,刚要说什么,我的手机响了。
看号码,是蔷薇的。我赶紧出屋接手机。
蔷薇很失意地:“你怎么老不给我打电话,从没想过我吗?”
我说:“不是。我现在在外面采访。”
蔷薇:“我好象觉得你一到月初就出去啊?你怎么象女人身上来事儿啊?”说到这里,她自己都笑了,接着又问,“你不会是和那个小语在一块儿吧?”
我笑:“不是。和一个老记者,男的。”
“你现在说你想我了。”蔷薇开始撒娇,“人家想你了,腰又有些疼了呢。”
我听得心里拱拱的,但我不敢说。
蔷薇一个劲儿地逼我说,最好,我只好低声说了。得到的,是蔷薇叭地一个响吻。
回到屋,我很难为情地说了句“我可上床了”才慢慢地上了床。
小语奇怪地问:“几时学得这样文明?刚才谁打的电话,听着象个女的。”
“你嫂子,说小家伙感冒了。”我撒着谎在床的另一头躺下。
小语坐起来:“这会儿,我倒想问问,和你妻子相比,我和你算是什么关系呢?”
我想了想:“我和妻子嘛,就是两根骨头,然后一根筋连着,和你,就好比两只刺猬,近了会扎疼对方,远了又冷了对方。”
小语摇头:“我得纠正一下,不是扎疼‘对方’冷了‘对方’,而是‘我’。”
“好好,就照你说的吧。我看,我们只有把刺拔了才不至于伤着对方。”
“拨了刺就不是刺猬了。”小语看着腕上了绿镯子,“你不觉得你象一只贪吃的猫吗?你妻子是一条躺在案板上的鱼,已经无路可逃,而你,又把目光盯上了我这只鱼缸里的鱼。”
我连说不是不是,我没想到小语会这么直接地谈到这个问题,无力地连连否定。
“不是?难道你真是个圣人,真的对我没有企图吗?”小语直盯着我。
我无语,反复地按手机的铃声,盲目地选了这个选那个。
小语:“不管你怎样否认,我们的关系现在和将来不外乎三种,兄妹关系,情人关系,夫妻关系。可这三种关系发展起来都是悲剧,也都不可能。”
“你突然说这个干么呀?”我有点儿不在所措。
“是你妻子的电话提醒了我。其实,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个现实,早说比晚说要好。”
“照你这么推理,我不如早回老家?”
小语点头:“那是你的事。我想,在北京,你也许可以成就世人眼中的所谓事业,但同时,也许会毁掉人固有的自在。佛教众生忍耐,但我看得分忍耐什么,如果只是忍受苦难,那应该可以承受,如果是在良心的煎熬中苦忍,倒不如不忍的好。”
我的心绷得很紧:“你,希望我走吗?”说开了也好,不等小语回答,我又追问:“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
小语愕然,对这个问题她毫无思想准备。想了想,她郑重地说:“绝对不是我爱你。”
这答案让我心里很酸楚,虽然我有思想准备,我问她:“那你爱谁?”
小语:“谁也不爱。”
这种回答又让我心里稍微好受一点儿,我剜她:“和一个不爱的男人同床,你怎么解释?”
小语:“说明我还不讨厌他。累了,睡吧,一个床,”说完,她扯过床单,盖在穿着衣服的身子上。
关了灯,我向外挪了挪身子,一只胳膊挨上了蚊帐。自尊,可以压抑所有的邪念,如果一个人还有自尊。
耳边,有蚊子嗡嗡不绝,正在蚊帐外不甘心地寻找着进入蚊帐的机会。
我睡觉一向很轻。刚想睡着时,就听到扑通一声,显然是有人跳进院子来了。难道有贼?
稍停,却又听到堂屋门被轻轻推开。
我笑了,我想到了那个打月饼的男人。
正想重新睡去——
“有贼——抓贼呀!——”
外面忽然传来一个人的叫喊声,接着,是院门被叭叭拍响的声音:“丁大姐!丁大姐!快开门!有贼进院儿啦!”
越来越多的杂乱的奔跑声。
小语的身子动了动,惊悚地坐起来:“怎么了哥?”
第132章 虽然是收获,但收获也很累
我安慰她:“睡吧,没事儿,捉奸戏而已。”
拍门声在继续。
这时,堂屋门又开了,先是一个轻轻跑出去的声音,接着,是翠儿恶狠狠地声音:“瞎叫唤啥,哪来嘞贼,都滚!”
堂屋门重重地关上了。
院外的声音这才渐渐散去。
这一夜睡得很安静,象睡在水底的沉船——面对自己原有欲望的女人,当她第一次明确地告诉你她不爱你,而你又心疼她从没打算用暴力征服她时,你还能作什么?
我醒来的时候,小语正坐在床上看窗外。
我也扭脖子往外看:有点儿阴天。
我坐起来。
“早。”小语淡淡地打招呼。
我回了一个“早”,尽量自然如初。
看着小语的脸,我一边磨身子下床一边笑道:“你眉心的位置有个红点儿,有点儿象菩萨呢。”
小语用手指轻轻揉着眉心:“别以为点个点儿就是菩萨,那是蚊子咬的,你一说又开始痒了。”
“说得好,别以为少条胳膊就是维那斯,那是让人给打的。”
小语终于笑了一下:“一睁眼就贫。”
今天是半阴天。身上凉凉的。
小语穿那套白色的秋装,都有点儿抖肩了,连喝了两碗热饭。
饭后,翠儿说去摘苹果,先轰走了两个闺女,又问我们去不去玩。小语说去啊。
临走前,翠儿用一根木把儿长勾子,喀喀从桐树上勾下几枝树枝子,呛掉叶子,往篮子里一放,领着我们去苹果地。
我说你不带东西,摘了苹果咋拉回来。翠儿一笑:到时候自有人帮忙。
出村,一斜西北有条小路,弯曲得让人想起几千年的阡陌来。翠儿的嘴不闲,说东道西的,等到了一块菜地,停下,弯腰用桐叶盖那刚种的小白菜,说这会儿的天,清早冷晌午热,刚栽的白菜不禁太阳。
小语也帮她盖,盖的时候象给婴儿盖被子。看那样子,我的心就隐隐的疼:这么有爱心的一个女子,怎么就不会爱人呢?就算不是爱我,也好啊。
地头,一个一人多高的麦秸垛,灰灰的,经一夏风雨,已经象一个老掉的大蘑菇了,而和小语一起割麦的情形却还象随时可以合拢的手掌。
白菜地只有一间屋子大,盖好了,我们穿过一片不宽却很长的杨树林子继续往西北方向走。
林子里是遍地的黄叶子,一步一嚓嚓,走不完的情调。
林子两侧是矮矮的棉花地,也就是说,这林子所在的地方原来应是良田呢。
我问翠儿:“这好好的地怎么种树啊?”
翠儿朝一棵树拍了一下:“地没人种,都打工去了。种树最省事儿了。等明年春上我也得种一块。”
快出林子时,一只斑鸠漱漱地飞进来,羽毛梳理空气的声音象遥远处冬天冷漠的表情,而苹果的香气也同时飘了过来。
满眼的苹果,全是红富士。云很低,压得香气郁结在果树之间,浓得口腔和眉眼里都是香。
小语欣喜地从这棵树看到那棵树,从这棵树摘到那棵树,说,从没见过这么多这么鲜美的苹果。
是啊,只有站在果园里,走动在果园里,直至让果实碰住了你的前额你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硕果累累。
五指刚捏住一个大苹果,手机响了。
是陈述的。
我问他干么,他说下午两点去承德,有个演出,让我马上到公司。我说我这会儿在外面采访呢,去不了。陈述你丫是采花吧,就骂骂唧唧地挂了。
突突突一阵响,接着,一个男人大声喊着翠儿。
翠儿折着身子扳着果枝子应着。
一会儿,一个男人,就是打月饼那男人,一手拿着一个黑呼呼的瓜进了地,冲翠儿大声喊着:“给你弄个稀罕尝尝——面瓜!”
翠儿笑着:“觉呼得(觉得)你打月饼不得闲不来哩。”
男人看看我们,嘿嘿地笑:“打啥月饼哎,你嘞事儿比月亮还大嘞。”
翠儿把一个面瓜递给小语:“俺俩去地南头儿摘,恁俩呆这儿摘吧。”
我从小语手里接过面瓜,一掰两开:“面瓜,专供没牙的老人吃的,尝尝,别太大口,面得咽人。”
小语尝了一小口,嗯着,“真面,怪不得叫面瓜……还香呢。”
我应着,一扭脸,我看见那男人的手掌在翠儿的屁股上拍了一下,然后,手和屁股同时消失在苹果低垂的果枝后面。
我笑着:“小时候,我们家自留地里也种甜瓜,我贪吃,就在靠边的一棵瓜秧上偷偷留了个小瓜妞儿,在瓜妞下面掏了一个坑,把瓜放到坑里边,然后用土一封。等过了一段时间,我以为瓜长大了,谁知一扒扒出的是一个小坏瓜。”
“偷偷摸摸不敢见光明,当然要坏事儿了。”小语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我的面瓜很快就吃完了,但小语的还剩下一大块,皱着眉不知道怎么办。我接过来就啃:“把我当垃圾桶吧。”
小语你你着:“吃我剩下的,不嫌脏啊?”
我坏笑:“相反,经你的口齿一切割,吃起来更香呢。”
吃完瓜,我们接着摘苹果。
这时,小语指着高处一个大大的红苹果:“看,太漂亮了!”
我二话没说,上去就摘下来了,放到她手里。
小语果蒂果脐的翻看着,摇头:“远没有挂在树上好看呢。看样子,果子如果不长在树上,就失去了欣赏的意义。”
我说:“这就象男女,如果不恋爱,就失去了青春的意义,对吧?”
小语看看我,把苹果塞进我手里:“去,把它重新安枝子上去你就知道答案了。”
我说好啊,就把苹果送了上去,放在一个枝桠上,然后,逗她,站在树下,一动不动。
小语:“干吗哪你?”
“等苹果落下来啊。”
“干吗?”小语理奇怪了。
“我要当牛顿,不要当牛粪!”
小语笑出声来,伸手在肩上推了一下,转身去摘苹果了。
摘苹果也不是好活儿,身上一会儿就见汗了。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