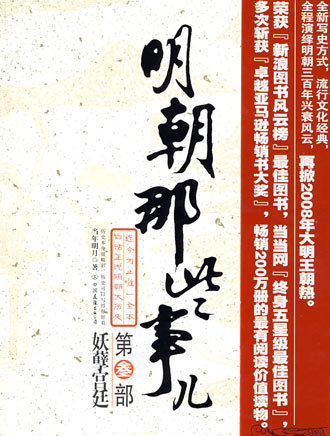北京爷们儿-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船老板满脸赔笑道:“谁能想到您的赌局如此高深,明天也不一定有人敢试,要不就算了吧。”
“期限是三天,要不老三该说我食言了。”说完范先生朝后甲板走去,一会儿直升飞机轰鸣的马达声又一次响起了。
我回头看看山林,这家伙居然如释重负般地长出了口气。当夜,山林睡得像头死猪,我则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有种不祥的预感叫人气闷难耐,就像上回去广州一样。
第三天我和山林跑到赌场里观战,那天范先生来得比较早,而且他宣布筹码再加十万元。有一段时间场内几乎白热化了,我看见好几个人怒目拧眉,身体如一张拉满的弓,可他们冲了几次最终都在牌九桌前停步了。范先生把手放在钞票堆上,手指像弹钢琴似的地敲来敲去,他一脸漠然地看着全场的人,眼里多少有些蔑视。突然他站起来,双手按在钞票上,得意地说道:“怎么样?钱再值钱也没有命值钱。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看来这场局我赢了。”说着他要随从递了个眼色,随从们竟开始收拾东西了。
我长出了口气,一阵轻松如宜人的煦风,似乎这种生活也就此远去了。突然一个穿着红马甲的人冲了上去,我定睛一看那家伙竟是山林。
山林冲到范先生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我可以试试吗?”
范先生不屑地哼了一声:“谁都可以。”
“不行。”我脱口喊了出来,全赌场的人立时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不行。”我觉得自己比山林都紧张。“不行,你他妈的吃多啦?”我扑过去揪住他的衣领,一较劲几乎把他提了起来。山林看着我,笑起了,笑得非常天真。“我要真死了,你就把钱拿走,我爸要是还没喝死,你就给他一点儿,让他有钱买酒喝。要是没死,咱俩回北京接着干。”
“不行。”我松开手给了他一个嘴巴,山林被打得原地转了个圈儿。此时范先生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几个马崽冲上来,从后面抓住了我。我突然把身体缩成一团,拳头和胳膊肘弹簧般崩了出去,立刻有两个马崽被打倒了。另外的几个马崽如闻见血腥味儿的蚊子,他们在周围转,突然十几条胳膊一起砸过来,我奋力抵抗可终归人单势孤,没几下我就被马崽们按在地上了。山林站在旁边,他抱着胳膊没动,脸上全是无可奈何状。范先生把脸转过来,他看着山林道:“要把你的朋友怎么样?看样子他练过拳。”
“让他到外面安静一会儿。”山林苦笑着说。
几个马崽把我抬到底舱,临走时哥几个还捶了我一顿。不久阿三跑了进来,他惊慌得差点在舱门口摔个跟头。“山林怎么样啦?”我一下将他提起来。
“他,他?!”阿三跟不认识我似的,他瞪圆眼竟研究起我的脸来。“你们真是好兄弟,你一直叫你呢。”
“到底怎么样了?”我冲他耳朵吼着。
阿三使劲胡噜一下耳朵:“他真给了自己一刀,扎在肚子上。可没死,现在正叫你呢。”
我撇下阿三,飞快地向甲板上跑去。船上特清净,人们都在赌场看热闹。我冲到赌场门口突然停下了,当时我发现自己对这扇门产生了无比的痛恨,如果手边有把斧子非几斧子把它劈了不可。更可笑的是我突然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种虚幻感,那感觉像一杯极苦的酒。
等我见到山林时,他并没有躺在血泊里,据说地上的血已经擦干净了。范先生深谋远虑,他带了个外科医生,山林接受了简单的处置,他躺在牌九桌上,脸色煞白,兰色的裤子已经变成了黑色。那只装满港币的鳄鱼皮小箱子就放在他手边,山林攥着箱子的提手。另一只手竟一直握着那把军刺。看到我进来后,山林长出口气,圆睁的眼睛终于眨了眨几下。“你要把我弄回去,我在船上呆腻了,我,我也不会游泳。”说完,山林安心地把眼闭上了。
“你的朋友身体很好,医生说他死不了,这么长的刀口他还死不了真是命大,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活着回去。”范先生在我身后说,他突然叹口气:“没想到你上船上还收留了这两个人?”然后是船老板尴尬的笑声。
五
深圳的故事
我就找到船老板把我们上船时留下的几口刀要了出来,船老板通情达理,也许他认为这几把刀并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不是我心恨,但用不了一天我们俩就将成为全香港黑道人物的焦点,到时候我和山林的小命肯定保不住。我没和别人商量,当天后半夜便逼着阿三出去找了条船,准备偷偷离开公主号。山林有股狠劲,他明白非如此不可,便在阿三的搀扶下硬是走了出来。我们上船前碰上个在甲板上转悠的服务生,我甩给他一千块钱,另一手中的刀尖指向他的鼻子。服务生摊开手,嘴张得比瓢都大。“我不要你们的钱。”说着他就要把钱还给我。
北京爷们儿全文(75)
“拿着。”我低声吼着。“就说没看见我们,听见没有?”
“好,好,好。”说完服务生就往底舱跑去了。
阿三是个边民,路熟人熟。两个小时后我们就登上了深圳的土地,登岸时我竟有股热泪盈眶的感觉。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这个清晨我又回来了。
朝霞如锦,河堤上已经有行人了,一大群鸭子铺天盖地的沿着深圳河游过来。灰黄色鸭群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面,连树干上都挂着黑豆似的鸭子屎。我毫无缘故地想起一句话:河畔的紧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
山林坐在旁边,偷渡船悄悄地离开我们的视野,阳光在半空画出淡黄色的光晕。微风似絮,拂过脸颊时有一种异样的舒适令人昏醉。
阿三通过熟人把山林安置在深圳郊区的一个小医院里,我在医院附近租了套当地人的楼房。等山林出院的期间我和阿三谈过一次,大意是说以后怎么办,跟我们干保证不会亏待之类。阿三对我们两个一直很钦佩,这两年多我们没少帮他还赌债。他听到这话马上满口答应下来:“我知道跟你们干不会吃亏的。”他挑着大拇指说:“你们是男人,将来都是老大。”
半个月后,山林可以下床活动了,我把钱藏起来,自己和阿三跑到广州调查市场。我在广州呆了三天,这一年多来走私香烟的市场变化挺大的,伦敦、登喜路基本上不见踪迹了,键牌也大不如前,可万宝路、希尔顿的销量大增,听说北京人就抽这两种烟。另外我又在其他市场看了看,那两年世面繁荣,物价也是一天一个变。还有一件事得说说,我路过八姐的店铺时,竟发现八姐的店铺还开着,离着挺远就能看见四川姑娘正在招呼客人。当时我喜上眉梢,八姐这个臭婆娘是不是以为我们死了?下回再说。
我们准备坐慢车回深圳,火车站在广州东面,是个小站。车站刚装修完,室内墙上贴满了瓷砖,活像个大厕所。站内倒是挺干净,当时不是经贸旺季,旅客稀少。我们到站时,月台上正好有辆南去的慢车。
售票员告诉我们,车是坏的,应该坐下趟。”我们闲来无事,便跑到月台边的茶座喝啤酒。
“山林的伤不会留下后遗症吧?”我看着酒杯,一脸茫然。这话与其说是问阿三,不如说是自言自语。阿三本来正瞧着过路的人群发呆:“你说什么?”
我苦笑了一下,阿三除了在赌场上还算精明外基本上就没心眼了,跑腿打杂还可以,却不是个可以交谈的人。
酒喝了两瓶,心思却越来越杂乱。阿三忽然道:“船老板对咱们挺好的,真有你说得那样严重吗?”阿三挑了下眉毛,看久了,这家伙也不见得有多寒颤,就是鼻子塌点儿,下巴短点儿,眼睛小点儿。
“这样你正好把船上的赌债躲过去。”我不愿意再跟他解释,站起来去结帐。
我们借着酒劲偷偷溜进了车站。这是个小站,下趟火车连影儿都看不见,月台上都是慢车上下来的旅客。我们无处可呆,干脆席地而坐了。这几天在广州转了好几圈,现在居然有些腰疼。此时天色阴下来,眼前的一切都成了灰的,看样子要下雨了。空气中有股淡淡的腥味儿,我在默数从面前过去的人腿。数行人和汽车是我从小打发时光的办法,有时在记数的某一瞬间,我会突然入定,于是所有的烦恼、欢乐、忧愁,甚至自己的存在都无影无踪了。月台上人挺多,他们涌来涌去的,毫无规律。
渐渐我有些困了,于是索性眯上眼,在一条白色虚逢里,所有的腿都变得模糊了。忽然我似乎觉得有两条腿在面前停下了下来,它抬了几次又放下,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快步离去了。那是女人的腿,年轻而富有质感的腿,健康发亮、绸缎般的肌肤让死气沉沉的空气四散飞扬。我恍惚中觉得精神一振,有股很熟悉的感觉驱散了困意,我揉了几下眼睛,举目望去只见暗淡的天空下,人群纷涌得如江水中活动的木头,那些长了黑毛的木材晃来晃去,似乎都是一个模样。的确有些东西被这两条腿轻轻搅了起来,如放久的果汁出现沉淀,一旦搅动便会新鲜如初。我不自觉地扯扯头发,再也坐不住了。火车还没有影子,我一跃而起,有意无意地那两条腿去的方向蹭。朦胧中似乎觉得那人穿的是一条黑套裙。可人潮如海,我的眼神也实在不怎么样,没看多久便放弃了。
“你看什么哪?吃了蜜啦!”阿三学着山林的腔调说,似乎很得意。
“说不好就别说。瞎操心,你就是个老太婆。”我极不耐烦地瞪他一眼,听他说北京话就像听驴学马叫。“怎么了?”我自言自语着,越想越不对劲。
“女人脱光了都一样,别瞎看了。”这翻话虽然是山林的特色,但阿三肯定看见什么了。
我突然把自己的烟盒塞到他嘴里。“应该找双臭袜子给你堵上。”
开往深圳的慢车终于极不情愿地来了,火车司机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大老远就开始鸣笛,即使这样月台上的人还是群狼捕羊似的,向车门发起前赴后继的冲锋。平时赶车,我都会事先判断车门的终点,抢占有利地形,然后不费吹灰之力的第一个冲上去,可今天我就是磨磨蹭蹭地不想动换。神经过敏!我暗骂自己一句,准备奋勇争先却发现自己排到了最后。我不甘心地再一次回头张望,顷刻间血压降至零点,像个踩了鼠夹而张皇失措的孩子,更像被悟空使了定身法的小妖,连表情都僵住了足足十秒钟。
她微笑着站在我身后,薄唇似夕阳在地平线上残存的最后一屡红光。她看着我微笑,有些局促,有点拿不准。刹那间我觉得天地升腾如幻,万物凝结成冰,只有这明媚的笑容是真实存在的。车站、人群、天上的乌云都游离出我的视野;旅行的终点、起点、连阿三的去向都苍白得近乎可笑了。这笑容我在梦里重温过多少回,又多少次地招来我对自己的咒骂和鄙视。而它一旦出现就好象可以推翻一切,验证一切。
北京爷们儿全文(76)
“精卫!”现在她就站在我身后,一屡长发绕过额头,随风飘着,飘着,几乎成了一条直线,黑色套裙裹着的两条腿,正是我寻觅良久的。此时她脸上已恢复了平静,倒是我半张着嘴,舌尖顶着上腭,似乎不如此脑袋就会失去一个支撑。我没记住自己是怎么接过精卫的包,又是怎样上的车。
“你——你结婚了吗?”记得这是上车后我的第一句话,真无聊!当时差点给自己一个嘴巴。
“我刚毕业。”精卫微笑着用小指挠了挠鼻子。“你的小鼻子真可爱。”我知道自己以前说过这句话,却又想不起什么时候了。
精卫说她现在于京郊通县的一座医院当医生,刚分配的,这回自费来广州旅游。她供职的医院非常有名,我早就听说过,以前还在那一带卖过烟呢。那里的大街小巷,饭店酒家我都特别熟悉,不过这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没在北京重逢,却大老远跑到广州来?天意!冥冥中可能真的有种神秘的、世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它制造悲欢离合、是人间奇迹的生产线。
“哪个科室的?”我说起话来昏昏沉沉,反应特慢。
“内外科我都学了,看医院分配吧。不过我最喜欢妇产科。”说着精卫有些不好意思了。
“那我可用不上了。”我开怀大笑起来。几个月我碰上一位老者,他颇感慨地告诉我:“妇产科的女医生都是女强人。”我断定老者的夫人肯定是妇产科的。
“可你太太能用啊。”精卫冲我仰着脸,小鼻子高高翘着。
“如果我不要孩子呢?”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那时我们没事就逗嘴皮子。
阿三这家伙上车时就找不到了,后来再没露过面。
在车上我们说说停停,往往只说几句话就都没词了,不得不重新思考新的话题。到后来我们便默默坐着,偶尔瞟一眼对方。幸好上车时就找不着阿三了,此时我真怕他会突然从一个角落里钻出来胡说八道。
想来我们分开已经六年了。我突然意识到,这六年的时光原来都是空白,那彻夜的无聊,淡淡的忧愁只是为了这一天。我把记忆挖空,把自己埋在沙土里,甚至向所有人表白:爱情就是瞎扯臊。可正因如此,我的心无法承受了,我感到气闷,扣子已经解开了好几个,天阴得厉害,真要下雨了。
深圳到了。
我提着包跟她下车,甚至把阿三的事忘了。在检票口,我塞给检票员十块钱,在检票员近乎哀求的目光下,我大度地摆摆手,示意不要票了。站外有不少工地,风越来越大,废纸雪片似的在脚下飞舞着。
“你真阔气,两室一厅就你自己住?”精卫兴奋地在房间里来回巡视。
“租的。深圳房价贵,我也不想久住。”我站在卧室门口饶有兴致地看着她。“你找什么呢?”
精卫巡视完毕,一脸轻松地坐下来。“有没有卫生间?”
我痛苦地摆摆手,她这样一说我倒真想去了。其实我并不想上厕所,是下身那玩意儿太难受,它时不时地间歇性膨胀着,好象有几根毛被拉锁夹住了。
出来后,精卫已经泡了两杯茶。“出门在外还带着茶叶。”
“我是医生。”精卫突然很认真地问我:“我觉得当医生挺好的,现在社会上是不是特烦医生?”
“劫道的不如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