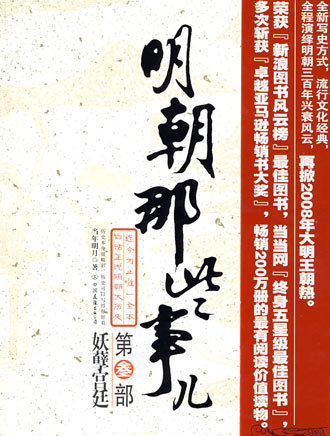北京爷们儿-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好哇!东南西北全让你玩儿遍了。”徐光很不屑,他没出过远门,在他眼里外地都是穷乡僻壤,是耗子不拉屎的地方。北京土著特有的优越感在他身上十分明显。
“听说,我们下个月就得去四川施工。”我想起出差就兴奋难耐。“走。”
“干嘛去?”
我拽起他往外拖。“喝两口,你们啥时分配?”
“有政策啦,我们学校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管分配。”
“什么意思?”
“叫他妈的双轨制,就是人多分不出去呗。”
“剩下的呢?”我没想到徐光会为找工作发愁。
“物竞天择,自己找地方。”徐光咂咂嘴。“有本事就上清华、北大,要不就老老实实地考个中专,我们这帮夹在中间的大专是傻 X。”
“你小子将来不会混得太差的,没准我还得求你呢。”我抬手拍拍他。
工作的第二个月我和玉玲给分配到川北工地。路过秦岭时,窗外黑漆漆的,只能听到列车穿越山洞的轰隆声。我白熬一夜,狗屁也没看见。
川北工程开工一年多了,工人也换了两三茬儿。基地就在小县城东边几百米的地方。
下了车,我大吸了几口气,山区的空气真新鲜,真想喊两嗓子。接站的徐姐跟见着亲人似的把我们接到基地,房间和床早准备好了。与我住一个房间的是一位吊车司机,徐姐说他明天才回来。
“听说你们俩刚毕业?”徐姐挺胖,嗓门也大。
“刚分来的,您还得多照顾照顾。”我忙着自我介绍。
“你们多深的文化!过几年大姐还得指望你们照顾呢。嘿?”徐姐偷偷拍了我一下。“你们俩是一对儿吧?”
“瞧您说的。您来工地多久了?”我赶紧转移话题。北京大姐念起两口子的经来,准没完。
“四个月啦!咱没能耐,儿子上高中,来外地不是能挣点补助吗?”
“活儿累不累?”
“不累,北京人都学奸了。苦活儿累活儿全是外地人干。你们是知识分子还能让你们干苦活儿?”徐姐整个一无线电,一句话能招出一堆。“你们先休息,队长他们明天才回来。”徐姐终于要打住了。“对了,可别乱跑,这儿的人说话都袅袅的,乱跑就丢啦。”
吃过晚饭,我拉着玉玲去逛街。北京的同志还能丢?
小县城很近,抄近路,穿过一条泥泞的小路就到了。傍晚的天空色彩明艳,落日象熟透了的小橘子,远山幻化成漆黑的阴影,阴冷的风从山里吹过来。玉玲不自觉地抓住我的手。
“有点冷。”玉玲直哆嗦,我把外衣给她披上。“我心里不塌实?这地方不吉利。” 黑漆漆的小城如罩着妖气的巨兽,那无数闪动的灯光正是怪兽口中泛着磷光的巨齿。玉玲茫然地望着小县城,越走越没有勇气,到后来竟不想去了。
“咱俩加一块儿也没五十块钱,抢就给他,怕什么?你是刚离开大城市,有点不习惯。”我挺坦然的。事后证明玉玲的感觉最终是对的。不听老人言和不听女人言都得吃亏。老人凭一辈子经验,女人凭天生的直觉。
县城很小,方圆不过一公里。唯一的百货商场早关门了,街道两边全是小吃摊儿。汤圆、麻辣烫、酒糟、担担面,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袋袋的大烟壳。街上没有路灯,每个摊儿上都点支小灯泡,可怜呐!萤火虫的屁股就那么点儿亮。路上泥汤四溢,泔水横流。没走多一会儿,皮鞋就成了泥坨子。在川北很久,我从没在地摊儿上吃过东西。因为我从未搞明白,他们洗碗的水是哪来的,或者根本就不洗,抹布擦擦了事。
“回基地吧,太脏了。”玉玲忍不住了。
“从那条路上绕回去,那边好象清静。”我领着玉玲躲躲闪闪,一蹦一跳地拐到另一条路上。这条路人少,黑乎乎的,挺渗得慌。
没走多远,我就听见刺咣刺咣的声音从假角传过来。“好象是敲破锣的声儿?”我问玉玲。玉玲摇摇头,也说不上来,我们循声而去。
街口是片几百米见方的小广场,好几十个大姑娘小伙子正在广场上跳舞呢。刺咣声是从一台俩喇叭录音机里传出来的。由于音量太大,喇叭劈了。广场四周拉着绳,几支二百瓦的大灯泡吊在四角,但广场中央光线依然很暗。舞者们狂舞猛跳,远远望去,人影婆娑,煞是热闹。
北京爷们儿全文(102)
“他们都穿着球鞋呢。”玉玲捂着嘴乐。
我果然看见垫着灰的地上,一双双绿球鞋扭来跳去,地面就跟起了片雾似的。“真够玩儿命的!”我笑着挽起玉玲。“想不想跟我跳一个?”
“我是北京人。”玉玲甩开我。“那边四川妹子盯着你呢,找她吧。”
我也看见了,人群里有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斜着眼瞅我呢。“大小姐眼睛真毒!人家是对外地人好奇。你在北京不是也瞅过老外吗?”
“你请她跳呗,人家高兴着呐。”玉玲嘴上不饶人。
“你受什么刺激了?有完没有?看你的男人多了,我说过什么吗?”我快让玉玲气疯了。
“那是你心里没我。”玉玲不知哪来的醋劲。
“回基地行了吧!”我甩手便走,此时已被她气得四肢乏力。我一直认为,自己不会跟女孩子呕气。可这玉玲软硬不吃,生熟不管,成心的。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依然没心思搭理她。倒是玉玲凑过来,“还生气呐?小心眼!刚才徐姐说了,队长要见咱们。”
“你就是小方吧?”队长拉着我的手,非常亲切。听徐姐说,队长三十来岁,是外地留京的大学生,在单位没根儿,一直不太得志。
“队长好!我是方路。”
“对,公司前好几天来过电话,说你们俩这两天就到。你肯定就是小周。”他又指了指玉玲。“这鬼地方不怎么样吧?”
“还找不着北呢。”我笑道。
“呆几天就知道了。马瘦毛长,人穷志短。在苦地方锻炼锻炼也没坏处。这样吧。”队长坐在办公桌后头,破桌子漆皮爆裂,早分不出颜色了,估计卖破烂儿也值不了五块钱。“小周是学统计的,先帮着管管库房,收发材料什么的,没事的时候就帮徐姐打打下手。她岁数大了,挺不容易。”看样子,队长还是个热心肠。“小方是小伙子,帮着跑跑基地和工地的联系,在山里步话机有时不管用。另外多跑几趟工地,熟悉熟悉业务,学点真本事。这回你们是实习,再开工号儿你们就是骨干啦。对了,没事帮着采购一下材料。”说着,队长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没意见就这么办?”
“听说基地有好几十号人呢,怎么没看见?”我说。
“铁路沿线还有四、五个点呢。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队长苦笑一下。“工地活儿不多,就是得多长几个心眼儿。刚毕业,过上两、三月就什么都明白了。”我和玉玲正准备出去,队长又把我们喊了回来。“等等,还得提醒你们一句,特别是小方要注意。”
“您说。”我挺奇怪。
“千万别跟当地人打架,年轻人火力壮,可得留点神。”
“您放心吧。”我笑了,这种事轮不上我。
“多说两句好。你别看这帮四川人都跟小地拍子似的,全是属马蜂的,惹一个能窜出一大窝来。咱们是外来的和尚,惹不起。”队长的表情非常严肃。“离家几千里都不容易。”
基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同屋的周胖子。这家伙不到一米七却足有二百多斤,双手将将摸着肚脐眼,脖子和脑袋一边顸,小寸头剔得楞青,要不是有两个耳朵,从后面看就跟肩膀上顶着个肉蛋似的。“兄弟,喝不喝酒?”周胖子见面就给我一巴掌。我笑道:“将就着喝。”
“好、好,又一个战士。”周胖子倍儿高兴,他指着另外几个同事。“这帮人,就知道穷攒钱。”
“胖子,我们可是老婆年轻孩子小,谁跟你比得了?”有同事大声说。
“他呢?”周胖子指着司机小张。
“我他妈又招你了?”小张推了他一下,可没推动。
“一帮穷人!喝酒能把人喝穷喽?人民政府是允许你们娶俩媳妇还是能生俩孩子?那俩钱还不够。”
“去,去。”徐姐给了他一巴掌。“瞎掰吃什么你?人家小方的女朋友还在这儿呢。”
“哎呦!我真对不起你,兄弟。”周胖子拉着我,一脸苦相。
“怎么了?”我被他弄得莫名其妙。
“我刚才还想,咱们工号好不容易来了个漂亮的女同事,咱不能让人家寂寞了,得追呀。我哪知道……。”周胖子摇头晃脑,特别可笑。“你得原谅我。”
众人笑弯了腰。我笑着说:“没事,思想问题可以原谅。”
“不行。”周胖子表演欲极强。“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得谢罪。”
“胖子,你少喝点行不行,明儿队长又骂你了。”徐姐转向我。“他就是跟你同屋的吊车司机,贫着呐!”
“我请你吧。”我对这活宝很有好感。
“不行,我不能让妹妹说川北工号没一个懂事的。”周胖子又冲玉笑笑。“妹妹,晚上让我们哥俩儿喝一顿。”
“我不管他。”玉玲不再笑了。她的确没管过我喝酒,反正我也喝不多。
当天晚上,周胖子真弄来一大堆鸡爪子、煮花生、麻辣香干。
“你的耳朵是怎么回事?”其实我早就发现了,周胖子的右耳很奇怪,整个就是块软骨,看起来又厚又硬。
“在摔跤垫子上磨的,好玩儿吧?”
“练过?”瞧他这一身赘肉,我不太信。
此时队长和司机小张走进来,小张指着胖子。“人家是全国亚军,退役了,到咱们公司发挥余热来了。”
“不地道啊,当着新同事的面揭我的短?”看来周胖子天生的贫嘴滑舌。
“又喝?明天还去不去工地?”队长假装生气。
“队长,咱得说清楚,我这不是偷着喝。人家小方大老远来支援咱们工号,队里请不起,我给人家接接风还不行?”周胖子的嘴不仅贫,还挺刁。后来我发现,运动员出身的都话蜜。
北京爷们儿全文(103)
“你找茬喝酒,还成了我们不仁义了?”队长气得哭笑不得。
“我没说队里不好,这不也请您喝吗?”说着周胖子给队长也满了一杯。
“我也是闲的,在屋里坐着好不好?碰上这么个刁民!”队长苦笑着被周胖子强行按下。“得,今天这顿酒,队里出钱。下不为例。”队长端起酒杯。“可有一样,你小子别把小方灌多了,人家刚毕业……”说着,队长向女工宿舍扬了扬下巴。
“您放心,咱心里有数。”周胖子举起酒杯。“干!”
那天我喝了将近一斤白酒,脑袋微微有点沉,周胖子却四仰八叉地倒在床上,来回来去地念叨耳朵的事。
队长没喝多:“下回请甲方吃饭,你得去。”
第三章:川北女人
毕业前我认为工作是件难死人的事,在川北熬了两个月发现不过是闲聊淡侃,在工地干活更省心,一天里能睡上半天。正如徐姐所说,施工公司的正式职工没有卖苦力的,脏活儿累活儿都是民工干。反正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民们大多以苦为乐。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提着步话机,跟在老技术员后头瞎转悠,看见谁偷懒,就吆喝牲口似的骂几句。没半个月,我就独自上岗了。
偶尔队长让我去广元、江油采购配件和生活用品。我大大方方地玩起了公费旅游。三个月下来,我就学会了骂民工、搓麻将、开虚票,该学的全学了。
我曾在公司听说川北工号上有五十多人。可待了几个月,最多才见到二十来个。有一回,我问周胖子是怎么回事?周胖子这人是嘴对屁股眼,直肠子,当即嚷道:“学生蛋子狗屁不懂,听说过吃空额没有?”
“电影里说过。”
“知道就完了。这是老区,耗子饿得都掉眼泪。稍微有点道行的就不来,可工地还得给人家开工资。懂不懂?”
“国民党的空额是官吃兵的,咱们这儿是兵吃官?”
“不是吃队长的,他哪儿来的钱?咱这儿是吃党的。明年我也托人回去。”
这几个月没少长见识,日子也算顺心。只有一件事让我不痛快,甚至感到沮丧。基地里人来人往,耳目众多。我想和玉玲亲热亲热却总找不到机会。即使有了机会也是干着急,玉玲对那事儿兴趣不大,经常是高悬免战牌。可我不行,有几次我猴急得想带她出去找旅馆。“早晚都是你的,瞎着急。”时间一长,玉玲的所有精神安慰全苍白了。
当时我以为玉玲比红玉害羞,后来才知道有性冷淡这个词。没办法我便从周胖子处找黄书看。周胖子这家伙吃喝嫖赌样样都精。牌局少不了他,喝酒更缺不了他。有好几次这小子深夜三点多才回来,一脸奸笑,心满意足。往被窝里一钻,呼噜就震天动地。我知道他干什么去了,百爪挠心,又不好意思深问。
第一回洗澡时,周胖子跟见了宝似的围着我转了好几圈。
“瞎瞧什么?没见过?”我清楚他在看什么。自从和红玉有了那事儿以后,我就知道自己这玩意儿是男人梦寐以求,女人苦苦求索的,中专那几年就不再掩饰了。同学们理所当然地把这事当成笑料。可我也不怎么在乎,再过几年他们都会自惭形愧的。
“我的天!”周胖子晃着脑袋,低头又看了看自己的,嘴里光剩下出气了。“妈的,你是人吗?”
“少见多怪。”
“我没见刚,我真没见过!”周胖子一直摇头。
“你傻,知道武则天吗?史书上说,武则天天下选妃,最后找着一个男的,大如剥兔。”我嘿嘿笑了两声。
“剥兔?那时候的人就说英语啦?”
“包了皮的兔子。”
“啊?”周胖子张大了嘴,半天没合上。
川北、陕南的山区是中国最贫穷的几个地区之一。这一带山高林密,地荒人蛮,本是道士们采药炼丹的地方。这里没有矿产,土地更是稀少而贫瘠。山区的贫困闭塞是城里人无法想象的。偏偏山区的人口密度又大得出奇,俗话说“省灯费炕席”,人们无事可做,只能关起门来生孩子。虽然实行了计划生育,但天高路远,一家子四、五个娃娃的现象非常普遍。孩子生出来却养不起,于是就卖。我听说前些年在这一带几百斤粮票就能换个大姑娘,而且姑娘和家里人保证欢天喜地。我一直在怀疑,电影里卖儿卖女的悲悲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