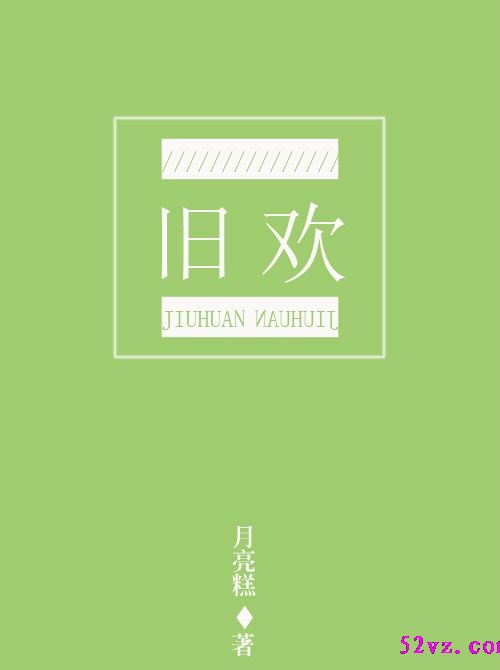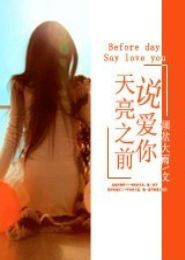水月亮-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湄停止了哭泣,却不知说哪句话才对。高其昌把她拉起来,又从地上拾起装着钱的信封递了过去:“钱你收好,可以不必还。这几年,咱们处得挺好,以后,该怎么做,你看着办吧。不过,我还要说,我是真喜欢你。如果我们能……你让我怎样我就怎样。”他把信封放在林湄手里,然后拉开了门,把林湄推了出去:“走吧,孩子在家等你呢。”
林湄慢慢地走出大楼,上了出租车。雨点“啪啦啪啦”地打在车窗上,很快就让这世界变成了一片汪洋。
三十七
九月下旬的傍晚,林湄背着小健出了北京车站,站在路口上,望着匆匆的人流,她觉得自己如同一粒灰尘。这粒灰尘不知道该坐几路车才能到达地处通县的胸科医院。远远地,她看见有个交警,就走过去问路。还好,北京的交警热情而又耐心,她在正确的指引下搭上了公共汽车。
下车时,天已经黑透,儿子趴在她的肩膀上已经睡着了。她怕他着凉,就摇醒了他,不过此刻,她还担心没地方投宿。
来之前,跟朋友打听过,最便宜的旅店就是小胡同里的民居,住一夜大概只要10元钱。林湄就沿着街边找这样的胡同,还好,几乎每间房屋的墙上都用白的或红的油漆刷着“旅店”的字样,她就摸索着找到一家,进了院子,看看所谓的小小的客房还干净就决定住下了。
房东很快送来了被褥等物,林湄给小健洗了脸和脚,让他在炕上躺着,然后从旅行袋里拿出干粮,又用开水在旅行杯里冲了奶粉。晚餐就这样解决了。林湄跟房东问好了医院的情况后,就躺在儿子的身旁,逗他随意说话。
电灯是用一根电线接过来挂在墙上的一根钉子上的,黄晕的光照着屋里看不出什么颜色的摆设。林湄恍然进入了电影里演绎的刚解放的农村的岁月,自己也变得虚幻起来。几只蚊子和蠓虫窥见了光从门窗的缝隙里钻了进来,围着她俩嗡嗡地叫着,让人无法入睡。林湄只好又起来找到一盘蚊香点上,熄了灯。
在这样的世界里,她居然做了个不好不坏的梦,梦见她又恢复了往日写字和上课的时光。
第二天6点钟,也没吃饭,她就背着儿子去街对面的胸科医院门前排队挂号。等到8点,医生才上班。她排到25号,医生给小健听了听肺,又看了她带来的胸片后说:“如果在这儿治,还需要住院全面检查,但是我们没有治小孩病的经验,药量的使用恐怕掌握不好,倒不如带孩子去儿童医院,那样比较稳妥。”
林湄只好又领着小健回到住处,拿了行李乘公共汽车返回了市区。辗转打听到了北京市儿童医院时,已经是上午11点多了,她带着儿子在小吃店吃了东西后就进了医院,重新开始挂号住院那一套手续。
交了1万元的住院押金,一切手续都完毕后,已经下午2点多了。林湄拖着小健、脸盆、拖鞋和病号服一大堆东西跟着护士进了病房。等找好了床位后,值班医生走过来,告诉她一大串的注意事项。这时,林湄有点傻了:孩子要在病房单独住,家长不许陪护,每周只有周二、周五下午两次探视时间,每次20分钟。小健也听明白了,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毫不放松。林湄就先陪着儿子坐在那里。又过半个小时,护士催了三次:“请家长快点离开。”无奈,林湄只好提着旅行袋向外走,小健哭叫着追了出来,没走几步就被护士拦在走廊中间。林湄回头看着小健穿着肥大病号服的细瘦的身体在蹦跳着喊“妈妈”,心里发酸,抹了把眼泪,横了心,跑了出去。
她走了几家旅店想把自己安置下来,可看着差不多能住的都要30元一天。旅店门口负责登记的阿姨知道她是从外地来给孩子看病的,就建议她住地下旅店――每天只要12元左右,如果加上吃饭不过超过25元。钱要花在看病上,能省就省。
地下旅店潮湿异常,充满着霉味。走廊里的灯整天亮着,是渴睡的老人的眼,浑浊的像蒙着层灰布。窄小的房间,刚容得她转身,半空中全是架设的各类管道。在桌角,她发现了一只散步的蟑螂。如果是在家,她早就惊叫起来,儿子也会跑过去替妈妈消灭那个害虫。而此刻,她却觉得自己有了个旅伴。
躺在床上没事做,林湄开了桌上那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图像倒还清晰,只是只有六个频道,没什么感兴趣的节目。她就任它开着,胡思乱想起来。
三十八
再去医院的时候,小健已经开始新的治疗。由于不是探视时间,林湄只见到了姓周的主治医生,那是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纤瘦的女人。周医生简单地说:“进行了全面检查,排除了肺结核,但是还要进行抗炎治疗。孩子肺部有两块不明阴影,不能确定是什么。要看情况的发展,如果没有进展就要进行纤维支气管镜治疗。现在用的是最好的消炎药――克拉霉素。给我留个电话,有情况我再联系你。”林湄把传呼号写给她,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回到住处。
林湄是第一次到北京来,她曾经无数次地向往过北京的名胜,却绝没有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同它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既然来了,就走一走吧。可她不敢去那些要门票的地方,比如故宫和颐和园,就只好买了一张地图,顺着街道一路走下去。她去了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在北京烤鸭店和民族文化宫前面稍做停留,又逛了长安商场和百盛商场,别的地方就没再去。
大部分时间,她把自己困在地下室的床上,一点一点地回忆过去的时光,末了,她给自己下了个定义:没劲。可没劲又能怎么样?又不能重新活一回。她想饿了,就爬上地面透透气,买一碗刀削面充饥。
第一次探视小健的时候,林湄又哭了。小健的身上全是蚊子的亲吻留下的红包,小健说他数过了,有60多个。林湄气得冲进了医生值班室,让他们给一个解释。一个小护士说:“没办法呀,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蚊子就是咬他,我们怎么办?”
林湄怒了,许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发怒,她嚷起来:“你说的是什么屁话!孩子交给你们了,就让他受这样的罪吗?我要找你们领导。”她气极了,顾不得什么文雅。
小护士不敢出声了,她没料到看似文静的林湄会这样暴躁。
周医生拿着一大堆治疗单走了过来,拉住了林湄:“生气没有用的,医院的条件也不是太好。我们会尽力再想办法的,这种情况不会再出现的。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孩子的情况。”
林湄抹着眼泪跟她进了另一间办公室。
“治疗有一定的进展,但纤维支气管镜手术还是要做。这个结果决定今后的治疗方案。时间初步定在下周一,上午10点钟的时候你过来签字。”
“有危险吗?”
“没事,只是需要孩子配合。因为要从鼻子下一根细细的管子到肺里,可能会有点难受。”
林湄想着,就要知道小健的病况了,就点头答应了。她给小健留了一大堆水果和零食,看着他吃了一些,才无奈地离开。
三十九
周一的手术进行得还顺利,周医生说那阴影是由于积液的长时间滞留引起的肺叶粘连。但是,这一次只是初步治疗,这样的纤支镜手术大概每周要做一次,什么时候会好也说不准。还有,你的预交金快用完了,还要再交5000元。
林湄先喜后忧,喜的小健的病有希望了,忧的是这意味着她要在北京呆上那么一阵子,也意味着钱一定不够。到哪里弄钱呢?
出了医院,她没着街道向住处走去,忽然发现街边有一家快餐店贴出了“招服务员”的告示。她灵机一动:自己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打打工给儿子赚点营养费。这样想着,她就推开了店门。
小老板同意林湄在这儿干,主要工作就是烙馅饼。工作没什么技术,面有人和,馅有人拌,她只须站在窗口烙饼就是了。每天的工资是二十元,管吃不管住。
林湄的厨艺并不差,又有上写作课练出来的站功,所以第一天上工就令小老板十分满意。
做了一周后,她开始感到累,每天十个小时的工,令她的腰隐隐作痛。做到第三周的时候,医院的费用又要交了。而她口袋里的钱已经不多了。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打电话回家里要吧,婆婆又要犯愁,亲戚们都已经借过一遍了。她边想边烙饼,一不留神手指被滚烫的油烫了个大泡,可那钻心的疼痛在她的愁烦里已经不怎么痛了……
收工的时候是傍晚六点,已经是十月下旬,天明显地凉了。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一条磨得发白的牛仔裤走在路上的林湄依然洒脱。路过一家练歌房的时候,坐在门口台阶上的一个青年男子向她吹了声口哨。她皱皱眉,那男子继续轻佻地指着墙上一张广告说:
“招服务员呢,小姐要不要试试,高薪,有小费。”
林湄瞪了那男人一眼。
“哟嗬,挺有性格呀。好!”
林湄生气地走了过去。
进了地下室的客房,她把自己摔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还在生气。转念又一想,和那种人犯得着么?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林湄又从练歌厅前经过,她注意地看了一眼墙上的广告。
晚上收工的时候,她又看了一眼,那男子还在,好像对她还有印象,倒冲她友好地笑了一下。
四十
转眼,小健已经做了三次纤支镜术,情况很好,X光片显示阴影只有手指甲大的那么一点点了。交了欠费,林湄的手里已经没有钱了。她好生的难过。
走回快餐店的时候已经三点多了,离晚上的高峰期还有一段时间,可饼馅还没有拌,老板吩咐她去做,她只好系上围裙忙开了。
那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日子,食客特别多,她的腰也不听话地痛得厉害。这是她在一次人工流产后留下的病根。这疼痛使她不由得恨起那个远在大洋彼岸的男人。可是恨有什么用,这就是她的宿命。她不得不坐下烙饼。小老板见了,好生的不乐意,嘴里叨叨咕咕的,可由于人多,也没说别的什么。正忙的时候,林湄的传呼机忽然响了,她放下饼夹一看,是个挺陌生的当地的号,但又不是医院的号,她就没着急回。过了没一会,又响了。小老板嫌她忙乱,就接过她手里的饼夹子,催促着:“越忙越有事,快去快回。”林湄扯下围裙,跑了出去。
小店对面就是公用电话亭,林湄拨通了那个号码:“请问你是哪位?”
“是林湄吗?我是彭堃,听说你带孩子在北京看病呢。我恰好出差在北京停留两天,怎么样?孩子和你都好吗?不介意我过去看看你吧?”
浓浓亮亮的嗓音雷一般击中了林湄。她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隔了好半天才拍着脑门说:“彭总?我们还好。您太忙了,别过来看我了。”
不知怎么,林湄觉得手有点抖。
“没关系的,公事办得差不多了。告诉我地址,我这就过去。”彭堃的嗓音显得特别的温情。
“不……不要了。”林湄突然觉得不应该让彭堃看到自己糟糕的样子,就支吾着拒绝,“地方不大好找,别过来了。”
“那怎么行,你别忘了,你还是我的员工呢。说吧,在哪儿?”
让他到哪儿呢?去地下旅店岂不更糟?她只好说了快餐店的地址,并说自己会去接他。
回到店里,林湄有些魂不守舍,自己现在这样子还见得了人吗?这一走神,便出了错,刚烙好的一张饼掉在了地上。小老板生气了:“你今天是怎么搞的。能干不?干不了,说话!”
林湄忙陪着不是,心里也很气恼:“干得好,没见你发奖金,差这么一点就挨骂,还不如去练歌厅赚小费呢!”这样的想法一跳出来,林湄自己很是吓了一跳,这是那个自命清高的,不与丁薇薇、单小霞之流同流合污的林湄吗?她真有点不认识自己了。
过了半个多小时,客人渐渐少了。林湄坐在小木凳上休息了一会儿,忽然听小老板说:“怪事,坐奥迪的大老板会到这里找饭店?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林湄忙抬头向外面看去,西服笔挺的彭堃正站在快餐店对面向周围张望着。
四十一
看到林湄的样子,彭堃真是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林湄会从快餐店里出来,更没想到他眼里那个月光温泉般的女人会是现在这副样子:往日那披在脑后的柔亮的长发打成一条辫子,虽然还整齐,但一点光泽都没有;原本亮泽的皮肤也是晦暗的,嘴唇有些苍白。她上身套一件有点松垮的黑色圆领T恤,袖口沾着一些油渍和干面粉;下身是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也满是油点子;一双白色的旅游鞋踏在她的脚上,却蹭了一些煤灰在上面。
林湄一见他的眼神,先就自嘲地笑了,然后她握了一下脸,问:“怎么?彭总,不认识我了吗?”
“你不是带孩子看病吗?怎么打起工来了?”彭堃还是不能相信眼前的事情。
“是呀,钱不够用了,就只好打工挣回去的路费。”
“钱不够用,为什么不跟我说?”彭堃咬着牙有些发狠地问道。
“你看,我是你说的那种随便跟人家借钱的人吗。”林湄笑了一下,拍拍自己的胸膛,“没关系,我有本事着呢。你可别以为我只会写文章。”
“天,这怎么是你应该做的事呢?打工,你丈夫干什么呢?”彭堃摇摇头,又点点头,眼前的女人还是那么开朗,还是那么自信,他真的相信这是林湄,也真的心疼了。
“他也打工,只不过是在美国。我们是真正的同志――志同道合。”林湄居然调侃起自己来。
那边又来了客人,小老板冲着外嚷着:“林湄,磨蹭什么呢,来客人了,没看见嘛!”
“哎,稍等。”林湄回过头喊着,转过身对着彭堃说:“彭总,你看到我了,赶快走吧。我不能请你吃馅饼,这也不是你来的地方。回C市我再跟您聊,成吗?”说着,林湄就要走。
彭堃拉住了她的手,这一次,他的疼惜真的写在脸上了:“不行,你跟我走,你不能干这个!”
林湄没料到彭堃会这样说,这样做!
小老板有些恼了,也冲出来拉住了林湄的另一只手:“快点干活去,当心我扣你工钱。”
林湄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拉着,一时间倒不知向哪个方向使劲好了。
彭堃见小老板不松手,就也喊道:“松手,她不干了,你另请高明。”
“不干了?这功夫你让我上哪儿找人去,您跟我逗呢,是不?”
“不,我再说一遍,你听清楚了,她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