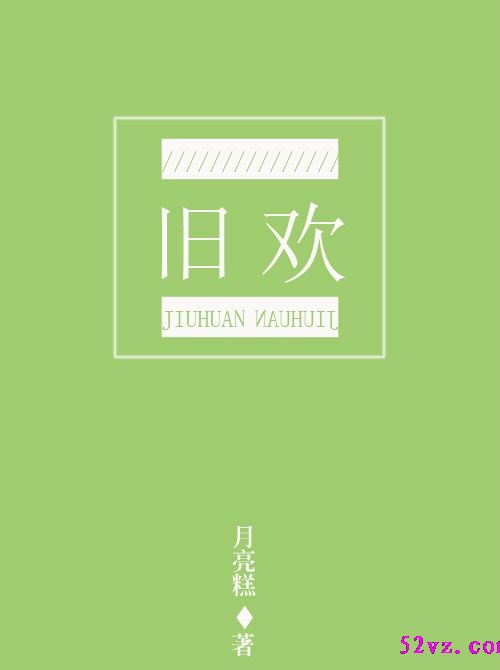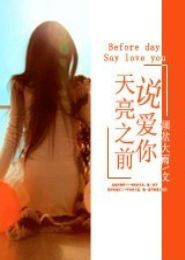水月亮-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彭堃没有进屋,叮嘱林湄好好休息后就赶忙下了楼。一路上,他一直担心,也不知道林湄进屋后会怎么样,会不会吐。
林湄的酒量一向不错,这一次她却觉得有些醉了。胡乱地脱了外衣,她接了一大杯凉开水咕咚咕咚地灌下去,清醒了许多。今天,小健在奶奶家住,屋子里更显得特别的宁静。她侧身躺在床上,没来由地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这委屈像一团海藻将她包裹了并缠得紧紧的,让她透不了气。泪无声地旋下,她先是偷偷地揩抹,可不知怎么,她止不住自己的泪。它们潮水似地越涨越高,她的鼻子塞住了,她的枕巾湿透了,她那么无助,从来都觉得自己付出的是有价值的,可自打从北京回来后,她却把所有的过往与挣扎都否定了――她为什么就不能活得快乐些?这样的苦,还不都是她自找的?
鼻子塞得难受,她只好披衣下床,绕到阳台向外面的马路上望。夜正深,路就显有些窄,她看见车灯一闪一闪地近了,又近了,就觉得自己其实一直就是在这样的狭长幽暗的小路上行走,没有人帮他,而她却走得挺快乐,当有车擦过时,她会傻傻地开心:我和你一样走夜路,我不用灯。而一但有车在她的身边停住,问她是否需要帮忙,或者不由分说把她拉上车,让她轻松一段,又把她甩下继续走自己的路后,她反倒觉察到了异样的孤单,觉得这样的路她居然走不下去了……
悬了一夜的心,第二天一大早,彭堃就忍不住把电话打到林湄家。电话铃响了好一阵才有人接,是林湄低柔的嗓音。
彭堃没敢多说话,只是提醒林湄下午还要去开发区新设立的分公司,看看那边需要怎么进行宣传。其实,林湄是可去可不去的,但是他一是特别想见她,二是觉得应该跟她说点什么。可是说什么呢?他还没想好。
四十六
林湄再次出现在彭堃面前的时候,是一付弱不胜依的样子:淡粉色的羊绒短大衣镶着毛茸茸的皮草领,米白色的羊毛长裤在上衣的衬托下显出白领女性特有的知性和温暖。她的眉毛微微地蹙着,皮肤显得有些干,像是一块刚刚挤出了水的海绵。
彭堃冲他笑了笑:“还好吗?”
林湄略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两个人就上了车。坐在后座,林湄感到腰酸腿软的,昨夜酒的余威依然霸道地占据她的身体。她把车窗嵌开了一条缝,风从车窗旋进来,旋乱了她的长发,飞满了她沉静得一如潭水的脸庞。过了一会,她感到眼皮有些发沉,便放斜了身体倚在靠背上想再睡一会儿。可是,睡眠却并不买她的帐,扭捏着不肯出场。
淡淡的烟草味从前面飘过来,她知道彭堃并没有回头却已把关切系在她的脸上,他问:“能睡着吗?”她摇摇头,无力地笑了笑,这一次她从他的声音里真切地听出了久违的疼惜。
分公司到了,他们一前一后下了车,进了卖场。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换着想法。还没看到一半,林湄的电话响了。她边接电话边向一边走,彭堃听得电话里是个男声,心里就不舒服起来。
隔了一会儿,林湄回到这边,抱歉地冲彭堃一笑:“不好意思,彭总,公安局政治处来电话,他们刚刚联系好了一个基层所,要我过去采访。所以,还得麻烦您把我送到那边去。这边的事,我回去先写一个简单的宣传方案,您看了再商量吧,可以吗?”
彭堃不好说什么,只好答应了。
林湄走后,彭堃自己又看了一会儿,觉得心里乱糟糟的,等司机回来后,也回了公司。晚上,一个外地的老朋友去省里,正好在C市歇脚,顺便来看他,因为没事,他便留对方吃饭。因为是私交,只有两个人,他就把朋友带去了“梅竹轩”。
两个人浅斟慢酌,吃得快差不多的时候,听得隔壁房间来又了一伙人,有男有女的。男人的嗓音都粗犷嘹亮,女人的声音却清亮柔媚。他觉得这女声很耳熟,略一思忖,他肯定那是林湄。果然,他听得那边谈的都是公安局办案的事。他想过去打个招呼,可又忍住了。正好,朋友提议买单回酒店休息,他就心事重重地跟朋友出了门。
四十七
这是一个晴朗而冷冽的夜晚,天上没有很多的星星,淡金色的半月在云彩里穿行着,像一只摇摆不定的小船。彭堃把朋友送到下榻的酒店告了别,就把司机打发了。他不想回家,一个人开着车在街上兜着,鬼使神差般地,他又绕回了梅竹轩。看看时间刚过了半个钟头,想来林湄他们不会结束,他就坐在车里等着。
等了又有四十多分钟,他看到一伙人从店门出来,陆续上了停在外面的警车,林湄是最后出来的,显然她没有上车的意思,跟车上的人说了一些话后就沿着路走下去。夜色里,她修长高挑的身材依然惹眼。彭堃想了想,发动了车,跟在后面。快到她身边的时候,彭堃撳了下喇叭。林湄略有些吃惊地回过头,看清是彭堃的车后,就微笑着走了过去。
“回家?我送你吧。”
“不,我想自己在街上转转。您走吧。”
彭堃把头伸出车窗外,看了她好一会儿:“不早了,你一个人在街上转不好,还是回家吧。”
林湄挑起了眉毛:“您对每个员工都这么好吗?别耽误您了,我习惯自己走路。”
“是不是每次喝了酒,你说话都这么冲?”彭堃有些恼火。
“您怎么知道我喝了酒?”
“不仅知道这个,还知道是和一群男人喝的。”
“真好笑,您跟踪我了?”
“不是跟踪,是意外。你一个女人不要老在外面喝酒。”
林湄“哦”了声,有些刻薄地笑了起来:“大哥,这句话你说有点不大对劲吧?这口气倒像吃醋的丈夫抓到了夜归的妻子。”
彭堃有些发窘,顿了一顿,他说:“对不起。不过我有话想跟你说,前面有个咖啡吧,咱们去那里坐坐。”林湄略一思忖,拉开车门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他们一前一后进了咖啡吧,在一个包间里落了座。房间不大,只有六个平方吧。墙上的灯放射着橙黄的光芒,是弯弯的一牙新月。草绿色的台布上印着乳白色的抽象的条纹,看来看去都像是女人身体的曲线。一只圆肚子的花瓶立在桌子上,里面插着几朵郁金香。悠扬而略带忧郁的萨克斯的音韵在天花板上飘来荡去。这首名为《回家》的曲子,落在林湄的耳际却变成很老的一首歌――《月儿像柠檬》。她的嘴唇一弯,一个虚浮的微笑便也升起在她的脸上。
他们面对面地坐了。彭堃点了蓝山咖啡、开心果和西瓜籽,又问林湄要点什么。林湄侧着头想了想,点了“烈焰”和两瓶洋啤酒。
隔了一会儿,服务生端着托盘走了进来,他先把一只玲珑剔透的浅口酒杯放在桌子的中央,一朵红色的花朵状的香味蜡烛正袅袅地吐着香气,接着,咖啡和啤酒也摆上了桌子。那杯名为“烈焰”的咖啡是掺了白兰地的,打火机一点便腾起一团红中带蓝的火苗,映得林湄的脸也有些诡秘。彭堃不晓得咖啡还有这样子喝的,便也笑了,像是一个长者欣赏孩子的恶剧后,那种无可奈何的牵就的笑。
林湄的咖啡喝完了,就又在玻璃杯里斟上了啤酒,啤酒花像假日的海浪懒洋洋地沿着杯壁流了下来,到了桌子上好一会儿,泡沫才消失不见,而杯子里的泡沫则劈啪劈啪地响着,像是在为逃走的泡沫举行着欢送仪式。
“彭总经常到这里来吗?”林湄端起酒杯摇了一会儿,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不常。一些喜欢这种气氛的客户有要求的时候才来……这几天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谈谈。”
“好啊,谈什么?是工作吗?计划书,明天我会按时交出的。”
“不是工作上的事。做为朋友,想给你提点建议。”
“那更好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你不应该喝这么多的酒。不应该这么晚回家。”彭堃又想了一会儿才开口。
“是呀,您说得对。那么我应该干什么?我理想的职业是全职太太,可是生活没给我这样的机会。再说,很多女人都没有您太太那样幸运。”
“这我知道,可是喝太多的酒伤总是伤身体的。”
这句话一下子勾起了林湄这段时日以来的委屈,她咬了咬嘴唇,把一杯啤酒干了,然后她美丽的凤眼眯了起来,里面就盛满了泪光。她就这样盯着彭堃足有十秒钟:
“您心疼了,是吗?”她的眼神里又搀杂了几许不确定。
为了证明这种不确定,她把上身挺直了,向着彭堃倾斜过去。
这次,她的眼神里更多的是等待,等待对方确定她的猜疑。彭堃有些愣神,林湄的眼睛里有两簇小小的火苗在闪。他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的感情说出来,可那两簇火苗实在是太亮了,晃得他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于是,那美丽的凤眼合上了,两颗泪珠顺着睫毛滴了下来,落在桌子上叮叮地响,林湄长叹了一口气,把她的唇压在了彭堃的唇上,湿润而缠绵的吻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宰了这一对男人和女人。一开始,他们吻得生疏,吻得犹豫,随着心跳的加剧,四片嘴唇便也熟识起来,舌尖也开始灵活地探寻彼此的热度,紧紧地纠缠着不愿放弃这种原始的交流……
过了好久,两人才从梦境一般的世界里退出来,林湄用手扶着自己的额头,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随之她又抬头望着彭堃,对方也正含笑望着她。
“不是在做梦吧?”她还是不大相信,继续发着呆。
“不,我想你,而你也想我,这是真的。”彭堃站起来坐到林湄的身边,把她廋廋的肩膀揽在怀里,使劲地抱了一下:“别怪我,我躲着你是因为你太年轻,太美好。而我,都这么一把子年纪了。”说完了,他的唇又压下来,不过是轻轻的温柔的一触,就好像林湄是一块薄薄的水晶,稍加一点力就会破碎。
林湄把头埋在他的胸前摩擦着,就像一只小狗在跟主人撒娇。
他的手便浮上她的秀发,轻轻地摩挲着。
房间里游荡的音韵更加渺茫,如丝如缕地将两个人缠绕起来,他们真想就此结出一只茧子,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
窗外,泥金似的半月舒适地停在半天云里,恬静而美好。
第一章 圆月满西楼
我相信:人的成长源于心灵的成长,心灵的成长源于对爱的寻求。其实爱,很简单,它是一个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但听从心灵的召唤;却是一个艰难跋涉的过程。
――题记
第一章 圆月满西楼
一、
午后三点的阳光慵懒地从薄纱窗帘的孔隙间溜了进来,泻在窗前那张布满紫色和草绿色条纹的布艺沙发上。林湄正漫不经心地挑拣着布块。
这时,紫水晶串起的珠帘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林湄微笑着站起来迎了过去:“是陈姐呀,几天没见,皮肤又白又嫩,有什么偏方也介绍我试试?”
圆圆脸的陈姐一下子捉住了林湄的手腕:“呀,这只手镯好时尚!配你这件米咖的棉裙真有味道!”
林湄忙除下乳白色的手镯:“昨天上辅料商店顺手牵来的,是蜜蜡的,现在正时兴呢,您要是喜欢就转给您吧。这类东西我也是太多了!”
陈姐伸出手,可戴了半天,也没戴上--她的手掌太宽,只好失望地重新戴回了林湄的手上。
“你的手腕又细又白,戴上这种宽镯真好看,让人嫉妒!”她皱了皱眉。
“哪儿呀?我倒是真想长几斤肉呢!可算命的说了,我福薄。”林湄用她那带着白色宽镯的手撩了一下垂在眼前的发卷,俯下身,从地下的一只白藤筐里拿出一块白色的棉布,“上次您订的抽纱桌布昨天刚完工,您看看,还满意吗?”
陈姐挑剔地端详着那块米白色抽纱,边缘钩缀着花朵的桌布,笑容堆在眼角,那本就不大的双眼更小了:“林小姐,您这手艺真是没得说,那回您给我加工的两套杯垫迷死了多少人呢!难为你怎么想的,做出那么可爱的小东西!”
“嗨,我呢,是真爱这些小东西,就是不赚钱也爱在这上边下功夫,还多谢您常照应着。”
林湄边递过印着“花样年华”的包装袋,边接过陈姐递过来的200元钱:“自己做的东西就像自己的孩子,真舍不得让它走呢。”她的眼角又掠过一丝温柔。
客人走了,林湄重又坐到沙发上,边继续着刚才的挑拣,边嘀咕:“小惠这丫头,请两个小时的假也该回了。。。。。”
她挑了明亮的橙红色和黄色棉布,再挑了同色系的一块格子布。她的眼前出现了一大竹篮弱不禁风的虞美人--这样的布艺花朵实在是惹人怜爱呢!林湄的眼前又幻出了一大捧蓝色的娇嫩欲滴的玫瑰――花朵遮住了送花的人,林湄先是在那捧花前喘不过气来,接着是在送花人的吻里喘不过气来。一想到这儿,她的眼神就有点迷离。
“铃……”身边的手机突然响了。她边把挑出来的布卷成一卷;边接听电话。
“你好,哪位?”
“小湄,是我。”电话那边是她熟悉的男声。林湄像一只弹簧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怎么可能?你不是后天才回么?”
“不是后天,是今天。我现在上海机场,大概3个小时后就可以好好地抱抱你了。怎么?不想我么?”
“天!!大哥,你总是这样让人惊喜。可是,你回来不先回家么?大姐不知道么?”
“就是要你惊喜,否则你一定会觉得生活没有色彩,也该讨厌我了。你别急,别急,我谁都没有告诉,下飞机就坐出租车过去……你也别来接我,就在店里等着。我想死你了,记得千万别走开!”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林湄的脸上漾起了红霞。她把电话丢在一边,抱着肩膀在屋子里走过来又走过去。彭堃去欧洲刚好半个月,她的日子也懒散了半个月,有时她真觉得他不会回来了,因为在梦里总是看不清他的脸。
正踱着,“哗”,帘子又唱了起来,小惠一阵风似地刮了进来:“林姐,我没超时吧,才路上塞了好长的一队车,真担心呢!”
林湄笑了笑,边将刚才挑出的布放在桌上,边把自己的设计写在了记事本上:“就照这个做吧!我走了,活儿别做粗了。”
“行咧,你放心吧!你带出的徒弟不会给你丢脸的。”小惠挤了下眼睛,抓住林湄的两条胳膊把她推到门口,“快走吧,别去晚了,小健又在校门口等。”
林湄跨出门,好大的太阳劈头盖脸地将她罩住,她情不自禁地眯起了眼睛,立刻从包里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