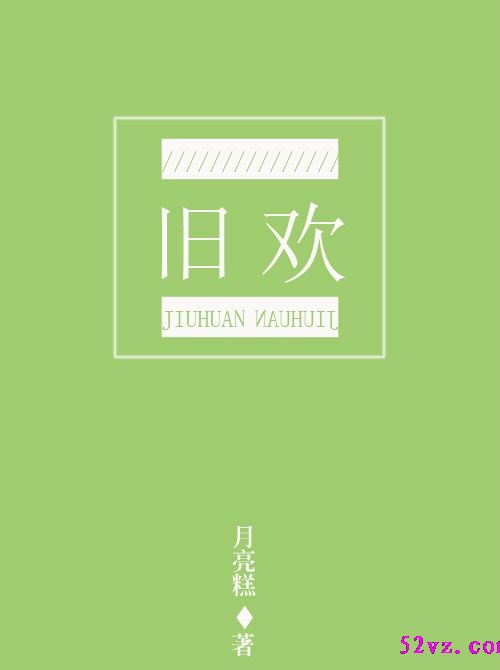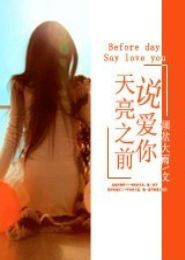水月亮-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湄没期望自己会再爱,不过,找个合得来的男人渡过下半生总是好些,对成文斌,她有些失望,但她不讨厌也就是了。
三个月后,成文斌提出结婚,这是林湄期望的结果。林湄想,通常男人把婚姻看得很重,如果他要娶一个女人一定是因为爱,这就足够了,虽然这三个月在她心里依然是一张白纸,所不同的,只是加注了时间的符号,但是婚还是要结的,女人总要嫁人的,嫁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要胜过嫁一个你爱的男人。
她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刘云婧。刘云婧瞪大了眼睛,叫了起来:“你是不是疯了?你爱他么?”林湄摇了摇头:“爱已经不重要了!我爱得还不够嘛?世间到处都是爱而不能的悲哀。我再也不想招惹什么爱情了。没有爱,也许更好些。再也许结了婚就会爱了呢。”
“哎,你不是想做第二个李双双吧?”
李双双?林湄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女主角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征服了男主角的。一想到这儿,她反倒有些兴奋,让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变得温情脉脉,也许更富挑战性吧。而且恋爱和结婚又有什么不同呢?不过是结束的程序难易不同而已。况且,她有几十年的时间来涂抹婚姻这张白纸,为什么她不能比别人涂得更美丽些?
这种选择也许很荒唐,但她决定冒险。
春节刚过,林湄和成文斌开始筹备婚礼的事。这是他们认识的第五个月。成文斌把一切事务都托付给母亲,林湄的课并不多,所以格外地忙活起来。租房,简单装修,买家具,添置各种物品,林湄有条不紊地做完了一切事,她对自己很满意,也令夫家另眼相看起来。
结婚的前两夜,林湄坐在窗前望着深蓝色的夜空――鹅黄色的月亮将水一样的月光泻在她细致的脸上,她叹了一口气:终于结婚了。她没有一般新嫁娘对娘家的眷恋,所谓的新生活不过是换间房子,换个伙伴,继续老故事而已。
婚宴那天,林湄穿着一件大红绣着金色团花的旗袍,她远远看到了小肖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那帅气的脸多了几分棱角,笑容就像酒店门前挂旧了的幌子,没有色彩,风吹得大些,它才会应付差似地动了动飘带。
林湄像一团火似地,从这里烧到那里,但就是没有烧到这个角落。
结婚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新婚之夜林湄的身体感受过瞬间的疼痛之外。她觉得自己还是从前的林湄!照常地上班、下班、买菜、做饭,这些是她在娘家做惯的事。如果说有变化,就是成文斌会讲多一些工作上的事,以及几乎每夜都要她。
对性爱,林湄没觉得特别快乐,对于丈夫看见她身体时痴迷的眼神,她有些困惑。难道男人无一例外都是贪恋女人的身体?否则怎么有那么多的君主因此而亡了国呢?唯一令她不快的是,成文斌开始限制她的外出,她的衣着打扮,并且关注任何一个打给她的电话。林湄有些恼火。
“你是我老婆,我管,你就要听!”
“我有自由,也有自尊。你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这么封建?再说,我又不是修女,为什么要穿黑的,蓝的,丑死了!”
一说到这儿,成文斌就阴着脸,不出声。在他的印象里,女人成了家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相夫教子。至于他本身,还有个小小的私心,那就是婚后的林湄越发地妩媚了,那美好的身材,润泽的肌肤,本是他一个人所有,怎么能让别的男人惦记呢?但他又不好直说:不许她打扮,只许留在家里给他一个人欣赏。这是多么说不出口的一个理由呢!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战争,如果林湄性格中没有倔强的话,战争永远也打不起来。好在林湄很快就怀孕、生子、休假,战争的导火索自然就埋藏在地底下了。
日子水一般地流过去,无声无息的。
七月的午后,窗台上的茉莉花吐着幽淡的芳香。林湄坐在床边细细地钩织着一条水蓝色的婴儿袜套――儿子已经两个月了。房间里除了花香还飘散着一点点油漆的味道。林湄自言自语:“都快半年了,这装修的味道还是散不尽,不要影响到孩子才好。”
六十几个平方的两室一厅,虽然不够宽敞,但告别了租屋的日子,她的心里十分踏实。总算有自己的家了。
一阵风吹来,两片花瓣落到窗台上,她走过去把它拾起来放到鼻子下嗅了嗅,随手又丢在花盆里:可惜茉莉不会结果。她瞥一眼儿子熟睡的小脸,情不自禁地笑了。墙上的钟发出一阵鸽子的咕咕叫,三点了,该准备晚饭了!由于休假在家,她的时间十分充裕,所以习惯了慢条斯理地做事。晚餐准备烧个糖醋鱼,再炒个窝笋。结婚后,林湄的厨艺进步了不少,每次吃完饭,成文斌都会满足地拍着肚子躺到沙发上,眯着眼注视林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是他最惬意的美好的生活。成文斌对林湄是很满意的。这个时代安心于厨房和照顾家人的女孩已经是极少数的了。他享受着自己的幸运,但绝没有站到林湄的那一面想一想,她是不是也同样地安适与满足。
通常,林湄的下午是这样渡过的。二点多钟,她就在厨房里预备晚饭。砧板上,鱼已经剖好,林湄用佐料将它腌制了起来。然后,将窝笋洗摘干净,切好。她蹩进屋,看看儿子醒了没有,再看看钟。才过了30分钟,她皱了皱眉,拿起抹布,这擦擦那抹抹,觉得这时间就像一个老病号似的,走两步,喘口气,歇歇脚,才又走两步。十分钟内,她看了7次钟,终于忍不住,她搬了椅子上去,把时钟拨快了一个小时。
五点半钟,鱼已经做好,盖着盖子,焖在锅里。窝笋呢,静静地放在砧板上,就等着丈夫回来旺火快炒。林湄抱着儿子站在阳台上向下望,这会儿,成文斌应该在视野里出现了。
对成文斌,她基本是满意的,工作很努力,做事也实在,只是话不多。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不怎么会心疼妻子,家务事很少做。好在林湄很能干,所以也不大在乎这个。她常常在想: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就是古人常说的天伦之乐呢?有时她倚在阳台边俯视着街道上往来的车马,觉得每个人都是那么忙碌,独她有着挥霍不尽的时间。想着想着,栖惶就像一粒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在胸腔里枝繁叶茂起来,那些枝枝丫丫又缠绕着,把她围个风雨不透。每到这个时候,她都感到无边的寂寞把她困在中央。
你耐得住寂寞么?你的步履依旧轻盈,明眸依然善睐。她偶尔会这样问着自己。
孩子满周岁了,闲极无聊的林湄迫不及待地回到学校。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出土文物,终于重见天日。学校的教师已经超员,虽说上了班,也是没课讲。“先代课吧”教学校长这样安排。
在家时寂寞,上了班依然寂寞。林湄便常上街转转。服装店、礼品店、花店、化装品店、眼镜店的门槛都快让她踏平了。不过,她很少买什么东西,只是逛。当橱窗被厚厚的墨绿、土黄、暗褐色挤满了的时候,林湄开始热衷于打毛衣,给身边的各类人。一些或前卫,或优雅,或活泼的毛织品从她的手底衍生出来,引起了所有人的赞叹。她自己也很满足,那些编织图、服装设计图、裁剪图好像是她的好朋友,有着久违的熟稔与新鲜。一天,她背着一只手编皮条休闲包和刘云婧逛街,一个女孩从后面把她叫住,不好意思地问:
“这只包和绒线小熊挂件是在哪里买到的呢?”
林湄还没说话,刘云婧倒是先笑了:“喜欢就只好把这个卖给你,这可是绝版的,世上只此一件!”
女孩一脸的困惑。
“你买不到的,是人家自己做的呢!”刘云婧指着林湄补充道。
女孩十分失望地说了声对不起。
“林湄呀,我看你干脆辞职算了,开一间做这些小饰品的商店一定能赚大钱!说不定还能卖到国外呢。我姑妈说澳大利亚那边特时兴手工织品呢!”
“辞职?哪是简单的事?再说那是澳大利。”
话虽这样说,林湄心里可是一动。当流传着一句话,叫“十亿人民九亿商,还一亿在观望。”这句话确实不过份,她眼看着昔日的同学一个个都当了经理、老板、领导什么的,连毫无特色只是有个好人缘的刘云婧,也在文化街开了文化用品商店。唯有她,还是个代课老师!难道她这辈子就这么算了不成?!
转眼,儿子小健5岁,林湄也已经28岁了。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她觉得这一生也就这样了,饮食男女这句话是绝对的精彩。
一天,林湄上街,经过十字路口时,遇到高中时的男同学正穿着警服站在路边。他的身体发福得厉害,相貌也老了很多。他们笑着打了招呼,简单地交待了近况,林湄这才知道他毕业后就一直当着交警,风雨无阻的。不知怎么,林湄就顾影自怜了起来,自己何曾又有什么进步呢?读书时的情景像是听了谁的召唤,倏地一下子从脚底漫到了头顶,她叹了口气和男同学告别。从前是回不去了,就是在梦里也不能够,将来呢?她只觉得站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的孤岛上,四处皆是茫茫的海水,而她呢,还不会水。
那一天,就这样忧郁着过下来,到了下午,林湄突然接到幼儿园打来的电话,说儿子的脚被打翻了的开水瓶烫伤了。林湄就如同自己被火烧着了似地赶到了幼儿园,到了那儿才发现并不严重,已经上过药,不碍事了。可林湄还是放心不下,恰在此时,成文斌打来电话。林湄忙把孩子的事说了,哪知电话那边,丈夫只是“嗯”了一声,就又说晚上有应酬,不要带他的晚饭了。
林湄有些急了:“应酬比儿子的脚还重要么?”
“我尽量早回,朋友有难事呢!”
林湄的脸一下子铁青,只那一转念间,心中就已经转过千百个念头,六年的婚姻生活好像一下子变成了黑白的默片。怎么一事当前,在他心里排在第一位的永远不是为她付出最多的妻子呢?
回到家,林湄心中的块垒依然不能平复。她站在灶台边,一面炒菜,一面想着刚才的事。炒锅里升起腾腾的热气,她的脸就浸在这热气之中。大滴的泪没来由地涌出眼眶。她在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却仍把持着,将火关掉――如同关掉了当年未嫁时对婚姻的一点点的热情。
一连几天,林湄没说一句话,洗衣服、做饭、打扫房间……如果不是空气异常的沉闷和低调,没有人会看出有什么不妥。这些年的日子,其实就是在这样单调的气氛中过来的。林湄开始真正地替自己不值了。但她还是很不服气,为什么别人都能满足于这刻板得如同原稿纸的生活,而她就不能?要么?就是她不愿意。对这个念头,她有些吃惊了。
第四天傍晚,成文斌有个朋友间的家庭聚会。开始林湄只说了两个字:不去。成文斌也冷冷地说:“多大的事,值得这样么?你是不是太不近情理了?”
林湄把眉毛挑了起来。
“得,你别瞪眼,他们几个你都是熟悉的,今天若不去,下次见面了怎么说话,尴尬的可不是我一个。”好像他算准了林湄是要面子的人,成文斌继续说。
结果,负气的林湄还是去了饭店。一路上,仍是不出一字。一跨进店门,笑容就马上从嘴角里溢了出来,职业得令她自己都害怕。男士们都喝啤酒、茶水,女士和孩子都要了饮料,独她要了杯白酒。好在她平时酒量不差,别人也没什么异议。倒是成文斌一直铁青着脸。
林湄看着他的脸色,在心里笑了一下,没说话。她很想喝醉,然而醉也那么不容易。回到家后,她又开了瓶红酒,但依然未能如愿。她灰心了,就清醒着把过去的事情一件件地复习起来……
上床的时候,成文斌的身子却又压了过来……林湄僵着身子等他做完了想做的事。她觉得奇怪,在这样的冷战中,他依然没忘记做爱!人究竟是不是有感情的动物?林湄就瞪着眼睛看着窗外,她想看到月亮,而窗上却遮着布满花朵的帘子……
1997年的国庆节来临了,香港刚刚回归祖国的怀抱,各行各业对这个国庆节非常重视。国市教育局组织各校进行歌咏比赛。林湄的嗓子不错,形象也不赖,自然成了主力。她练起歌来格外地卖力,好像自己的能力只有在这时才能展示一下。
一同练歌的同事中有个叫张宇的男老师,教体育的,是个热心肠。平时搭台、搬桌椅、打水、抬琴的活都由他包了。碰上练得晚些,他便自告奋勇送林湄回家。碰巧有几次,这样的镜头落在了成文斌的眼里。醋意像一团发酵的面团,一下子膨胀了原来五倍大的体积,堵在他的嗓子眼。
于是,一天早上,有意无意的,成文斌向林湄问起张宇来。林湄轻描淡写地说:“啊,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人还不错。”
“不是只对你一个人不错吧?”
“你想哪去了?人家是学雷锋呢!”
“学雷锋?可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学?”
“瞎琢磨什么呀!这不该操心的事,你还是省省吧。”林湄白了丈夫一眼,拉着儿子的手上班去。
这一天,依旧是练歌。由于快比赛了,那天结束的时间格外晚,大概8点钟了。林湄和张宇肩并肩走出校门。刚走到拐角,一个黑影转了出来,吓了林湄一跳,她“妈呀”一声抓住了张宇的手。再定睛一看,是面色阴沉的成文斌。张宇有些不自然地松开林湄的手:“林老师,你爱人来了,我就不送了。”
“好的,谢谢你。”林湄答应着走到丈夫的一边。
两个人一言不发地回了家。
进了家门,成文斌换了鞋,把脱下的皮鞋摔在地板上。“咚咚”两声闷响砸得林湄浑身一抖。儿子也吓得躲在林湄的身后。
“练歌?!我看是和男人约会吧!这么晚了还在外面,饭也不做,孩子也不管,这日子你还过不过?不想过,趁早散伙!”
林湄皱着眉看了丈夫好一会儿,脱了外衣挽起袖子进了厨房。
成文斌大踏步地跟了过来,抓住她的肩膀:“这会儿,也不用急着做饭,先把那个教体育的事说清楚。”
“根本没有事,要我说清楚什么?”林湄恼火了。
“没事?你当我是傻瓜?你唬谁呢?是看上人家比我年轻,比我嘴巴甜是吧?”
“你无理取闹!”林湄一使劲甩开了他的手。
“好呀,抓到了,还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