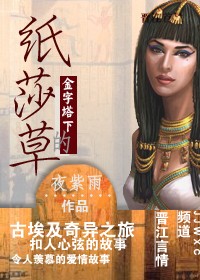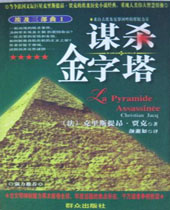红底金字-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杂院里没什么秘密可言,作家汪曾祺的女儿曾回忆说:
我们曾经住过的国会街五号的后窗外,是一个大杂院。我们习惯地管那儿叫“后院”,虽然我们的院子与“后院”并不相通。刚搬来时,邻居就告诫我们:别惹后院的人,尤其是那些“野孩子”!
搬来不久,发现后院的人真的跟我们不大一样。他们说起话来,从不轻声细气,一律横扯着嗓子,夹杂着各色脏字;酷暑时,那些已经结了婚、生过孩子的妇女大都光着上身,裸着一对丰满的或干瘪口袋奶,在院子里坦然地走来走去;从来没有听那帮孩子正儿八经地叫谁的名字,都是“三儿、四儿”的,或是亲昵的浑号。
后来我发现爸爸对后院挺感兴趣。每当写剧本或看书累了的时候,爸喜欢站在后窗前,不动声色地朝外看,看好半天。
后院的人在院子里做饭,用很大的蒸锅蒸很大的馒头和窝头,窝头里塞了很多的菜馅。主妇们抡圆了小臂用力在窝头上拍打出一圈规则的手指头印儿,远远看过去,挺像一件工艺品。爸说,这可是艺术,这样拍出来的窝头蒸出来才不会散。出锅时,满院子都是菜窝窝的香味,爸很夸张地做深呼吸,说他想像窝头一定不难吃。妈说他,“好像自己家吃不饱似的!”
有一次后院的一家在大铁锅里熬一大锅灰色的浆水,爸把我叫到窗前看,一边纳闷:“熬什么呢?”不一会儿,浆水发凝了,是熬淀粉。熬好了,把铁锅放在一个很大的洗衣盆里冰着;凉了,扣在菜板子上,好大的一坨凉粉!这家的主妇把凉粉切了,送到各屋去。不一会儿,就见各屋的大人孩子各自捧着加了盐酱的一碗凉粉,蹲在院子里呼噜呼噜地吃。爸先说,他觉得凉粉里加了辣椒油会更好吃一些,后来又发现,熬凉粉的和一个吃凉粉的不久前刚刚互相揪着头发打了一架,祖宗十八代都骂遍了。爸直乐:他们倒不记仇啊!③
不论住楼房还是平房,宽绰还是狭小,北京的绝大部分家庭,能自小独享一间住房的孩子是很少的,能分开性别居住,就算不错了。而老人和孩子一起住,甚至几代人同堂的现象,甚为普遍。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家当
屋里的布置,也大同小异。水泥地,白墙,电走明线,伞型白瓷灯罩里,是15瓦、25瓦,至多40瓦的灯泡。机关宿舍,家具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一次,在饭桌上,几个朋友就中央财经大学的沿革发生争执,在这个院子长大的高世英拿出了过硬的证据,他家的家具上印有两个单位的戳子,人大在先,从而“印证”了财大是自人大擗出去的一说)。三屉桌上摆着这些器物:菱形玻璃底座加绸纱布灯罩的台灯;搪瓷盘子里扣着开口带花纹的玻璃杯,上面盖着钩花白手绢;机械马蹄闹钟放在玻璃罩子里,每天晚上摘下罩子给它上劲;陶瓷或石膏的毛主席像得放在桌子中央,有的也罩罩子,有的石膏像下面还垫着四本“红宝书”(《毛选》)。五斗橱或带两个抽屉的小衣柜或书架上摆着电子管收音机。搪瓷茶缸子则随处可见,不少是作为纪念品发的,印着由五角星加一圈文字组成的图案。墙上除了毛主席像,必挂的还有月份牌,每天撕一张,每年换日历不换牌。桌子上铺着塑料布,床上摞着绣着一对凤凰或别的图案的缎子被面。那时候,挂窗帘的家庭是不多见的。
后来,公家配给的家具逐渐被折价卖给个人,折打得厉害,双人床、三屉桌、书架都不过几块钱,等于白送。到70年代以后,一些家庭或结婚或更新换代,开始从家具店购入新家具,家庭的色调略有分别。有个朋友还记得70年代一些家具的价格:箱子22元,大衣柜87元,五斗橱56元,双人床木头的47元,钢管的39。50元。他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有零有整,是因为他替他行将结婚的哥哥买这些东西,在西四家具店排了三天三夜的队。他说,下辈子也忘不了。当然,当中的两天一夜,他并没有亲自去站着,而是买通了一个蹬三轮车的替他排队,代价也还合算—— 一盒飞马烟。
北京孩子,生活的质量大同小异,大体不离上面描述的生存环境。
六七十年代的孩子,玩归玩,折腾归折腾,家务活是不能不干的,而且样样都得干。2003年8月14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把一个小学生学会洗衣裳挖出来当新闻,若在当年,这样的新闻应该颠倒过来说。
家务活之一—倒炉灰
那时家里的垃圾,以炉灰为主。家家都用蜂窝煤炉子做饭,7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替换成煤气灶,平房冬天仍得用炉子取暖。掏出来的炉灰,盛在破洗脸盆里,底下垫一张报纸,至少一天一倒。这活一般要落在孩子身上。单元楼虽设有垃圾道,但多半搁置不用。
垃圾站最初的设计是高出地面一米多,与拉垃圾的解放牌卡车持平。倒炉灰要上更高的台阶,所以垃圾站多半带有楼梯。后来改为升降式的,看上去有些自动化的意思。再后来又改来改去,直至今天的分置垃圾的红、黄、绿等颜色的桶,无所谓垃圾站了。炉灰也早被日常垃圾替代, “倒炉灰”这个词也成了历史。当年的垃圾车,是带两个跨斗的解放牌或东风牌大卡车。后跨斗下面有一个固定的木头隔板,环卫工人都站在上面,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口罩、手套和草帽,随车运转,不算违章。北京的大街小巷,天天可以见到以这种方式载着工人的垃圾卡车。
倒炉灰是一项简单劳动,不用学。孩子从低龄时就能干。有时候你倒我也倒,传染成呼啦呼啦一拨又一拨你来我往的壮观场面,有的孩子也不管家里的垃圾盆该不该倒。人人去时端着一个脸盆,回来就改成拎着了。有个朋友说起他们院垃圾站常有一个捡破烂的老头,用耙子钩出垃圾里的废纸,扔进背着的竹筐里。有的孩子倒完炉灰,有时候也顺手划一根火柴,趁老头不注意,把筐里的纸点着,让老人半天甚至一天的劳动所得付之一炬。
葛优小时候,也干过倒垃圾的活。他妹妹回忆说:“我哥有次倒垃圾,从二楼走到一层那几步路都懒得走,图省事,干脆把垃圾从阳台上往下倒,垃圾全落在楼下住家的门前,把人家气得够戗,上来告状。我哥还觉得自己怪聪明的。”④他确实聪明,自小能把生活琐事演成喜剧。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家务活(1)
六七十年代,还没有家用洗衣机,家家洗衣裳都用手搓。大人一般是在直径一米左右的大洋铁盆里支一个搓板,坐着小板凳或马扎搓。孩子开始洗不了大件,但也自很早起就逃不过洗衣裳这桩活。先是袜子、手绢、红领巾,然后是裤衩、背心,小学高年级以后,就无所不洗了。进了中学,再娇气的孩子也免不了自己洗衣裳,因为每学年长达一个月的外出学农生活,早把这类孩子逼了出来。
孩子洗衣服,一般不够“专业”,程序也经常乱套,洗不干净更是难免。不少孩子没有用洗衣粉的习惯,就用灯塔牌肥皂、药皂甚至洗脸的香皂蹭两下了事;有的孩子是一件一件来,即把一件衣服搓完,投毕,晾起来,再去洗下一件;也有的孩子洗过的衣服和没洗差不多,家长还得返工。但不管怎么说,洗衣服是当年绝大多数孩子必须体验的手工作业,也是一件多少年后说起来都值得自豪的事情。后来,他们气急败坏地教育自己的孩子时,都说过这样的话:“我从×岁就自己洗衣裳了。”今天十来岁的孩子,何止不会洗衣服,不会穿衣服、扣扣子甚至不会吃饭的孩子都大有人在。《光明日报》2004年4月23日的一则报道说:“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子,在中午吃饭时突然大哭起来,老师跑来问她为什么哭,这个女孩子一边抽泣着一边说:‘今天的鸡蛋太硬了,没法吃。’原来,以往每天带的鸡蛋都是她妈妈事先剥好皮的,而这次由于来不及了,没有剥皮。”
与衣服沾边的,是一些简单的针线活,如钉扣子。孩子的衣服扣子都挂不大住,掉了以后,无论男孩女孩,差不多都是自己钉,不少孩子有自己的针线包。有的孩子还能熟练使用顶针,甚而能蹬缝纫机。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一些孩子戴的黑纱,是买了黑绸布以后自己砸的。女孩子则大多自小就学着织毛衣。
家务活之三——收拾屋子
在家不干活的孩子,对这种活也不会陌生。因为学校轮流值日及不定期大扫除,都干过。
那时不兴装修房子,家里都是水泥地,用墩布擦。尽管是水泥地面,每天都擦,有的还蘸着煤油擦,差不多能擦出玻璃效果。当然,这与当年水泥的质量以及居民楼所用水泥的标号之高不无关系。墩布都是粗木头棍当把,墩布头是一堆破布条,用一种专门的铁夹子固定住。孩子多的家庭,今天老二,明天老三,天天擦地,一周也就轮个一两回。
收拾屋子,在很多家庭里,也是孩子的事。活不难干,但孩子下手不大稳当,免不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个杯子盘子之类的东西,为家长所心有余悸。
家务活之四——做饭
有相当数量的北京孩子,自小学三四年级起就开始做饭。这也是逼出来的,家长是双职工,院里没食堂,学校再不能入伙,那时不兴也不可能顿顿吃饭馆,不自己动手,就等着挨饿。他们人人可以写一本自己的做饭史。
有个朋友,自幼由其奶奶照料。小学四年级他奶奶去世时,哥姐或插队或工作。开始,吃饭瞎对付。某日,家里留下四毛午饭钱,他在小饭铺买了五个炸糕,这其实是该当早点吃的。孩子都眼大肚子小,他只吃了三个,就被噎得不善,连晚饭都没吃下去。他后来带着悔腔回忆说,早知如此,还不如买个黄瓜溜肉片就米饭可口。从此发愤学做饭,从炒鸡蛋做起,不出半年,就能在家开席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家务活(2)
当年没有整体厨房和现代化的厨具,没有不锈钢水槽、抽油烟机、玻璃钢炉灶和热水器。筒子楼或拿走廊当厨房,或几家人合用一个厨房。谁家伙食如何,一览无余,没秘密可言。四合院里就在屋做饭,后来普遍自搭厨房,“小厨房”是破坏胡同文化的原凶之一,也是方便老百姓炊事的最佳办法。单元楼虽有自家的厨房,也都烟熏火燎的。普及煤气之前,家家在蜂窝煤炉子上做饭,天天得封火、掏炉灰,火筷子、钩子、铲子,是厨房的必备品。上炉子炒菜,无法控制火的旺度,尤其是煮饺子,得以点水的方式配合火候。老楼的厨房,水槽是个大水泥池子,除了涮墩布、洗菜、洗碗,还可以把案板支在上面切菜。也没有专用的碗柜,不少人家把机关发的书架戳在厨房里,拉个帘子,放锅碗瓢盆和瓶瓶罐罐。厨房里常使的家伙,以铝制品为多,锅、壶、盆、勺皆然。舀水的葫芦瓢,枣木擀面杖,课桌面大小的案板,都是当年家家厨房里看得见的东西。不少人家吃饭都用陶瓷大碗,也称海碗。70年代以后,高压锅开始进入一些家庭的厨房,提高了作饭的耗时效率。沈阳出品的双喜牌高压锅一时热销。
我的不少朋友、同事和同学,都是自小就做饭的北京孩子。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一起吃饭,还经常能听到做饭的话题,有时候就着桌子上的菜切磋做法,可见艺无止境。前些年流行一种家庭聚会,来客每人做一道菜。我曾在这种场合见到这样的事,大家各显神通一番后,一桌子鸡鸭鱼肉吃不了多少,惟有一位客人做的姜味豆角,被一扫而光。这是他小时候随家长在北京饭店开会时吃过并学会的一道菜。做起来再简单不过了:把豆角掐头去尾,整根入锅煮熟后,并排码,然后浇上用姜末、醋、酱油、香油、味精搭配而成的作料即可。
做饭据说是一门艺术,从小做饭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被逼无奈,凑合做熟了口填饱肚子而已,动机并非对艺术的追求。所以几十年下来,多数 “孩子”的厨艺并未历练到家,至今吃他们做的饭,味道“不过如此”,顶多有一两手自视为看家的手艺,也大多得不到公认。我以前的一个同事,父亲是名厨,湖南人,解放后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做过饭,后来曾在马凯餐厅和曲源酒楼掌勺。他也未免于从小做饭,但由于父亲坚决拒绝传艺,不让子女再干这行,他至今没有得到点滴真传。多年前,我在他家吃过他做的一顿饭,柿子椒炒肉丝之类,属于饿急了吃吃还行的水平。另一位从小做饭的前同事,现在对色香味都极挑剔讲究,据他说,是上大学期间,经常到一个同学家听古典音乐的唱片,那位同学的父亲视其为音乐知己,常留他吃饭。该同学乃江苏人,其父厨艺非同一般,他的那点做饭的本事,用他的话说,是那时才“偷艺”得来的。
我的一个同学,1990年患急性肝炎,住在地坛医院里。晚上有时失眠,干躺在病榻上,滋味不好受。他就在脑子里过电影,把鱼香肉丝、烧茄子、炸鸡蛋酱之类的家常菜挨排“做”一遍,都是打小练的本事。我曾目睹他炸过那种拌面条吃的鸡蛋酱,操作并不复杂,但不大常见。程序为:先在碗里磕三四个鸡蛋,打匀;再咕嘟咕嘟倒上相当于鸡蛋三分之二的量的酱油,再打匀;在炒锅里多放点油,烧热后加入葱花,将和着酱油的鸡蛋倒进锅里;待液体趋于固体时,加入味精,端锅。用它拌面条,头一次吃,绝对香。他也是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了做饭的经历。
做饭不比前几样,它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家务活。一般孩子是从熬粥、焖米饭做起,而和面包饺子、蒸窝头、擀面条,而炒鸡蛋、熬白菜,而杀鸡炖肉烧鱼。孩子做饭,用凉水煮鸡蛋,下面条,把握不住火候,把菜炒不熟或炒煳了,或咸了淡了,甚至菜刀切了手,种种事故,都不免发生。大人也难免如此,何况孩子。熬粥、焖米饭都不费事但费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