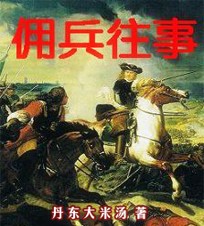���²��̳���ʷ ����:����-��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1937��6�¸���Сѧ��ҵ�����ڼҾ�ÿ�����£�үүΪ�˱��ϴ����ڱ������м��������������ø�����ѧ���̣������ѧͽ�����Ǹ���̫������ˣ�������һ������Ǯ���ٻ�Ǯ��ѧУ����ѧϰ����Ŭ����ȡ�˹��ѵı�����ҵְҵѧУ���൱�����ڵ���ר������ҵ��ɽ����������ˡ�
��������������������������ѧ��ʱ�����ߡ�¬�����±䱬���ˡ�����֮��¬���ŵ�����¡¡���������ǻֲ̿�����9�³�������ս���ӿ�ʼ���ˣ���һ֧���Ӿ�������£��ھ������ϼ����˸��š��ձ��ɻ����������˲���ʱ���������ն����ɿڿ����ը��˲�䣬���类ս���������֡����15��ĸ���Ҳ������ץ�ˁ���ǿ�Ƹ�һ�������������ʮ������������������������Ž����Żء�
���������վ��Ľ������Ĵ��ģ��ȴ��ʹ������������������״̬��һʱ���ɳ�����������ӣ��Կ���Ϊ���ĸ���������Ծ�������������������Ŀ��ն��飬���������ʵ���ׯ�ᣬ�������˺��ְ�����������Ǹ���һ����������̡�1938�괺�����˵��ص��������������������ũ����װ��������������һ֧���飬���������˱����о�������Ϊ���ж����ס��졢䵾�����˾��Ժ���Ͷ���ձ����˺��飩��1938��6�£����Ÿ��ײμ�����֧���ӡ�
�������������ﻹҪ��һ���ҵĴ��ֲ�Ȫ����1918�����ˣ���¬�����±䡱ʱ��ֵ�������������������������ּң�����һ���������桢��ѧ�ʵ��ˣ����ּ��ŵ�ϣ����Ҳ�����ּҵ��ص㱣������Сʱ��������˵����ʱ���ѧУ�ؼң�������װ�㣨��ʱũ�廹��ഩ���ɿ㣩������Ь�����������ģ�һ���������ε����ӡ������ڱ�������ѧ����ʱ�ĺӱ�ʡ�ᣩ�����������˼�룬��Ϊ����ѧ������¬�����±䡱�����˳����ǣ����������ݲ���һ�Ŷ���Ŀ������������μ��˿��ն��飬�����Լ��ĵܵܡ����ҵĸ��״������ӡ�
���������ξ�����һ���£��վ������������ˡ�ɨ������һ�Ѵ���������ҵ���չ⣬������ӻ���Ҳδ�����⡣��ʱ�������ڼ��п������̣����վ�Χ���ڴ��С����˼�Ϊ�ֻţ����̺ʹ��裨���ѳɼң�ǿ�ȴ������¾�װ����װ���ϰ��յ����Ӷ���˽١�����Э�ˣ����¾�װ����ˮ�����档����ȴ������ӣ������������õ������������������˰�ΧȦ����ȴ�������Ϻ��Ⱦ���Ҳû�ز��ӡ���ź����ż����ξ�������˵�������һ��֮�ƾ��ѧʶ�����ܼ�ֵ�����ʤ������ְλ����ȸ��ͣ�ƽ��ս��ʱ���ڱ�ƽ����������ݵ���ƣ�����Ȼ���ⶼ�Ǻ��վ��IJб����ᶨ�˸����յľ��ġ�
��������1938��9�£����ױ��ɵ��������ѵ��ѧϰ���£�������ҪΪ���С�վ�ڷ��ڵ�һ����³�ʶ���̹پ��ǹ��ɾ��ˡ���ױ�ҵ�������䵽24��5������ϰ�ų���3���º�5���ڷ���ɨ������ɢ��һ�롣��ʱ���о����������������ɣ���������7�˱�ѡ�С�1939��2�£������ںӼ��ҵ��˼��о�����������ѵ�ӣ�������������120ʦ�̵��Ŵ�ѵ��
����������ѵ��ѧϰ���������桢���š����ġ�ѧϰ������Ҫ��ս������棬����������Ρ�120ʦ����ͬ־��������һλŮ����������θ���ѵ���ϿΣ������й���ʷ����ʱ���ײ������Ӵ����й������������ڼ䣬�����������Ӱ��ܴ������μӹ���������120ʦ���Ա������ÿ��������һ�𣬳��������������к���������ӦӢ����ս�����ܶ��Ĺ��¡����ŶԵ���ʶ�����룬����������֯��£��10���ڰ�����¼������й���������
����������ѧϰ�ڼ䣬120ʦ�ڲ�ѵ��פ�ظ�������ׯ���վ�����һ�̣���ѵ�Ӷ�����Ա������վ�ڷ��ڣ������ڹ�����������СС��;Ͳμ�ս���������Ժ���
��������1939�궬����ѵ�ӽ�ҵ���ص����к��ױ��ֵ����о���˾���ս�Ƶ���ϰ��ı�������תΪ��ʽ��ı������ʱ���춨����һ����ս��ı�����ġ�
��������1942���վ���ζԼ��н��д�ɨ����ʵ���˲п�ġ����⡱���ߣ������������ӳ�����ƽԭ������Ϊ����Ӧս�����������о������ؾ������ࡣ1943��������ױ����뼽�о����̵��š�Լ����������ί���������м��������������ת�ƣ����켽����˾�����ί������ͼ��о���˾��������ȥ�Ӱ��μ�����͡��ߴ������ٵ��ν������˾��Ա�����״ӽ̵��ŵ�������������ת�������������˾�����ս��ı��
��������1945��8��15�գ��ձ�Ͷ�����������������������������뿪�˽��磬�������ٵ������������ξ��ܲ�˾�����ս��ı���Ӷ����������ξ��������������������������ž����й������ž�����Ұս�������������ˣ���ƽ����ս�����½��ϣ��ı��ٽ������ﶬ�����ƣ�����ƽ�����Ұ������ս�ۣ�ֱ�����ս���������������Ͼ��������ݾ��������״Ӳ�ı�����Ƴ����Ƴ������ݾ���˾���ս�������������������Ϊ��ս�������м��1955��5����1956��7��������41��123ʦ��һ��ʦ�����ı����һ����ֱ�������ս���������ݾ�������ı������ı����1969��5�µ���ί�ܲ�ı���θ��ܲ�ı������ս������1970��4������֮������ս��������1971�ꡰ��һ�����¼�����飬�Ž���������ս��ı�����ġ�
������������33����������У�������������˾�����ı����������û���뿪��ս���š������Ҿ���˾�ҵ��Ƚϼ���ս��������������׳����ݵ������Ծ��ϵġ��ڼ��о�������ı����Ҫ�����ǣ��о����̸�����׳�����ͼ��������ս�ң�����ս��ֵ����һЩ�ϴ��´�Ĺ������ڼ��о���������ʱ�䣬���������β�ı������һ�β�ı����Ӣ���������ٴӶ�����������һ��Ӫ�����ɾ���ϰ��Ũ�������ϰ����ף��������Ͷ����淢Ƣ��������ط�������ı��˽�¸�������������ӡ������β�ı����ɳ�˺����㣬���οƳ��ǹ���Ѭ�ߴ��š���Щ�׳��Ƕ������ı�����Դ����̣��ػ���������ʹ�����ڹ������ɳ���
�������������������ı���dz���Զ����ʱ���������ƺ�ת���Ҿ��Եж�����Ҫ��ʽ�����ռ����Dz�乤�ӣ�����Ⱥ�ڣ�Ϯ�ŵ��ˣ�����Զ�dz�������������������ϼ�Ҫ����������ȥ�˽�������ܽᾭ�顣���ڼ䣬��Ȼ������һ�δ�ɨ��������˾����վ����ˣ����Ҿ����ݵ����������ȶ��ġ����Ӵ������˶���úܺ����ս��Ҳ�����Լ����������أ���Щ����֮���ũ���
��������������Ϊ�������IJ�ı�����У�����ѧ���㶫�������ڶ�����1945��յ�����������������ı������Ф���⣬��������Ȩ���Ρ�������Ȩ���ڶ����ָ����浱���ķ��룬�ճ�����ʵ���ɸ���ı������ͤ���֡�����ͤ�Ǹ����ʸ��ϲ�����ʱ�����ֱ���һ�����ӣ�����ͤ��һ���ų����ֱ��Ƕ����ų���������ʱ�ֱ��ѵ�������������˾�����ͤȴ��������ξ����������ϣ�ʱ��ʱ���ڿƳ�����ı���м���ҫһ�¡�1946��7�¡����ߡ����������¥��������������ı��������Ȩ�εڶ���ı����
������������¥�μӹ���������ս��������ע�ؽ��վ�˾��Ĺ����������õ���������˾���������������һ�Σ����ײűȽ϶��֪�����Լ�Ӧ����Щʲô�������������ø��á���ı���Բ�ı��ԱҪ����ϸ�ǿ��������Ϥҵ��������������ʱش��ر��Ƕ��Լ��IJ��ӣ�Ҫ����ָ�ơ���ʱ��ս����Ҫ�������ڴ�������ȷ������ı��Ҫ�����Ӵ��������˽�������ܽᾭ�顣ÿ�����ս����չ������׳�����ս��ͼ���йط��淢ͨ����������������ָ������ǰ�������֣�ǰָ���ڹ��������ϵ�˫�ǣ����׳�����ǰָ�����������кܳ�һ��ʱ���ı��Ҫ����ս�Ƴ��ǵ��׳������������ס��һ�𣬼�ʱ�˽��׳���ͼ���Ա���֯�йر��Ϻ�ͨ�����������е���ս�����ɹ��Ļ�ʧ���ģ�����Ҫ������ȥ�ܽᾭ���ѵ��
������������ս��ǰ�����ڶ���Ұս��˾���ı����ս���θ��Ƴ������ֱ���սָ�Ӱ����еij�Ա��һֱ�����֡��ޡ����ж���������ս��ǰ��Ϊ�������ж���ͼ��ָ�Ӳ����Բ������Ҫ���⣬��Ҫ�ɳ�ר��ȥ�����������ɿƳ�����ȥ���ݴ������ܰ�Χ���ص������ɸ���������֯���ݡ����ݵĻ����ͣ��ɲ�ı�����վ�������ǰ��ȥ�ܽᾭ�飬����ɽǰ��ȥ��ս�ȵȡ������ܲ���Щ����ս���ж���ͼ��������һЩ�ݶ��׳��ܲ����⣬�������ݴ�������ʱ���ݶ�˾��ȳ����ʸ��ף�Ϊʲô��ʹ�õ籨������ս���ڼ䣬�������Ƴ��Ǽ���û�м����档
��������1948��9��12�գ�����ս���ڱ����ߵĽ�������������ȴ��졣ë�������ί���Ұ�֡��ޡ�����λ�׳���ָ�ӻ�����˫������ݷ���ǰ�ơ�9��30�գ�ǰָ�ڻ��������з�����һ����Ϊ��֪���¹ʣ��Ҷ�����ʱ���֣��ű������¹ʶ���������غ����
����������˧ȥ��20����ں���Ϊ��д�ġ����ٻ������жԴ������й����������������������ڵ��ュ�ŷ��ֹ���DZ����̨���������Ͽ������ֳ�վ��Ȼ��ͻȻ��ͷ���������������������������ȥ������
��������Ϊʲô�����������ֵ��г�·�ߣ���Ȼ���������Ұָ�ӻ���Ѹ�����½��ݣ�Ϊʲô�ѷ��ֵ��黹��Ѹ�ٰ��ѣ�ȴ�ڹ�������Χ�������ڣ����������˶�Ұָ�ӻ��ر�¶�ڵе�Σ�գ���ʵ��˧�����˽�ʵ�顣
�������������Ļ����ϸ��˵����Ӧ������һ��û��������غ�����¹ʡ��˽��������������˺��٣�����һЩ˵�����Dz�ȷ�ġ�
������������ս���ڼ䣬ǰ��ָ��������֯�����ɲ�ı������¥ͳ�ܣ���ǰָ��ר�еı�����г��ƻ��ɹ�������·��ͳһ���ȡ�
�����������ڵ�ʱ��������������Ҫ�����ڹ���ռ���У�Ϊ���г���ȫ������ս����ͼ�������Ƶ����С����ƻ�������Ұǰָ����ר����˫�dz����������������ر������������������������������İ���Ϫ��ͷ���£����׳��ӡ�˫�ɡ����������¸��£�Ȼ��ת������ȥ����ǰ�ߡ�
��������9��30����11�����ҡ���Ұǰָ��ר���뿪��˫�ǡ�Ϊ�˷��������ƻ���ר���ж��ƻ��߶ȱ��ܣ���������ֻ֪����һ����ͨ�г���˫�Ƿ�����������
������������ս�ۿ�ʼ��æ�ľ���ʹ�������ֵĵ����Ե���Щæ�ҡ���������û�н��������ר����ҹ�������������ͣ�����������м������Ҿ���ר�з������ַ���
��������ר������������Ϸ�����ʻ�˽�����Сʱ��ͣ��һ����վ�ȴ����ᡣ��ʱ�����賿��ר���ϵ��������ѽ������磬��������δ��˯����ս�ڼ�����Ϊָ�ӻ��صĹ�����Ա���ϳ����ú���ս�Һʹ������֡��ޡ����׳�����Ĺ����������ش����鶼��Ҫ���������һ��������ͣ�������ױ��µ�վ̨���ⲽ���ߵ�һ��վ���£����Ż谵�ĵƹ�̧ͷ����һ�ۣ�վ���Ϻ�Ȼ�������֡����֡�ӳ����������Ϥ�������εĸ��״��һ�������ԭ�����г�·�����෴����Ҫ��������ȥ�������峣���������Ժӡ���ͼ��������ˣ����ϣ�����������ʯ��÷�ӿڱ�ֱ������ر�ռ��ij������������ⲻ����ԭ�г�·�߱������ۣ����һ������Ұ��ָ�ӻ��ش����ش�Σ�ա�����Ҫ���ǣ�ë�;�ίʮ�����������Ұ��ָ�ӻ������½��ݣ���ʹ���������ߴ���·����ȥ������������ִ�������ʱ�䣬��©�ӿ�ͱ���ˡ�
������������æ�ϳ�����������¥��ı��������¥��֪�ߴ��˷���Ҳ�����ˣ��и��Ͻ���취����ʱ���ǿ�����Զ�IJ������һ�еȴ�����ǰ��������������г�������æ��ǰ��̽����֪��������һ�ݺ����������ʵ��г�����������Ѻ���ĺ��ڸ�������������¥��������¥���һ���г�ԭ�ش�������ͷ����ר�з��ع���������������������ı����ȫ��������һ�ݵij�ͷ����ר������������۶�ȥ��
����������շ�����ר����ƽ����վ�����£����������ġ�ë�š�����ͷ���ڴ�ӭ����ص��ȵ�֪������ר�У��϶��ŵò��ᣡ��ͷ����ר�к�ԭ��·���۶�ȥ��������ʻ���ɻ������������š���
����������ʱ����¥���������������ֱ봦�����ֱ����ڶ��ŵ�ͼ��˼���ֱ������¥���ſ�̽ͷ̽�Եı��ʵ�������������ѽ��������¥��æ�������۴������ˣ����ˣ�����ɻ����ˡ��������Ǵ�ս�ڼ����ֱ��и��������Ҫȥ˼�������û�и����ʡ�
���������������ֻ������¥������������·�ֵĵ�����֪���������˶����ڹ����ʮ������ײŶԼ�λ��ͬ־�ἰ���¡�����˵������������ս�۴�ʤ�ˣ�����Ҳ�Ͳ������⣬֪�������ּ��٣�û��Ҫ��ȥ˵������Ѿ�д�����ϵĶ�����û��Ҫȥ�����ˡ���
������������ڴ�������������⣿���������ʱ�������ս�����������Σ���������·�ֿ϶���Ҫ�Բ��˶������ˡ�
������������ݸ������ˣ�������ǹ���ˡ���ǰָ���沿���������Χ�˶�ʱ����ս�������ʵ���ƥ�ܾ����������������������ε����ڵ�����ҷ�˽������ײű����£���ʱ������첲����ȫ���ã�¶��ɭɭ�ǡ������ǵ��Ÿ첲�μӽ���ս�۵ģ��Ժ��첲�ϱ�����������İ̺ۡ�
������������ս�ۺ�ƽ��ս���ڼ䣬���ױ���ս���������ǰָ����������¥ͬ־���������ս�۵�ȫ���̡����Ժ��沿�����µ���ս�ۡ��ɺ���ս��ź��ϵ������ϵ����˷˵ȣ������ڡ���Ұ���ܲ���������Ұ���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