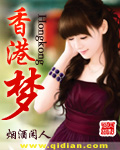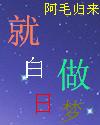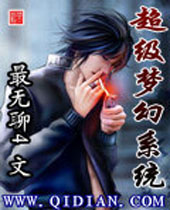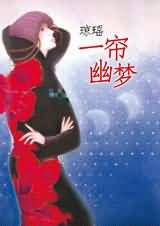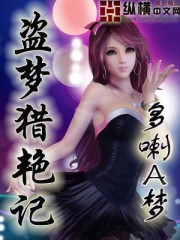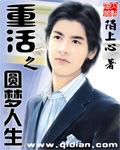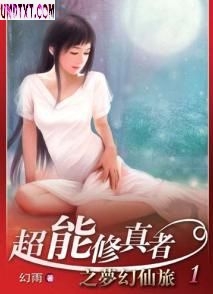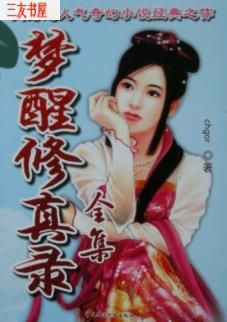江浙残明梦-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人在隔墙道:“不敢。在下以为,君为忠臣之后,诗文不可不精。吾观贤弟颇为勤勉,但缺乏旁人指点,故而有意导入此途。”
宗羲大喜,慌忙道谢。
原来,那人姓韩名上桂,字孟郁,号月峰。为广东番禺县沙湾司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他原为南京国子监丞,刚刚左迁照磨。为人豪爽慷慨,好谈兵略。工诗善词,写诗多倚马可待。还编戏剧在当时也颇有知名度。早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即集数十名文人结社秦淮河上,共演新作《凌云记》。以南教坊艺人傅寿演卓文君,其兄傅卯演司马相如。当傅寿演到卓文君取酒一折时,将卓文君的妩媚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宛然绝代佳人复出,场下随之掌声四起。韩上桂当即赋诗数千言,立赠白银百两。
在未来南京之前,宗羲就听人多次提起,不想竟在此处相逢,他不禁又惊又喜。
自此朝夕过从,拜他为师学习作诗之法。
韩上桂见他悟性极高,很为欣慰。一日,问他道:“老夫现与诸同人结社金陵,同人众多,以诗会友。我观贤弟诗艺日臻,大有前途,意欲引荐加入,如何?”
宗羲正苦于交流面不广,闻听大喜道:“求之不得。”
此后,黄宗羲便加入了以韩上桂为首的诗社,并结识了不少诗友,如广东博罗人韩如璜、南海梁稷等等。宗羲通过与他们交流切磋诗艺,不久便诗艺日臻,在金陵声名鹊起,为他日后成为清诗“浙派”的开山祖师奠定了基础。
二
不久后,韩上桂移居他处,但他仍时常与诸人往来酬唱,黄宗羲也多次受他赠诗。
七月七日,韩上桂在秦淮河上举行规模盛大的新秋七夕诗会,来约黄宗羲一同参与。
二人刚到,在场已有不少人,见到韩上桂纷纷起立招呼。
韩上桂于是一一为大家做了介绍。来者大多为闽粤人士。
居中坐座的是一位须眉皆白的官员。经介绍,宗羲知道此人为南京工部尚书何乔远,号匪莪,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氏,在这班人当中年纪最长,向来德高望重,众望所归。
坐在他左边年龄稍逊的为故南京国子监丞黄居中,字明立,也为晋江人。一问,竟然与黄宗羲同宗。二人初次见面,顿感亲近,宗羲便以兄长相称。
右边的为林云凤,字若抚,长洲人,寓居南京,也为一位词坛耆旧。他乍见宗羲,便格外亲切,颇有长者风范。
再往下分别为福建福清林古度、武夷张隆甫,浙江乌程闵景贤,南直隶徽州吴馡、歙县汪逸以及韩如璜、梁稷等等。而林古度竟然是天启四年继万燝之后遭廷杖的巡城御史林汝翥之子,二人见面,忆起父辈的共同遭遇,涕泪交流。
宗羲这才知道,他们都是南中诗社的成员。诗社领袖即为何乔远,韩上桂也为该社主要负责人之一。
当下新秋七夕诗会开始,大家分别拈韵作诗。
黄宗羲分得“秋”字,于是依平水韵下平十一尤韵部赋七绝一首。
顷刻诗成呈上,韩上桂当场改定数字,赞赏不已。
过了两天,何乔远再于城南凤凰台举行盛大诗会。宗羲亦到。赴会多为东林子弟,如周顺昌子周茂兰、林汝翥子林古度等皆到。
一时已临秋季,红叶纷纷,扑面而来。名流分韵赋诗,何乔远一一予以品评。
临别时,何乔远道:“老夫有意倡选《皇明文征》,诸人意下如何?”
众人大声叫好。
韩如璜素好古文,自号其作为“小韩文”,闻言率先主动应承参预此事。经商议,大家便决定此事由他与南海梁稷一同具体负责。
后来长达七十四卷的《皇明文征》出来时,黄宗羲细读,大为赞叹,深知社内诸子学术之深。
再过几日,宗羲又与寓居城南委巷的徽州籍诗人吴馡等一同游林云凤寓所南京报恩寺。
报恩寺为南京名刹,位于南京城南长干里。据说为明成祖纪念生母贡妃所建。寺内琉璃塔,高九重,由五色琉璃砌筑而成。塔顶悬挂百余盏篝灯,夜晚点燃,数十里外可见。林云凤长期寓居于此。
众人同游报恩寺,登上寺内九重琉璃塔。
但见南京城貌一览无遗。行人如走蚁,山川如盘景。清风拂衣,猎猎作响,颇有高处之胜寒之感。
尔后,大家又一时未能尽兴,干脆游遍南京城南雨花台高座寺等七十二庙宇。
接着,以吴馡为首,集林云凤、黄宗羲及河南祥符周亮工、南直隶桐城吴道凝诸人,在城南高座寺成立星社。
星社中以黄宗羲与周亮工、吴道凝最年少。林云凤便赠三人诗“慈恩他日题名处,十九人中肯见容”,流传社内。
不久,吴馡又在南京天界寺举行时文社大会,集者近百人。宗羲与林云凤、吴道凝、周亮工等星社成员都应邀参加。
大家拈题赋诗,不到午时结束。吴馡设宴于天界寺内丹墀,请大家分别入座。
席间,众人觥筹交错,谈笑风生。
大家不由自主地将话题提到了国事上。林云凤首先道:“今东有海盗李魁奇、刘香老为患,西有陕北流寇四起,北有鞑虏骚扰边境,朝廷可谓左支右绌呵。”
吴道凝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小后生,他年轻气盛,抢先应口道:“崇祯元年不是招抚了郑芝龙吗?以寇制寇,何愁不成?陕北流寇四窜,无非乏粮迫无生路而已,朝廷发内帑多济以粮,贼自复转为良民。所患惟辽东鞑子而已。”
周亮工点头道:“此言甚是。小弟观辽东十数年来尾大不掉,坐观养虎成患。”
此时,隔席一人厉声叫道:“郑芝龙海匪本性未改,与李魁奇、刘香本为同伙,旧情难断。数年来无非迫于王命,东追西赶一番,哪里肯真正剿寇?将希望寄在此人身上,岂不好笑?”
一语既出,四座皆惊。原来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儒生,长得剑眉挺拔,英气勃勃。
宗羲见此人出语不俗,不禁转头朝他多看了几眼,发现他也正在看自己,宗羲不由得将眼睛移开。
此时,吴馡招呼道:“眉生,又大发议论了?”
那人见是吴馡,转而笑道:“心有不平,故有此言。”
宗羲一听“眉生”两字,心中一动,便上前施了一礼道:“这位兄台,敢问莫非为宣城沈眉生?”
那人还礼道:“不敢。正是在下,敢问兄台尊称?”
宗羲答道:“在下余姚黄宗羲,草字太冲。”
那人一听,上前握住宗羲双手道:“原来是太冲兄。失敬失敬。”
原来,此人便是与芜湖沈士柱并称“江上二沈”、在江浙士林中无人不晓的宣城诸生沈寿民,眉生为他的字。黄宗羲不想在此遇到了从他曾生活过五年的宁国府里走出来的名士,惊喜万分。所以两人互通姓名后,陡觉亲近,拉手相视哈哈大笑。
这次大会甚为成功。吴馡当众宣布,拟刻唐人《孙樵集》、《皇甫湜集》行世。众儒士齐声叫好,然后相互作别散去。
宗羲和沈寿民互相留了地址后拱手而别。
过了几日,沈寿民果然来找宗羲,还带着他的弟弟沈寿国。沈寿国,字治先,也是位能诗善文的诸生。二人今年来到南京,都要参加今科乡试。
沈寿民问道:“太冲兄所来金陵何事?”
宗羲道:“因家仲父赴任应天府经历,小弟奉王母来此,故而流连。”
沈寿民道:“原来如此。”
他又问:“今年为乡试开科之期,敢问太冲兄可将应试否?”
黄宗羲道:“不曾。”
沈寿民劝道:“贤弟应当理经生之业,如能中举,对家人亦为慰籍。”
宗羲一听,不禁怦然心动。
沈寿民虽仅年长宗羲三岁,然而文章功力却较宗羲为深厚。他敬宗羲父亲黄尊素在宁国府任推官时泽润一方,而宗羲为人又大忠大孝,于是为宗羲开导理路,谆谆讲习。
黄宗羲禀明叔父,准备与沈氏兄弟一同参加庚午科秋闱南京乡试。自此埋头攻读,雄心勃勃意欲金榜题名,匡国安邦,实现父辈未竟之遗志。
三
转眼之间两个月时间过去了。
到了这一天,诸考生早早候在金陵贡院前。
五更时分,开始灯火传名,监考官唱名、核对、搜身。众士子依次进入龙门,分号归房。
主考官为江西人姜曰广,一名颇为正直的东林党人。众士子摩拳擦掌,力求一逞。
黄宗羲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满以为必高中头魁,他昂然走出了场屋。
他每日便坐书房内读书,却读不下去,心里一直在想着应考的事。期望能高中举人,自此平步青云,以遂经天纬地之愿。
不想待到秋闱开榜,却顿时从头冷到了脚——他竟然落了榜!与他同时落第的,还包括与他一同攻读的沈寿民、沈寿国兄弟。
宗羲失望之余,内心转为烦闷、消沉,决定辞别祖母与叔父南归余姚。
这日,他正在家中百无聊赖,拿着一部《汉书》翻看。自韩上桂迁走后,他除了外出应酬,在家只能独自读书,颇为寂寞。另外就是宗兄黄居中家有千顷堂,藏书很多,有时到宗兄处索书借阅。
忽闻有下人来报:“金坛周仪部大人来访。”
黄宗羲闻讯,慌忙迎了出来。
原来这位周仪部单名镳,字仲驭,号鹿溪,南直隶金坛人。崇祯元年进士,官拜南京礼部主事。其伯父周应秋、叔父周维持都属魏忠贤一党,崇祯初均被列入逆党,尤其周应秋更是臭名卓著的魏贼手下“十狗”之首,号称“煨蹄总宪”。周镳以此自耻,入仕后即结交东林,与黄宗羲曾有一面之识。
当下双方客气一番,相互谦让进入内室。
宗羲吩咐看茶,二人分宾主坐下。
宗羲开言道:“久闻周仪部大名,甚为仰慕。今日竟蒙屈尊驾临,深感荣幸。”
周镳忙笑道:“哪里哪里。太冲兄乃刘蕺山先生高徒,才华卓绝。四海之人,谁不闻名如雷贯耳?小可不过一介寒儒,承蒙诸友看重,得以结交善类,岂比吾兄?”
黄宗羲忙道:“仲驭兄也恁地过谦了。”
周镳哈哈一笑,站了起来踱了几步,又看看案头宗羲正在读的书,笑问道:“太冲兄现在也爱看此类书籍吗?”
宗羲道:“正是,仲驭兄也对此感兴趣?”
周镳微微一笑道:“自幼所好。”
于是两人坐论一会经史,颇为投机。
宗羲这才问道:“不知周兄今日到此有何见教?”
周镳见说,想了一想,方道:“娄东张天如,自去年草创复社,以兴复绝学为号召,重气节, 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因慕太冲兄为东林之后,才高八斗,名振宇内,甚有人望,故想相邀入社,以壮声威。不知太冲兄觉得如何?”说罢只管拿眼睃着宗羲。
张天如名溥,字天如,号西铭,南直隶太仓州娄东人。与其族弟张采并称“娄东二张”。崇祯初嗣,江浙一带文人集会结社之风盛行。什么应社、匡社、端社、几社、邑社、超社、庄社、质社、闻社、南社、则社、读书社、小筑社、诗社、文社、登楼社等等,不一而足,各执一方。崇祯三年,张溥、张采联合这些社团组成“复社”,在南直隶吴江县尹山召开首次大会,时称“尹山大会”。从此吟诗作文,讥议时事,品谈执政,成为继东林党之后的又一大文人群体,周镳也是社中骨干。对此,黄宗羲早有所闻。
而且,他与二张还是故交。崇祯元年春,张溥以选贡生入京师太学,张采则中了进士,二人结燕台社,又倡成均大会于京师,东林诸士多与他结纳,一时间闹得轰轰烈烈。那时宗羲正滞留京师为父诉冤,因而结识。
然而,乡试落榜让黄宗羲一时雄心全消,他推辞道:“小弟虚有其表,无才无德,恐有负吾兄盛意。”
周镳忙道:“说哪里话?太冲乃当世豪杰,文武双全的名士,如屈驾入我社,则为复社之幸也,岂有辜负众望之理?”
宗羲沉吟一会,自感盛情难却,便道:“即如比,小弟从命,惟恐才不堪大用而已。”
周镳大喜,连连称谢。
两人攀谈多时,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周镳感叹道:“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太冲兄博学多才,真使周镳折服不已。”
他见天色已晚,便起身告辞。宗羲送出门外。
周镳又道:“三日后张天如会社内众弟兄于秦淮舟中,望太冲兄切勿负约,届时前往。”
宗羲答应了。
四
十里秦淮河,为金陵最繁华之地。河畔多青楼妓院,金粉楼台,鳞次栉比;画舫凌波,浆声灯影,人文荟萃,商贾云集。名妓马湘兰、傅寿、李贞丽等都立户于此。
这些妓女不是寻常风尘女子,有许多出身名门,因世道多变,转而沦落风尘,故而大都才貌双全,并且卖艺不卖身,引来了一批文人雅士的追捧。较著名的,有人称“顾大脚”的顾喜、人称“张小脚”的张元,还有善做和事佬的“和气汤”王小大、自称“横波夫人”的顾湄等等,都名噪一时。
三日后的复社社盟大会,便是在这十里秦淮河上举行的。时称“金陵大会”,为复社成立后第二次大会。
乡试发榜后,各地赴考诸生尚滞留金陵。而除了应试诸生,其他江淮宣歙等四方名士也纷聚而来,舟楫相蔽而下。主人登堂供具,仆从或在舟中作食,烟火四、五里相接,极一时之盛。
复社原为浙江湖州人孙淳所创。当时江浙一带党社林立,孙淳立复社,张溥立应社,两社本互不统属。二张居中努力,孙淳便甘心情愿为张溥跑腿传信,招纳同志。凡张溥游踪所及,孙淳则为前导,人称“孙铺司”,又号“神行太保”。
崇祯二年尹山大会后,始成规模。众推张溥为盟主,又以宇内名宿南直隶文震孟、钱谦益、郑三俊、瞿式耜、侯峒曾,浙江刘宗周、钱士升、徐石麒、倪元璐、祁彪佳,河南侯恂、乔允升,江西姜曰广、熊明遇,福建黄道周等等四十余人为宗主。天下士人称张溥、张采不直呼其名,以居处分别称张溥为西张、张采为南张,其弟子则尊称他们为“两张夫子”,拟之为当世孔孟。张溥本人毫不谦推,也将自己居处称为阙里。于是更有好事者将其门下高徒赵自新、王家颖、张谊、蔡伸列为“四配”,吕云孚、周肇、吴伟业、孙以敬、金达盛、许焕、周群、许国杰、穆云桂、胡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