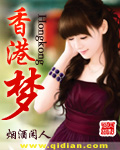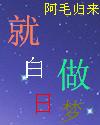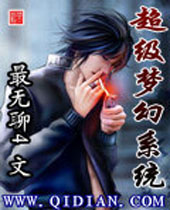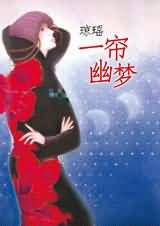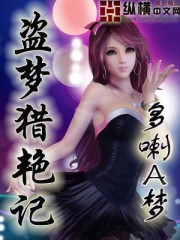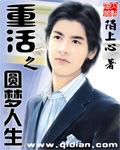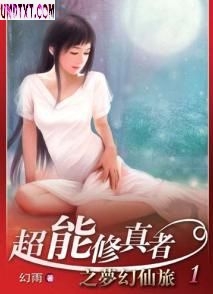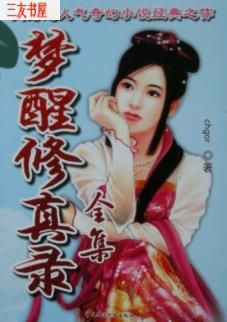江浙残明梦-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弄了半天,先前也赞同拥立潞王的史可法现在竟然要改立桂王?
众人仔细一想,福王名声不好,潞王又非嫡系。改立桂王,倒也不失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折衷方案,否则如此闹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当下张慎言道:“史公已与马瑶草取得共识,既不立福,也不立潞,礼部可速备乘舆法物,择日动身往广西迎桂王监国。”
吕大器道:“既如此,请回告史公,吾等谨遵吩咐。”
来人答应而去。
送走送信人,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刘孔昭等见此,自然也不好再说什么。
众人满怀赤忱,继续商谈拥立善后事宜。
正待散席,忽然传来消息:江北四镇联名上书一致要求拥立福王,马士英也翻悔仍旧拥福,集四镇兵陈于仪真。
众人一听,不禁相顾愕然。
二
原来,江北四镇为当时屯兵江北的四名总兵的统称。
闯王入京后,原镇守北方的山东总兵刘泽清等率部南下,加上原来驻守本地的总兵黄得功等,这里一带顿时热闹了起来。他们互相攻杀,抢占地盘,搞得民不聊生,形成新兴的“江北四镇”。
此四镇,屯驻庐州的为靖南伯黄得功,字虎山,绰号黄闯子,素以剽悍善战闻名,在四镇中拥兵最众;暂驻扬州城外的为总兵高杰,字英吾,绰号翻山鹞,初为李自成部将,后叛变受抚,以骁勇黩武著名,在四镇中兵力最强;暂驻临淮的为总兵刘良佐,绰号花马刘,暂驻淮安的为总兵刘泽清——此二镇军纪最坏,素搜刮掳掠,残害地方。
四镇拥兵十数万,是崇祯末年南方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他们的动向决定着明朝是否有资本与李自成农民军或新兴的大清军对抗。早在南京官员讨论拥戴意见不一时,他们这边却早已取得共识:拥立福王监国。
明朝除了京师和留都南京,凤阳作为太祖龙兴之地,位列中都,其地位仅次于南京之下。驻守凤阳的除了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马士英,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此人姓卢,名九德,绰号“胎里红”,为凤阳守备监军太监。他是当年万历帝郑贵妃的心腹太监。郑贵妃逝世后,因知兵,一直得到崇祯帝的信任,屡屡外出监军,与左良玉、黄得功、刘良佐等交情颇好。现在先帝既亡,太子不知去向,他便有了拥戴“娘家人”——福王朱由崧的想法。
而怀宁人阮胡子阮大铖则是一个投机主义分子,他认为:如果想东山再起,没有一个拥戴之功是不可能。崇祯帝殉国,南方无主,这使他有了一个破格擢用、飞黄腾达的机会。因此,他积极联系,总想沾点拥戴之功。但他知道自己为清流人士所摒弃的,想加入拥潞大军希望渺茫。于是,与卢九德一拍即合。
经过密议,阮大铖建议先去取得黄得功等领兵将领的支持。但光有领兵将领还不够,还得有一位朝中重臣作靠山。
阮大铖早已胸有成竹,他的对象是与他同穿一条裤的凤阳总督马士英。
然而马士英还是犹豫不决。老马虽然与阮大铖情同手足,也赞同迎立福王,但是他还不想开罪史可法等清流派人物。禁不住阮大铖再三唇干舌燥苦劝,总算勉强答应。于是他暗助福王搭上漕运巡抚路振飞的官船由淮安至仪真,派妹夫罢职知县杨文骢私谒福王,道明将拥戴为主、请静候佳音之意。
落魄江湖的福王朱由崧做梦都没有想到竟然有人要拥戴他为主,喜出望外。
阮大铖怕老马中途变卦,又与卢九德商议。要卢九德与诸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驰檄相告,取得共识,并与南京方面的拥福派官员刘孔昭等紧密联络。然后,决定由诸镇出面,联名上书拥立福王。
马士英虽然赞同拥立福王,但是他心里还是没有底,于是应史可法之邀赴浦口商议,最后决定迎立桂王。不料卢九德、阮大铖等抢先一步,鼓动江北四镇中的三镇要联名上书拥立福王。剩下一镇刘泽清见势不妙,也倒戈“拥福”。
至此,马士英只好顺水推舟,摇身一变成为“拥福派”首席文臣。
如此一来,“拥福派”反而占了绝对优势。
现当乱世,正需武将出死力。武将既如此,文官又能如何?
韩赞周见形势于己方有利,急取出事先备好的拥立福王的誓文,道:“快取笔来!”
大家面面相觑。想签吧,实在不愿。不签吧,恐启兵端,且当前处于社稷危急存亡之秋,根本经不起再来一阵折腾。况且万一福王真被拥立,诸大臣不但拥戴无功,恐反有弃主之嫌。署礼、兵二部印的吕大器更是迟迟不肯下笔。
韩赞周、刘孔昭等早察知众文臣心思,在旁只顾催促大家当众签字。
此时外有马士英合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镇,陈兵江北;内有韩赞周、徐宏基、刘孔昭等相为连结,气焰甚为嚣张。众大臣手无缚鸡之力,被迫不过,最后只好一一俯首就盟,并起草公启至仪真迎立福王。
三
次日凌晨,韩赞周与徐宏基、陈良弼、朱国昌捧着百官的公启往仪真。
福王此时正与阮大铖商议南京议立动向。闻听南京方面将派人劝进,慌忙向阮大铖问计道:“孤恐拙口笨舌,群臣进见,不知该如何答言。”
阮大铖道:“我主宜旧枕敝裘,与从人故作寒碜状。百官进见,我主只须如此如此,阮某敢保九五之尊唾手可得。”
福王大喜,连连答应。
不多时,韩赞周、徐宏基等到,呈公启,请福王启行。福王谦让再三,方才接受。
二十九日,福王乘舟过江。中午时分,泊舟观音门外燕子矶。
次日,群臣分批依次拜见福王于舟中,先勋臣再九卿后科道。
福王身着半污旧的角巾葛衣。坐在寝床上,手摇白竹扇,枕旧衾敝,帐亦不能具,行囊空空。随从太监田成等也都布袍草履,不胜狼狈。见百官来,都以手相扶,待茶款礼,极其宽和。谈及先帝,即不住地以衣角擦眼泪。
刘孔昭恳请继承大位,声泪俱下。福王也不由涕零,但坚辞不允,道:“国母尚无消息,只身避难,宫眷未携一人。初意欲避难浙东僻地,迎立决不敢当。”
群臣呈劝进之书,福王仍谦辞道:“封疆大计,唯仗众先生主持。”
群臣久闻福王荒淫无道,只道为一个贪婪无耻的纨绔子弟,不料面前所坐的却是一个落魄潦倒的乡下人模样,这才稍稍放心。纷纷额手相庆,口称宗社之福。
五月初一日,史可法等迎福王入南京城。
福王自南京西南的三山门登岸,鸿胪寺卿朱菊水与各科道诸臣前导,九卿在后扈从簇拥。士卒夹道而立,并分别在大教场和孝陵前驻营,以防不测。
车驾所至,万民欢呼,声闻数里。士民以纱灯数百盏来迎,一路上不时有生员、举人伏谒于路旁。老百姓们奔走相告:今日五彩云现,昨日有大星夹日、江中浮大木数千株,这些都是瑞兆,看来国家中兴有望了。先前闻京师失陷,人心多不安,至此士民才开始有欣欣然脸呈喜色。
福王先乘轿由城外直至孝陵门前,下轿改乘马入内。从臣请自陵东门御路入。福王谦辞回避,而从臣民所经的西门入内。至享殿前下马行祭告礼。
拜谒毕,福王徘徊良久,潸然泪下。忽问:“懿文太子②寝园安在?”
左右导之。于是也前往拜谒瞻仰。
复上马离开孝陵,从朝阳门入南京城,至直东华门入皇城,下马步行过皇极殿基,率群臣参谒奉先殿,仍旧徘徊良久。然后出西华门离开皇城,以内守备府为行宫住下。
这时众文武正式晋见,行四拜礼。福王面呈渐色,急起身欲避。
史可法在旁止住道:“殿下宜正受。”
福王这才端坐受礼。
这时刘孔昭之流以“定策”功臣自居,人人脸有得意之色。
福王传诸臣上殿,共商战守之事。
史可法首进战守大计道:“请素服郊次,发师讨贼,示天下以必报雠之大义。”
徐弘基、韩赞周等随后各上前奏数事。
福王无以为答,只是唯唯称善而已。
这时灵璧侯汤国祚上前道:“户部筹措饷银,而久盼不发。今士卒枵腹,军心动摇。如此作为,实乃可恼、可恨呵!”言辞激切,声色俱厉。
福王温言良语听惯了,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呆了半晌。
太监韩赞周上前斥责道:“放肆!发言不当,起来!”
吕大器也道:“此非对君之体。”
汤国祚也自知没趣,只得起身退下。
祁彪佳继而上前跪奏:“殿下与诸臣言战、言守,固然是要着。然而纪纲法度,尤为立国之本。纪纲明、法度修,才可以固结人心。先圣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今日宜当颁大号以正名。至于用人,更有关系。目前宜亟议政府及冢臣,共理庶政。”
福王一听,回头问韩赞周:“此为何人?”
韩赞周道:“御史祁彪佳,浙江绍兴人氏,系忠义之士。”
福王点点头,允其所奏。
群臣退朝后,复聚在内守备韩赞周私宅一起议拥立福王之事。
其时日将晡,甚为暑热。众人挥泪如雨,列座商议。
有的建议仿效南宋高宗称“兵马大元帅”。
祁彪佳道:“元帅系官衔,并且无所授。依祁某之见,不如直接称‘监国’为好。”
众人点头赞同。
当下议定先上监国玺绶而后登基。
次日一早,群臣都改穿绣服朝见福王。
福王站着接受百官朝罢,召百官升殿议事。
大臣面奏劝进。
福王道:“人生以忠孝为本。今大仇未报,是不能事君;父遭惨难,母无消息,是不能事亲。富与贵,是人所欲;贫与贱,是人所恶。但于义来说则不可。”
言罢痛哭涕零,任凭群臣苦劝,只是不允。群臣中也有感动涕零者。
群臣中再劝道:“天下不可一日无君,臣等不得命不敢起。”
福王推辞道:“东宫及永、定二王,见在贼中,或者可以致之。且桂、惠、端三王皆本王之叔,听诸先生择贤迎立。”
这时各台省言官集体上前跪奏劝进。
祁彪佳当先奏道:“昨者殿下驾入南都,士民欢悦,夹道拥观。即此人情,可卜天意。”
福王仍旧逊谢。见众意甚坚,便命百官暂退,留兵部及内守备进入内廷商议。
片刻,再上朝接见群臣。
文武百官排列两旁。吕大器于庭下面奏,跪呈劝进第一笺。
福王这才传旨:“暂领监国。”
群臣拜而退下,聚于守备府内耳房商议。
张慎言道:“国中空虚无人。不如遂即大位,以便摄服人心。”
史可法悄悄地道:“太子存亡未卜,假如北将护送南下,则当奈何?”
刘孔昭也赞同立刻称帝,于是在旁叫道:“今日既定,谁敢更移?”
史可法道:“且稍候数日,似亦无妨。”
刘孔昭还待强辩。
祁彪佳道:“监国名位极正。越是推让,越发彰显我主贤德。再则兴师讨贼,申复国耻,可以示海内无固以得位之心。而江北诸大将使共推戴,则将士亦宜欢欣。不如待发丧,择吉登大宝,布告天下为当。”
吕大器、徐宏基等也持异议。
刘孔昭只得作罢。
祁彪佳又道:“宜即日再上第二笺。以显得诸臣推戴之坚及殿下辞让之美。”
史可法深表赞同。
于是群臣再上劝进第二笺,请遂即帝位。
福王命传进,提笔批道:“仍领监国,余所请不敢当。”
四
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正式即监国位。
此日晴空万里,惠风和畅。文武百官身穿朝服齐集皇宫。
福王御冕旒,行告天礼祭告天地。忽空中紫气如盖,众皆异之。
司礼各官爇烛焚香,恭行三跪九叩首礼。读祝官朗诵祝文。
读毕,读祝官将祝文焚烧,纸灰竟随风直飘入云宵。一时官民奔走相告,以为吉兆。
礼成,福王入内。少顷升武英殿,文武百官行四拜贺礼,作乐。福王谦让再三,并述“未堪多难”之意,方端坐正受。
魏国公徐宏基代表群臣跪进以纯金所铸“监国之宝”。
福王受讫,再行四拜礼,这才退下。
于是福王摄监国事,大赦天下。
谕曰:
我国家二祖开天,昭宣鸿烈,列宗缵绪,累积深仁,历今三百年来,民自高曾以逮子孙,世享太平,代受亭育。其在大行皇帝,躬行节俭,励志尤勤,宵盰十有七载,力图剿寇安民。昊天不吊,寇虐日猖,乃敢震警宫阙,以致龙驭升遐。英灵诉天,冤气结地,呜呼痛哉!贼因而屠戮我百官,杀掠我百姓,滔天之恶,盖载不容,神人共愤。
孤避乱江淮,惊闻凶讣,既痛社稷之墟,益激我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图必报。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终夜拊膺,悲涕永叹。乃兹臣庶,敬尔来迎,谓倡义不可无主,神器不可久虚,因序谬推,连章劝进,固辞未得,勉徇舆情,于崇祯十七年五月三日暂受监国之号,朝见臣民于南京。孤夙夜兢兢,惟思汛扫妖氛,廓清大难,上慰在天,下对四海,忠孝之道,庶几无亏。期逭深愆,敢不戮力;德凉任重,如坠谷渊;同仇是助,犹赖尔臣民。其与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
福王监国,一时人心振奋。东林党官员虽然心里不太乐意,但毕竟社稷有了主心骨。于是原先的“拥潞派”纷纷转而一心一意拥戴福王。
福王既监国,于是改史可法、高弘图为礼部尚书,史可法仍掌兵部事;姜曰广、王铎为礼部左侍郎;升马士英为兵部尚书、副都御史,仍总督凤阳。又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吕大器、解学龙为左右侍郎;周堪赓为户部尚书,徐有范、张有誉为左右侍郎。张国维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贺世寿为刑部左侍郎,何应瑞为工部左侍郎,刘士祯为通政使,王廷梅应天府尹,郭维经为府丞。改李沾太常寺少卿,韩赞周为司礼太监。补科臣陈泰来等十一人,补吏部诸司华允诚等五人,补兵部诸司李向中等四人,余各升赏有差。
廷推阁臣,按故例五府都督勋臣不入班行。因怕不和,特地邀他们也来共同商议。
众人议推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三人,而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
张慎言道:“老夫老了!只愿安于总宪③。”
徐宏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