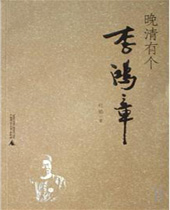亲历晚清45年-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当地的督抚大员建立了个人友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8 中国音乐从儒家学者那儿,我了解到,他们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宋朝一本著名的著作《礼乐》(可以翻译为宗教仪式和音乐)来阐释的。宋朝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就是在研究儒家礼乐的音乐部分时,我接触了中国的首调唱法体系,欧洲人一直很自豪地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新近发明的东西,而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了。读者若打算了解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可以翻一翻理查德夫人1898年发表的小册子《中国音乐》。与此同时,我妻子和我着手编撰一套十卷本的介绍世界音乐的书。现在九卷还是手稿,其中一卷在山西出版并被人们使用多年了。这些书中包括了每个国家的国歌的曲调和歌词,展示着不同民族的想象力。为了表明黑人的理念,还插入了一些禧年歌者的美妙歌曲。1882年,新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后来成为著名的总督——在山西致力于儒教复兴,建立了一所新的孔子庙,庙里配备了各色各样的一整套乐器,同山东——孔子的老家——的孔庙里的乐器一模一样。孔庙主持负责训练学生们的音乐艺术。一天,我去拜访他,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期间他发现我懂一些音乐。当我问到下一次他们练习时我可不可以来听一下时,他说:“我们现在就排练。”很快,他召集了大约三十名秀才,开始演练。那可真是一场可怜的表演:尽管乐器很多、很新、很漂亮,使用它们的人却不知道如何把音调调准,结果制造出来的是一片恐怖的噪音,而不是音乐。我问校长为什么不把所有乐器的音调调准。对他来说,那是一门新的技艺,他说他希望马上就弄懂这种新技艺。我邀请他到我住的地方去,告诉他说我的妻子精通音乐,她能够跟他讲解一下。这样,我们帮忙为山西的儒教音乐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佛教僧侣的交往
9 与佛教僧侣的交往为了理解佛教,我去一所寺庙住了一个月。那是当地最大的佛教寺庙,住持方丈是从外地来的,手下有一百多名和尚。每天我都同他一起进餐。他为人很善良,年纪六十多岁。每次吃饭之前,他都用一种基督徒难以超越的热忱进行祈祷。他的祷辞包括四个字:三、宝、法、僧(意为我们生活在宝贵的“三位一体”的恩泽里) 。然而,和尚们的教育却是非常简单的,除了每天例行的早晚诵经,他们的学业主要就是被教以各种宗教仪式的要点。经过大约五十天的学习后,他们就会获得由方丈签发的结业证书。10 参观五台山 在山西,有一座山是佛教五座圣山之一,这就是五台山,在太原府北边,只有几天路程。1880年6月,我前往参观了一次。山上有数不清的庙宇,其中的数千名和尚分属两大教派:一是中国的普通教派,穿灰色僧服;二是穿红色法衣的西藏和蒙古教派,称喇嘛。在每年的仲夏季节,五台山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宗教集会,论重要性相当于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也是一个举行大规模贸易的机会,蒙古人带着他们的小马和骡子前来进行交易。当时五台山最重要的人物当属中央喇嘛庙的方丈。为了能见到他,我精心制作了一幅很大的彩色世界地图,用汉字标出了地名。我把地图和名片一同让人送给他,表示希望能见一面。他定下了见面的时间,于是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谈话。我向他解释了地图的含义,从上面指出不同的地区、大陆和国家,并说明地图是按一比多少里的比例画成的,由此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的相对大小。这是他看到的第一幅世界地图,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立即命令上点心伺候。于是我解释说,我前来访问他的目的是为了对佛教有更多的理解,希望能允许我参观他们第二天的祈祷仪式。他很高兴地同意了。第二天到达时,我看到寺庙内外挤满了汉人和蒙古人,很难挤出一条路穿过去。当我登上通往寺庙大殿的一百零八级台阶时,发现很多手持鞭子的仆人在等候我的到来。一看到我,他们立即用鞭子在人群中开出一条路。于是我被领进一所大院子,穿过又一群人,到了一座平台上。那儿坐着一位中国官员,是个蒙古人。他的夫人,身着红黄两色的鲜艳服装,也被邀请坐在他们中间。在其他乐器的配合下,一面巨大的鼓被敲响了,这宣布了祈祷法会的开始。僧侣们用一种非常低沉的声音诵经(比俄国神父的声音更有俄国韵味)。接下来是一场想像不到的、令人吃惊的舞蹈。一群男人出现了,头上带着非同寻常的面具,有老虎,也有食肉猛禽,整个集会看起来成了埃及神话中各类野兽的大荟萃。看完这种宗教舞蹈后,我又参观了汉传佛教的中心寺庙。在那儿,我在他们的祈祷仪式中见到了规模宏大的音乐合奏。一切都令人肃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音乐强烈地使我回想起格列高利的圣咏和令人感动的古代教堂的颂歌。和尚们被分为两队,一队在大厅通道的右边,另一队在左边。一队站着,双手合十抱于面前,非常和谐地咏唱四行一首的宗教诗歌;另一队则拜倒致敬,悄无声息。礼拜结束后,轮着他们站起来,唱第二首歌,而原来站着的则跪下去,伏地行礼。他们所唱的圣歌是那样甜美,我把其旋律记了下来,用在了以后的礼拜仪式中。下面是其中的片断:
在山西,我没有发现任何道教徒接受教育和获取圣职的地方,但1881年在北京时,我却访问过一所道教的学院,那所学院是由政府资助的。我还给江西省道教的大教长写过信,向他讨要一些道教现代教学的教科书,但收到的只是一些护身符,人们认为那种东西像罗马教皇所赐福的十字架一样,具有除魔避鬼的功效。除了研究中国宗教、翻译那些我认为对传教有帮助的外国文学作品,我还通过给官员和士绅们做演讲、去农村旅行传播福音,来使工作变得多变有趣。我还筹办了一所能接受六十名孤儿的学校,由我的妻子掌管,她抽空参观了当地农村中七所基础学校。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张之洞
11 张之洞从1860年大不列颠和法国占领北京开始,恭亲王——当时最有权势的人——就明白,与外国势力作对是徒劳的。但在1880年前后,涌现出了三个聪明的、主张抵抗外人的少壮派。他们都是饱读经典之士,对中国往昔的荣耀念念不忘,声称中国只要去勇敢地面对,就能把傲慢无礼的外国人赶走。其中之一是张之洞。1882年,他被赐予山西巡抚的要职,这打破了京官不外派的惯例。第二个年轻有为的官员是张佩纶,驻防福州的海军舰队司令。他向上级汇报说,沿海要塞都固若金汤,但法国人的行动驳斥了这种官场套话:他们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攻克了全部堡垒。第三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但三个人最后都发现,他们所拥有的世界知识还是非常基本的、不充分的。上任山西巡抚一开始,张之洞就大力采取富民措施,预防灾荒。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里,他发现了我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一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厂等方面的建议,便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这里来,问我能不能放弃传教工作,参与中国政务,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我的回答是,尽管我理解改革的价值,但我不是个专家。中国的改革要想顺利进行,引进大量各个领域的外国专家,是十分有必要的。代表们说,对此巡抚很清楚,但既然我在内心里知道怎样做对中国最为有利,巡抚大人还是希望找到一些合适的人才,在我的指导下实施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对此,我回答说,不论物质上的进步多么急迫,传教士所从事的工作仍然是更重要的,我不能完全离开崇高的传教职位去从事低级世俗工作。这样,我谢绝了巡抚的好意和报酬。因为存在着洪水淹城的危险,巡抚让我对太原周围的地形进行一番勘测,为预防将来的洪水泛滥提出建议。我请斯哥菲尔德()医生帮我测量地平高度和照相。我们向巡抚汇报了自己的观点。他还请我帮他考察适合开采矿山的机械,我遵命照办了。正当巡抚下定决心进行他的改革计划时,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处理与法国之间的争端。法国人那时正在安南边境制造麻烦。不久,他被改任湖广总督,驻武昌。他还没有忘记在山西时我给他提的建议。他建立了一座钢铁厂,开始修筑铁路,开办各种工业和现代学校。这些都是我在山西时向他提议的。他又一次邀请我参与他的幕府,而我又一次拒绝了。我也有一种感觉,在这邀请下面,仍然遗留着强烈的排外情绪,我担心那会在工作中导致过多的摩擦。在当时的官员中,他大概是唯一头脑清醒、办事认真的人,其他的各级官员都在酣睡,盲目自负,对民众的苦难漠不关心。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
12 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对罗马天主教表现出信任和善意,就像对待非基督徒的中国人一样,尽管我认为他们的观点不正确。1873年,第一次去济南时,我问烟台的一位名叫安哲力尼()的天主教神父,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帮他捎给省府的神父们。安哲力尼曾经在新西兰待过,英语说得很好。他托付给我一个包裹。到达济南后,我将包裹送到了天主教堂。主教出门在外,神父们对我很友好,邀请我一同进餐。回到烟台后,我把去拜访天主教堂的情况向安哲力尼作了汇报。三年以后,恰巧也是在烟台,我听说他病了,就去看望他,看到他正躺在床上。谈了一回之后,他问我可不可以为他祈祷。这我当然很乐意去做。当我在1878年结婚时,安哲力尼不请自到,出席了我的结婚典礼。去山西后,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的,巡抚建议我去与天主教的人协商,合作赈灾。那时太原府有两位主教,其中一个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将近七十岁了。另一位比我大几岁,是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会员,是个富有活力的人,中文名字叫恩革()。一开始,他极力劝我去母教堂交涉,我质问他,怎样才能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母教堂呢?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开始了持续三天的争吵。他固执己见,我对他说,因为他只了解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没有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讨论问题。他用同样的方式反击我,但我向他保证说,我了解他所掌握的所有权威著作,而他,却不能获准阅读清教派的权威作品。第一天,他们最出色的当地人神父也在场,因此我们用汉语交谈,但接下来几天里,他并没有被邀请参加。我们谈论的是纽曼()枢机主教的宗教经验以及两个教派之间的各种不同之处,直到彻底理解对方的立场。最后我们友好分手。当大卫·希尔()和约书亚·特纳()来太原时,我曾领他们俩去拜访了主教,顺便对他通过遍及全省的神父们为我收集关于灾荒程度的证据材料表示了感谢。当我们三人散发救济金时,曾听说他以我们双方的名义在天主教堂举行祈祷大会。当我再次来到太原府,一种流言在人群中广泛散布开来,说天主教堂顶上的天使会给人带来灾祸。那是个吹喇叭的天使雕像,起着风向标的作用,面对能带来雨水的季风吹来的方向。紧接着,就有人声称,无论何时风从那个方向吹来,那个吹喇叭的天使都会把云和雨吹跑。因此,他们扬言要推倒天主教堂。巡抚巴不得激化我们和罗马天主教徒间的矛盾,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我不赞同在教堂顶上放一个天使像,现在机会来了,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于是他派助手前来找我。我回复道:“告诉巡抚,那些人彻彻底底地错了。天主教堂顶上的那个天使,只不过体现着我们的《圣经》经文的一部分内容,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他问我能否让他看看那一段。我拿出一本《新约》,把涉及到天使的那页折起来,让他拿给巡抚看看。他如释重负地走了,天主教堂也保住了。此后,在太原府的时候,主教和我每年都要相互走访几次。在一次拜访中,他告诉我他已经向他的神父们下了通知,如果我到了邻近他们教堂的任何地方,他们会邀请我在他们那里住宿,那要比旅店里干净多了。他还邀请我给他的学生们做天体学的讲座,我都照做了。利奥十三世成为罗马教皇后,他把中华帝国划分为五个区,各有一个中心,主教们可以在那里聚会商讨传教中遇到的问题。太原府作为其中一个区的中心,举行了一次会议,有来自山东、山西、甘肃和蒙古的主教参加。我被邀请参加晚宴,大家用汉语交谈,彼此都能听得懂,没有任何困难。我也被邀请参加他们的会议,由于会上不是使用汉语,在对他们的美意表示感谢后,我婉言谢绝了。他们依旧和我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多次给我们送来番茄和他们自己做的山西葡萄酒。主教来访时,常有一个名叫维()的意大利神父相伴,他是天主教堂的风琴演奏家。我家里有一个簧风琴,当我的妻子演奏罗西尼的曲子时,维很高兴。我的夫人问主教,陕西省是不是像山东和直隶那样也有欧洲修女,但当时是没有的。他们还不敢把修女送到那么偏僻的内陆,那些中国人会想当然地散布各种谣言。还有,维神父刚刚为失去父母的一些女孩办了一个班,叫她们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书籍和缝纫,以便她们能自谋生计。我夫人建议教孤儿们学习使用缝纫机。我们为他订购了一部。缝纫机如期送到了,我夫人曾到他那儿去,教女孩子们如何使用它。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山东之行
13 山东之行现在,再回到编年史顺序来叙述。1882年,我的同事,主持山东青州教堂的阿尔弗雷德·仲斯()奉命回国。考虑到教堂创建不久,他请我在他回国期间代为料理。我实在不想担当这个差事,因为我想,当地的基督徒是能够培养起自立能力的,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放手让他们去做。然而,经不起仲斯先生和两个新到的同事的一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