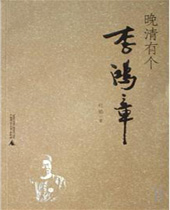亲历晚清45年-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过来,尽管已有两本中文书籍(非卖品)讲解伊斯兰信仰的真义。同时,我也了解到,尽管伊斯兰教徒投入大量的时间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一般说来,他们对中国文学却令人可悲地无知。20麦考文,济南府的第一个长老会传教士直到那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之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写过一本供伊斯兰教徒使用的基督教书籍。然而,在青州府,住着一位美国长老会的牧师,叫麦考文(),他是在我来访问前一年从北京转到济南的,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传教士,曾跟长老会中一些资深传教士一起出版过一本在中国的传教规范。由此,他开始研究伊斯兰教义,打算写一本供它的支持者使用的小册子。从他动手准备到现在,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遗憾的是,还没有任何一位传教士就这个题目用中文出版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济南府,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卡洛斯特()先生,他深得中国人的喜爱,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然而,这两个人都陷入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精神状态之中,克服这种状态的主要困难是他们的观点过于僵硬,并且缺乏对中国环境的适应能力。第二点由麦考文先生的着装这种事情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因为中国人的居室和旅馆里没有火炉,我们外国人的冬装不足以御寒。于是乎,麦考文先生自己动手做了一件皮袄,跟中国人的样式——里边是长袍,外罩一件马褂——不一样,而是类似我们外国人穿的大衣:以羊皮做里子,一片类似披肩的东西盖着两肩和胸部,后边部分却缝住了。在他穿着自己的新衣服出现在街道上的第一天,看到的人无不捧腹大笑。“这洋鬼子的老婆多蠢哪!”他们大叫:“她不知道怎样做一件大衣!从前面和侧面看,他穿着马褂;但当他走过去,从后边看时,却看不到马褂了。谁见过跟这些鬼子一样荒唐的人?”当我告诉麦考文,说这种日复一日、持续不断的嘲笑何辱骂使我无法忍受,他的回答尽管听起来漂亮,却不切实际:“我们必须超然物外”,他说。但事情很快就超出了他作为人的本性所能忍受的程度。一天晚上,他来到我住的旅馆(那时候,没有人敢租房子给外国人),显得非常沮丧,说:“理查德,我想请你帮个忙。”“非常愿意。帮什么呢?”“我已经得出了结论:原来以为上帝召唤我做一个传教士,现在看来这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如果是上帝指派我做一个传教士,他早就会使我拥有一些皈依的信徒了,但现在我一个也没有。所以,我决定离开差会,好让委员会把钱用来资助那些真正蒙上帝召唤的人。我打算到任何一个通商口岸去,尽我的能力编写一些学校用的教材,以此来维持生计。我有一块钟表,是母亲送给我的,我不能失去它,希望你能为我保存一下,直到我在新地方找到工作,安居下来为止”。“当然我将照看你的表。”我回答,“但你不认为,你的决定做得太匆忙了?”就这件事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分手时我对他说:“为此再祈祷一次吧,在你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我们再谈一次”。几天以后,他又一次来拜访我,一见面就说:“我已经得出结论了:不论我们关于生活、宗教和差会的看法如何,总会有一条路绝对适合于我,它的价值永远也不会改变,那就是行善”。我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说:“这是一块磐石。站在上面,你的麻烦很快就会被克服的”。从那天开始,他成了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更有效率的工作者。他去世于1878年,因为精神上的问题早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麦考文的同事卡洛斯特
卡罗斯特先生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但对于他认为是自己的职责的事,他同样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有一段时间,他对自己多年来的工作毫无成效感到非常伤心,得出的结论是祈祷得不够。因而,有时他会在一种灵魂非常痛苦的状态里连着祈祷几个小时,不久就导致了精神的彻底崩溃,先是被送到北京,后来被送回美国老家。待在美国期间,为了寻得启示,他访问、研究了那儿所能找到的各种奇怪的宗教派别,但他回中国工作的渴望却有增无减。由于传教委员会不打算再派他出来,他去了海边,作为驶往巴勒斯坦的一艘轮船上的一名普通水手开始了他的旅行。在由雅法 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他竟然碰上了罗马天主教驻济南的主教。卡洛斯特简直高兴得手舞足蹈,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次会面,更强化了他前往中国的渴望。他访问了巴勒斯坦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宗教团体,然后去了埃及,从埃及又乘船去了孟买。在孟买,他拜访了圣人鲍恩(),印度人对他敬若神明。在得到圣人的特别训示后,卡洛斯特又一次站在了桅杆下,开始了前往中国的航行。在离开中国的这段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由一些稀奇古怪的作者——其中包括早期的神父、中世纪的作者,直到现代的神秘主义者——所写的有关基督教教义的书籍,接受了许多奇怪的教条。比如说,认为身体上的毛孔是数不清的邪恶精灵进出肉体的大门。一到烟台,他就去拜访他的传教士老朋友们。看到他衣衫褴褛地出现在面前,他们吃惊不小,送给他钱让他去买一些新衣裳,但他一分钱都不要。他们偷着把一些碎银子塞进他的钱包里,但他发现后,把银子送给了路上碰到的第一个乞丐。他一路上为人看病,步行到了济南。当济南本地为数不多的几个基督徒看到他后,他们对他的形象同样非常吃惊,但他的归来使他们非常高兴,表示哪怕只剩最后一点食物,也会与他共享。有一段时间,他又一次被派往北京。在那里,他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城里乞丐的救助工作中,无论是阿西西的圣方济(),还是任何其他苦修者,都没有像他那样投入地照顾穷人。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同他一起歇息在伦敦差遣会内达真()医生的房子里;医生不在。晚上我睡在一张西式床上,而尔卡洛斯特则去医院跟病人睡在一起。每天早晨黎明时分,他往往到我房间里来,躺在地板上,和我一起讨论基督教早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宗教信仰,他的肚子里装满了这类学问。后来,在1889年我们家定居北京时,我们经常邀请他与我们一起吃饭。他来时经常带着一个中式面饼;他更愿意与我们分享那种简单食物而不是吃我们做的饭菜。当我们请他留下过夜时,有时他也会接受,但他从来不睡床;经常是,他躺在火炉前的地板上度过一夜。他非常小心地保存着一本日记,里边记载了他第一次离开济南后的感想和经历。米切尔()先生从中摘录了一些,不定期地发表在北京的报纸上。米切尔对他的奉献精神深怀敬意。一次,卡洛斯特把他的日记拿给我,请我编辑一下出版。发现他那种怪诞的行为与念头又有所回潮,我把日记还给他,告诉他等一段时间再发表。一年或两年后,他到了上海。从北京到汉口,他一路上都靠步行;到杭州以后才改为乘船。他同傅兰雅()博士一起住在阿森那旅馆,那儿的仆人对他都表现出十二分的忠诚。傅兰雅先生的夫人告诉我,一天早上,他去吃早饭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现在我战胜了我的最后一个敌人”,他宣称。“它是什么?”她问。“我的日记是我的骄傲。我刚刚把它烧掉了”。这真是一个悲剧!就在这年夏天,他的体能已开始衰退了。他认为如果能到达蒙古,就能恢复身体健康。于是他乘坐“爱德拉都”号客轮前往天津。船长佩恩()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把船长室让给了这个疾病缠身的人。但是,船刚到天津,他就去世了。那时我不巧正在外地,我的妻子在听说这件事后,直接赶到轮船上,安排他的葬礼。后来,我在他的遗体所埋葬的地方树了一块很平常的石头,作为标志。麦考文和卡罗斯特先生以及另一些我所认识的罗马天主教牧师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错误的神学理念,归因于对基督教教义的错误应用,也归因于他们对成功传教的环境条件理解得不够。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慈善家引进牛痘接种技术
1874年,由济南回烟台的途中,我在潍县停了一天,与我的朋友、苏格兰长老会联合会的麦金太尔牧师见了面。在潍县,我了解到了有关在中国传教成功与否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是政府官员的强烈敌意;第二个是,即使在非基督教的中国,也能找到最虔诚的人。在传教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麦金太尔先生租了一所小房子,整个潍县城像被戳了的马蜂窝一样起来反对。就这么点小事,却使人们如临大敌,如遇劲匪,躁动不安。他们威胁要使用各种暴力手段,除非外国人被从他们当中清理出去。然而,当地一位有头面的绅士突然拜访了麦金太尔先生。他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一个虔诚的人,饱读圣贤之书。他告诉麦金太尔先生没必要害怕民众的威胁,因为他们无知得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个人将出面向人们说明他们所犯的巨大错误。在这之前好多年,这位绅士就听说北京来了一位洋人(伦敦差遣会的洛克哈特医生),懂得如何预防天花。那时候,天花被看作神明对人类的可怕的惩罚,在很多地方的小城镇和村庄,有一半人口因此而死去。听说有办法可以预防天花,他非常高兴,奔波十天到了北京,去看望洛克哈特先生。洛克哈特先生向他传授了接种牛痘的技术。于是,他雇用了两位妇女,让她们带着她们经过接种的孩子,同他一起回到了潍县。一回到家里,他就忙着给朋友和邻居们接种疫苗,直接从那两个孩子身上取种。最后,人们都认识到了种牛痘的价值。很多年中,确确实实地,直到麦金太尔先生来潍县的时候,这位中国绅士一直夜以继日地义务为群众接种牛痘。作为回报,人们在他的大门楣上挂了一块颂德匾。现在,当人们看到他去拜访外国人的时候,非常气愤,纷纷说真不该把那块匾送给他,那样我们就不在乎他同危险又可恨的洋鬼子交朋友了,我们应该把匾摘下来。他回答说:“我给你们种痘,并不是为了得到这块匾;如果你们要取下来,那就请吧。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误解了外国人。在预防天花方面,我所能做的一切善行都是从一位叫洛克哈特的好心肠传教士那儿学来的。并且我知道,这位传教士除了行善之外,并没有其它意图。因此,我必须尽我所能地善待他”。在我住宿旅馆的一两天里,麦金太尔先生问他的这位中国朋友,可不可以带着我去拜访他。他说,他很高兴见到任何一个麦金太尔先生的朋友。于是我就去了。那时,我很想知道,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在第一次读我们的《新约》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了解到他已把《新约》通读了三遍,我问他:“当你读它的时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思考了几秒钟后,他回答:“也许其中最美妙的思想是——一个人应该成为神圣灵魂的庙宇”。23不寻常的行医之旅,与布朗医生结伴1874年初,在离开济南将近五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烟台。这时,我发现布朗先生的中文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在秦牧师的协助下,他正在翻译一部重要的医学书,并且正在训练四名当地人,作为学生和助手。我回来不久,领事馆的马杰里()先生到布朗先生这边来做客。那天晚上,苏格兰圣经会的利磊先生也在座,他讲的那些滑稽故事使我们把肋骨都笑痛了;所有的故事,他讲的时候都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那年九月,马杰里先生离开汉口,开始了他那厄运已定的缅甸之行。1875年2月,他在迈文()被奸诈的中国人杀害。这年上半年,我和布朗先生打算在山东东部的半岛周围各县做一次旅行,在每个县城和中心集市停下来,在他为病人诊疗时,我在候诊室里向候诊者布道,依次安排病人去布朗先生的房间。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对外国人还非常好奇,为了保障秩序和安定,我们在到达县城前给当地的首席行政长官(县令)送去我们的名片,告诉他我们打算做什么,请求他安排两名警察(衙役)帮助维持秩序。县令们总是很有礼貌,毫不迟疑地满足我们的愿望。也有不少衙门里的人前来看病。每天一大早,布朗先生就开始诊治病人,工作非常繁重。担心他老这样绷着弦,身体会跨下来,我极力劝他一天不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但他就是不愿听。对他来说,病人的叫喊就是必须听从的呼唤。知道他的体能负担不起这样的超额“税收”,一天晚上,我用胳膊强行把他从岗位上拽下来,送回睡觉的房间。他治疗的许多病人很快就出现了好转,这在就医者看来简直就是奇迹。例如,有一天,进来一位男子,肚子痛得厉害,身体都蜷缩起来了。布朗先生给他开了一人剂量的药,十分钟后,他站起来,直起身子,睁开了双眼;惊奇于自己突然病愈,他大喊了起来:“我好了!我的病好了!不痛了!”这种戏剧性的广告场面使其他病人先是大笑,接着,意识到他是真的好了,都很急切地想得到药品,希望像那人一样药到病除。还有一天早晨,一个麻风病人走了进来,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带来了一些礼物表达他的谢意。他说,多年以来,他的手和脚都麻木了,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在服了昨天布朗先生给的药后,两手和双脚都有了刺痛的感觉了。在旅行的过程中,有一天我们恰巧住在了离宋村不远的一家旅馆里。前年,在参加规模盛大回龙山庙会之前,我曾在那儿住了两个礼拜。旅行时,我们乘坐的是一种叫做“什子”()的交通工具,是一前一后两头骡子中间挂着的一个有顶的吊床。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布朗先生的一个助手,帮助布朗先生配制并分发药品。这样,人和骡子加在一起,我们的队伍事实上把整个小店都占满了。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请店主结账时,他却一点钱都不收。他说:“你们来到这里,免费向大家发放药品;倘若我收你们的住宿费,那就太不对了。况且,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