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走-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文
第一章
我慢慢地走在街上,这几年的夏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一年比一年热。有报道说是因为工业大生产破坏了大气中的臭氧层,致使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大量涌入,不仅能杀伤皮肤,而且使地球温度升高。还有的说法说是因为大量工业废气的排放,和空调的大量使用产生了大量的热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温度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只穿了一件短T恤,可刚出来,身上就全是汗,湿湿的沾在身上,很不舒服。毕竟岁月不饶人了,有时候不服老是不行的,这上了年纪的人就是不能和年轻人比,我只不过才走了几十米,就感到气喘吁吁了。很久没有上街,这街上的变化都有点儿让我大吃一惊了,今天要不是小孙女哭着闹着要什么“伊利四个圈”,我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来的。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是最毒的,现在的人真是聪明多了,出门就带一把伞,反正现在这天气不下雨就有太阳,正好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下雨用来挡雨,天晴时用来遮太阳。
退休一年多了,我只是在家坐着不停地总结这一生的经历,基本上没有迈出过家门,现在外面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那不是属于我的世界,什么网吧、迪厅,什么保龄球、桑拿浴,在我的词典上都是没有的。今天的事儿也怨老伴儿,她抱着孙女看电视,广告里出现了这个伊利四个圈,结果小孙女看见了,就非得要不可。开始我没明白,这伊利四个圈是什么,老伴儿说:“就是雪糕。”我奇怪地说:“雪糕家里不有的是吗?她爸爸妈妈不是买了满满一冰箱吗?”老伴说:“那里面没有伊利四个圈,你快去超市给她买去。”
社会还是发展得真快,这雪糕都进了超市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以前的那种方式,那时候叫冰棍。卖的人都做一个木头箱子,用棉被包着,只在上面留一个小洞,开一个门,能把手伸进去就行了。那时卖得的人基本上是骑着自行车,也有推着小车的,上面绑着箱子,满街吆喝着卖,我一般都是在他们吆喝“处理了!处理了”的时候出场,因为这时代表他们准备清理箱子底回去了。我会拿一个大碗出去,这时候他们箱子里的冰棍剩不几只了,而且大多都化了,那种保温方式毕竟和现在是没法比的。他们会从箱子里把那些几乎拿不住的冰棍拿出来放在我的碗里,然后说:“一共六根,你给一半的钱,一毛五。”我端回家中,孩子就会高兴地蹦起来,虽然很多次他们吃时,都是要用勺子舀着吃,但仍然掩饰不住他们的喜悦,我一直都想,我是愧对孩子们的。
超市的布局让我感到晕眩,转了几个弯后,我就感觉转向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眼花,我走过洗发水的展柜时,粗略地数了一下,大概不下五十个品种,想想我那时,一年四季不论洗澡还是洗头,要是能有一块肥皂,简直就是上等的待遇,我们用的最多的烧碱。
最后还是问了售货员,才找到了雪糕在哪儿卖,这得浪费多少电啊!我想,还没见到这样的冰柜,上面没有盖,敞着口,那冷气像白烟一样一道道地往外冒着,这能挣回成本吗?一只雪糕才多少钱,这保管费用恐怕要超过成本。我一看标价,也吓了一跳,我以为看错了,又仔细看了一遍,才确定没错,是一支三块钱。这一支雪糕要三块钱!按现在的价格,在市场上能买半斤肉,一斤二两鸡蛋,在这里却仅仅等于一只雪糕。我想,无论它是用什么做的,似乎都不值这个钱,它又能用什么做呢?无非是水,糖,奶,还能有什么?
我还是没有找到老伴说的那种伊利四个圈,我觉得自己一个老头子了,在这里翻来翻去的找雪糕,似乎不太那么雅观吧!我还是把售货员找来了,售货员很客气地说:“对不起,这种产品我们还没上货,你看别的行吗?”她的态度很好,但是别的真的是不行,要不我也不用出来了。我只能再去其它的地方,虽然我很不情愿,但还得一步一步地去找。只是我的辛苦并没有换来成果,我找了几家店,都没有找到,我奇怪地问:“电视上都打广告了,这么有名的产品你们怎么不卖呢?”对方笑着说:“伊利离我们这儿有五六千里路,从那儿运过来,费用太高了,那价格也就会相应地很贵,恐怕没有竞争力,所以我们没进。”我明白了那个敞口大冰柜的存在原因了,凡存在皆合理,确实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它总有可以解释的理由。
买不到怎么办?这小孙女还在家里闹,老伴也就指望着我了。小孙女两岁了,正是最难看管的时候,谁拿她也没办法,是气不得打不得,什么事儿都得由着她。这可怎么办?可真难为我了。走在路上,突然想起了以前的事情,是关于儿子的。他很小的时候,大概也就五六岁吧!那是一年的冬天,快过春节了,所有的人都在忙着置办年货,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可置办的,就是买几斤鱼,几斤肉,顶多再备一套猪下货。这时候儿子却喊着说要吃黄花鱼,这黄花鱼可是那个年代的上品鱼,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的,回来就嚷嚷,小孩子也不懂事儿,和他不能讲道理,却也发不得火儿,而我当时的条件也根本吃不上黄花鱼。最后我想了一个办法,买了几斤带鱼,告诉他是黄花鱼,结果他信以为真地高兴了好几天。直到他长大后,有一天他回家说,今天上动物课我们老师讲到鱼类时,挂了一幅彩图,那上面的黄鱼和我小时候吃的不一样,我觉得我吃的那个怎么像带鱼。我只能说你记错了,那时候你才几岁,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又能说什么呢?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一个人对事物没有辨别能力时,离他最近的人可以影响他的观念,这种影响可能会是很长时间,或者是一生。就像儿子和黄鱼,如果不是以后他上学接触了,或许他会永远认为带鱼就是黄鱼,因为这是他父亲告诉他的,他可以完全地相信。
今天想起这件往事时,又触动了我的感觉,我想,可不可以把这件事再在孙女身上重复一次呢?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这个和儿子的不一样,我只不过是用一个其它牌子的雪糕去冒充伊利四个圈,它们都是雪糕,孙女只有两岁,当然不会认识上面的字,而且我也可以肯定,以她现在的味觉能力,也绝对不会在若干后对我说,“爷爷,这个伊利四个圈怎么和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不一样?”就算真有那一天,借口也会很多,毕竟这和用带鱼冒充黄鱼的性质不一样。
第二章
我就又回到了附近的超市,随便买了几支,提着回家了。老伴儿见我回来了,忙问:“买着了?这小祖宗可在一直盼着呢。”我走到老伴旁边,在她耳边低低地说:“这种牌子在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卖的,我随便买了几样,你就骗骗她吧!”老伴说:“这能行吗?”我说:“反正她也不认识,就试试吧!要不她闹起来可没办法。”
这个办法当然行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孙女高兴地吃着她要的“伊利四个圈”,老伴也高兴了,她就怕孙女闹。我就回到了我的桌子边,从退休后,我就一直想写点儿东西,但时间过去这么长了,我始终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经常是写了撕,再写再撕,很少有自己满意的。
我想从自己懂事时写起,那大概是在十二三岁吧,我的记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集体食堂,大炼钢铁…
我的家乡在农村,普通的中国小乡村,那一年,村里的广播喇叭每天都吼个不停,我记不清是喊什么了,我只记得爸爸让我和弟弟抬着家里仅有的一口锅送到生产队去,那是爸爸刚从锅台上拆下来的,我有些不可理解,锅没了,以后怎么做饭吃呢?结果爸爸大声吼着,“让你送你就送,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我只得和弟弟抬着去送,弟弟长得很小,抬锅很费力,我们就走会儿玩会儿,一里路走了半天,回家还让爸爸踢了一脚。
后来我们家就真的不再做饭了,我每天都到生产队临时搭建的大棚子里吃饭,妈妈就在那里面做饭,但是饭却一天比一天差,有一天我问妈怎么没有好吃的,妈说好吃的都在山上没有人去收拾回来。我问那爸爸呢?妈说他在干活儿。我问干什么?妈说炼钢。后来放学后我就到了山上,我发现满山的地瓜花生,却没有人来收,都烂在地里,我不明白,为什么家里没吃的,它们却烂在山上无人过问?
对于那段记忆我是没有权利去评判的,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有思考的能力,虽然现在有了,但我对当时的事情都忘得差不多了,即使有能记着的,我也不知道记的是不是就是正确。
所以我真正有资格去评论的是从清理走资派、当权派开始的。二伯是村支书,那时他却整天要戴着高高的纸帽子,在一群人的推搡下去游街。二伯家的墙上被刷满了标语,二娘每天都哭丧着脸,一听到街上有敲锣的声音,就吓得浑身发抖。尽管爸爸声明和二伯断绝兄弟关系,可我们家还是没有免遭牵连。我不能戴红袖章,不能和别人一起去串联,他们不允许我加入他们的队伍,所以我没有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活着的时候到天安门广场去见他,我见他时,已是在他逝世二十几年后了,那一刻我在外面,他在里面。
那时的斗争让人防不胜防,昨天我记着毛蛋他爸还押着二伯游过街,今天他们家的墙上也被刷上了标语,毛蛋他爸也戴上了纸帽子,脖子上挂着纸牌子,在一群人的推搡下,沿街游行。我听说是毛蛋有个什么堂爷爷在旧社会到南洋去当了劳工,现在有人说他是大资本家了。后来一次我回乡下见过毛蛋,问他那个当资本家的爷爷的事儿,他气的说,“我也一直都在找,如果真能找到,我现在也不用这么受穷了。”我想他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他根本也没有那做资本家的爷爷,或许他爷爷早在一次劳工暴动中被军警打死了。
那段岁月,我真的不想回忆,因为现在想起来,那就是一场梦,甚至还不如一场梦。那时候的人其实都应该是死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思维。到今天我才真正感觉到那段岁月的沉重,但我不是因为它给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伤害,而是那些年毁了我们整个的国家,直到今天,我们始终都没有走出它所带来的桎锢。
真正的生活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那时我的儿子都已经上学了,我也通过努力在这所城市找到了工作,在机床厂当了多年的工人了。那一年的确很热闹,农村的地都分给了老百姓自己,想种什么他们自己说着算,而且收入也是他们自己的。城里更热闹,东西再也不用凭票买了,什么布票、肉票全都不需要了,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去买。所以在一霎那,钱这个我们以前最不屑一顾的东西成了最硬的通货。我的钱是固定的,就是每月的工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它收入了。不过我一点儿也不羡慕,钱多了也不是件好事,说不定哪天再定成分,钱又成了区别革命同志和阶级敌人的标准。
我住在城里的“棚户区”,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像我这样的外来人口,能有个住处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想起分房这件事,我就觉得一阵的自豪,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了。这只是两间平房,很旧很老了,是以前的工人分房时交出来的私房,他搬楼房了,自己家的平房当然是要捐献给公家了。按照当时的排名,我是分不到房子的,所以别人都在忙前忙后,急着向厂长家送礼时,我一点儿也没着急,我想,我急也没有用,还没我的份儿。可就在分房子的前夕,不知谁得到消息说,厂里准备盖一栋楼房,今年就要破土动工,有了这个消息,能分到房子的人都开始沉默起来,他们想的当然是能分到楼房多好,谁还会要这旧平房。我不这么想,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份,我不能和别人比,也别想那么多,能搬出这集体宿舍,有这平房也就不错了。所以等报名结束时,名单上就我一个人,房子自然而然是我的了。当时有人说,真傻冒,等着分楼房多好。只是事情和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厂里并没有盖楼房,因为厂里连工资都快发不出了,还哪儿来的钱盖楼房?厂子的效益大幅滑坡,原因是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了,国外的产品技术水平既高,价格又便宜,一下子将我们的市场完全占领。
我印象最深的是厂长的脸,从那天开始就再没有见他笑过,几个月后他被调走,同事传言调到局里出任什么领导去了。后来我见过他,那是他走后好几年的事了,我在街上碰到他,他骑着一辆“大金鹿”,见到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我问厂长上哪儿去,他说没事儿,去买点儿菜。再后来,同事们都纷纷传言说,老厂长并没有升官,他把一个厂带垮了,又怎么可能升官呢?上面把他调走后给他安排了个闲职,没几年他就退休了,现在他在农贸市场贩卖海产品,有人在那儿见过他,穿着中山装,拿着一杆称,在那儿卖扇贝。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因为我见他那次就觉得他身上一股很浓的腥味。同事们都在感慨,想当年这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出入做的都是进口轿车,现在他只能骑自行车,去做了一名小贩。可生活就是这样,你必须要活下去,所以为了钱,没有什么不能干的。
第三章
好了,不说别人了,再说说我自己吧。厂子换了厂长,也没有扭转局面,这种局面也不是换一个人就可以改变的。但新厂长上任总是要烧几把火的,这第一把就把我烧焦了。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清理合同工,我虽然年纪一把了,在这厂里也干了十多年了,但很不好意思地是,我还是合同工,因为我不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所以我不能是正式工。结果我是首当其冲,成了第一批被解职的工人,那时候还不兴下岗这个说法。就这样没了工作?那怎么行?一家老小怎么办?
回到家中和妻子一说,妻子一脸的慌乱,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无论如何她一个人是撑不起这个家庭的重担的。妻子说:“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呢?”妻子说:“那别人是什么意思?”我说:“还能有什么意思?厂里和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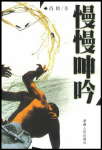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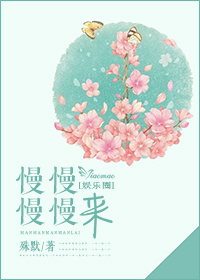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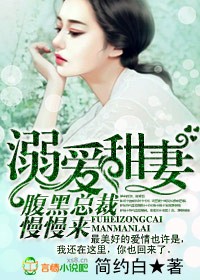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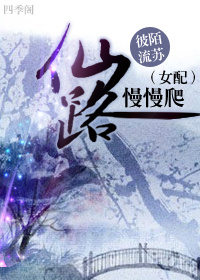
![忠犬遍地走[综+剑三]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90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