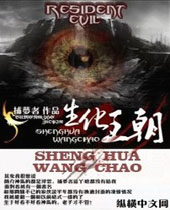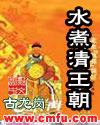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7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此,郑成功虽早已决定“移孝作忠”,却不得不在表面上与清人虚与委蛇,边打边谈,假借与清人和谈,以保住老父及家人的生命。
同时,借和谈的幌子,私下遣使与老父互通书信,在信中道出自己心事说:“但因一人在北,不得不暂作痴呆耳。”“我岂非人类而忘父耶。”
“乃到所以强忍须臾不得轻身一掷者,徒南望吾君,云天万里,北望吾父,喘息重圜,恐一朝落机阱,饱虎狼,为妇孺所笔,负君父重恩,靡有极端耳。”其情状之悲苦惨然,跃然纸上。
虽然在表现上,郑成功是一个大义灭亲的铁汉,然父子之情常使他不能自已,常于中夜起立北向,私自痛哭失声。“父子天性,情何以堪,以故居常悒忧。”
由于郑成功拒不投降,满洲人对郑芝龙的迫害一步步加深。先是软禁在京,后是被捕入狱,最后又举家被流放到宁古塔。之所以始终不杀者,是因为清人一直对招降郑成功报有一线希望。
东征台湾,有可能使郑芝龙最终丧命,对这一点,郑成功心里比谁都清楚。因为征台之举,向整个中华证明了郑成功不可能回头。老父也因此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发兵的那一天起,郑成功在心里其实就在默默等待着不幸消息的到来。
然而,当这个消息最终落实之时,郑成功还是没能使自己像期望中那样平静下来。就在与荷兰人谈判的过程中,准确的消息终于传来,1661年十月初三,老父终因自己拒不投降,全家十一人被清人杀戮,报至,“成功先叱为妄,然中夜悲号,不能自已,乃发丧,一军皆缟素”。
“忠臣孝子”,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男人的最高自我期许。命运对郑成功似乎格外吝啬,只允许他从中选择一样。郑成功用牺牲“孝子”为代价,以期成就“忠臣”,孰料孝即不能,忠最后也成泡影。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四月,就在郑成功初步平复丧父之痛,大举组织移民,准备把台湾建成复明基地之时,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吴三桂深入缅甸擒杀,大明皇统至此彻底断绝。
也就是说,郑成功这个最后的忠臣,已经没有了可效忠的对象。他竭尽全力,攻下台湾以图复明,而大明已经彻底灭亡。
不能不说,命运和郑成功开了个彻底的玩笑。
收复台湾,在郑成功看来,完全是因为以此支持反清复明大局才有意义。明既不能复,收复此岛,对郑成功又有何益?回顾一生,郑成功看到他一生其实一无所成。他戎马一生,仅保二岛,两次南下勤王,都成虚行,一次问鼎中原,则大败而回。奋斗到最后,父母兄弟包括侄子,都不能保住。
在还没有来得及起兵之时,那个赐郑成功国姓的隆武皇帝即已倾覆。
后来,郑成功虽然奉永历正朔,然而永历远在云南,兵微将寡,与郑成功难通消息,有君实似无君。而至此,连这个象征性的君主,这个精神支柱也已失去。郑成功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坚持到底为了什么。
第一十八节 孤臣辞世
两个接踵而来的噩讯,摧毁了三十九岁盛年的郑成功的心理平衡。就在此时,一件极小的事情成了压断郑成功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郑成功的长子郑经留守厦门,与奶妈私通,生了一个儿子。这类事情其实在“除了石狮子干净,剩下都不干净”的旧式豪门大家并不稀见。然而,治家极严又心绪极度恶劣的郑成功勃然大怒,说:“我欲成大事,乃不能治家,遑问天下!”立命使臣持令箭返厦门,斩郑成功之妻董氏,以明其治家不严之罪,同时并斩郑经、奶妈并其所生子。
在厦门的部下,当然无法执行这个过于峻切、有失人之常情的命令。他们集体抗命不遵。郑成功愤懑至极,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说道:
“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进退无据,罪案日增。今又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
临终又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顿足拊膺(yīng),“以两手抓其面而逝”。
享年三十有九。
(全书终)
后记 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第一节
一九九六年初,我把一个大信封投入邮筒,然后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否落了进去。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市巨鹿路675号《收获》杂志社”,里面装的是我的一篇历史散文:《无处收留:吴三桂》。
十五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收到《收获》杂志的回信。不过,我的“体制内文学生涯”确乎可以从初次投稿这一天开始算起。
第二节
只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这个字眼儿,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人人捧读文学期刊的时代。一篇小说在稍知名一点的文学刊物上发出来,则举国皆知,人人谈论。那是一个作家是社会精神导师的时代。
人们相信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是正义的化身,是未来的宣告者。那个时候,写作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发表一篇引起关注的小说,就可以使一个人从社会底层一夜之间变成万众瞩目举国议论的焦点。一个人如果揣本诗集,号称热爱文学,就可以行走天下(套用高晓松的话“那时的人们相信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人们相信会写诗的孩子更是好孩子),人心如同白莲花,刚刚绽开。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而我身处的辽宁省朝阳市,又是一个对文化和文学抱着特别质朴的尊重的边地古城。去年我回朝阳办理母亲的医疗报销事宜(母亲是在朝阳市退休的),异地报销手续繁琐,工作人员表情慵懒,公事公办,眼看着一天之内不可能办完。陪我去的表妹夫很机灵,对工作人员说,他是个作家!说着把我刚送他的一本书拿了出来。
顿时整个办公室人都轰动了,每个人都站起来,争相传阅这本书。科长给我端来了椅子,请我坐下,另一个人递上了热水。人们如同对待一个前来视察的大人物。一路绿灯,很快全部办妥。
在“作家”如此贬值的时代,此地对文字还保持着如此淳朴的尊重,那么可以想象二十年前这种尊重会是何等盛大!
古城里的人认为读书肯定是一件好事。并没有人教导自己热爱阅读,但是书籍几乎是小时候除游戏之外唯一的娱乐。初中时,我在朝阳市图书馆和市政府图书室各办了一个借书证。别无选择,借回家的都是“名著”,当然,是那些勉强能看懂的名著。什么《大卫·科波菲尔》、《鲁滨逊漂流记》、《基督山伯爵》、《名利场》……记得有一年夏天去北戴河旅游,我坐在大客车的第一排,手里捧了一本厚厚的《愤怒的葡萄》,因为看不懂而愤怒了一路。
一个初中生看《愤怒的葡萄》,这就是我成长年代的文化景观。一方面我们没太多书可读,另一方面,撞到手里的书大致都有着坚硬的品质,把每个读者都练成了钻头。浅阅读、轻阅读、软阅读这些词汇,当时尚未出现。
更多的文学熏陶发生在上大学的九十年代初,大学图书馆里的书毕竟更多。王安忆、韩少功、莫言、韩东、王朔,一本接一本。高中时没读下去的《战争与和平》重新再读,从此迷上了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没法不成为一个文学青年。
第三节
但是工作以前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当一个作家。在大学里,我业余时间大量投入书法和篆刻之中,加入了大学的书法协会。除了“作家”这两个字在我心目中过于崇高之外,还因为我莫名其妙地认为当作家是起码要人到而立有了阅历后才能尝试的事(形成这个印象也许是因为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作家大多是有了一把年纪的知青出身)。
开始写作发生在上班一年之后。写作的动因相当简单:无聊。大学毕业之后,本来是想好好工作,先“混”上(用我爸的话来说,是“熬”成)副处级,能用公款请客吃饭,在小城市里有地位有面子,这是一个北方小城长大的人的普遍理想。但是一九九四年大学毕业进入葫芦岛市建设银行工作之后,我发现“混”和“熬”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事:一个星期的工作,基本上一两天就能处理完。其他的大部分时间,主要都用来打扑克。那个时候,国有银行还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革,工作氛围和政府机关差不多。我记得有相当一段时间,每天上班之后不久,我们科里几个人就把门上的玻璃亮子用报纸一糊,在里面拱猪、炸金花,一打就是一整天。
这样的生活虽然自在,但时间长了,未免觉得空虚无聊。还有什么更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呢?在单位没法写毛笔字或者画画。那么,写点东西吧。
我想起我似乎还真有一点“文学天才”: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曾经被老师当作范文。托尔斯泰说过,成为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虚荣心。
很幸运,这个品质,我也具备。
写什么呢?什么都行,只要不平庸。要知道,我从小就爱把自己弄得与众不同。从初中就开始读每一本能弄到手的《新华文摘》,越是看不懂的长文章,看得越投入。初二的那年暑假,我还借了本《小逻辑》,在公园里硬着头皮读了十个上午,当然最后还是没读懂。从小只要是带字儿的东西,不论天文地理医学农业生物自然科学迷信甚至日历,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大学四年,我基本就是在大连市图书馆泡过来的,读得最多的,是历史书,还有那本介绍朝鲜人民幸福生活的《朝鲜画报》。所以截至此时,肚子里已经装了太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虽然“余秋雨”这三个字今天已坏了行市,但我从不否认,那种所谓“文化散文”的写法令我豁然开朗。这种纵横捭阖的叙述方式,正好将我一肚子的乱七八糟搅合到一起,一股脑抽出来。
半年时间里,我写出了《蒙古无边》、《无处收留:吴三桂》等好几篇很长的散文。其中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无处收留:吴三桂》这一篇。
对吴三桂感兴趣,是因为读了一本很薄的小书《叛臣吴三桂》,我发现,这个被严重脸谱化的人,年轻时居然是以“孝勇”闻名天下的。青年吴三桂是个美男子,下马彬彬有礼,上马武勇过人,颇为时人称许。从道德至高点走到一叛再叛擒“旧主”以事新主,他经历了什么样的精神地震和灵魂撕裂?我又买到刘凤云教授写的另一本书《清代三藩研究》,找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与吴三桂及那个时代有关的资料,从材料碎片中一点点复原吴三桂在重压之下如同蜗牛一样一层一层脱去道德面具的精神历程。
从文体上,它非驴非马,不是纯粹的散文,也称不上小说。它是一种叙述和思考的杂糅,是一种合金体的怪物。后来还是评论家们给这一类东西定义为“跨文体写作”。后来有人说:“张宏杰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典型的跨文体写作,掺杂了大量小说式、历史报告文学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写法。”
我对这篇东西相当满意,认为我可以开始文学青年的第二个规定动作了:投稿。
第四节
那个时候要成为“作家”,必须向文学杂志投稿。文学杂志是通向文坛的独木桥。网络那时刚刚兴起,网络文学这个名词还没出现。每一个“文学青年”,都先要在文学期刊上“露脸”。一般的路数是先在“省市级”文学期刊上“崭露头角”,然后在“国家级期刊”上引起关注。这样,你就有机会参加各种笔会采风之类的文学活动,有资格加入市、省乃至中国作家协会。接下来你的奋斗目标就是被一些知名评论家评论和文学权威认可,获得一些“省级”乃至“国家级”文学奖项,这样你就会在作家协会体系内混到一个“官位”,比如某市作家协会主席、某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这样你就算是功成名就,可以被称为“知名作家”,有资格出席“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或者“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之类的荣誉性大会,享受各级作协组织的免费出国采风交流之类的活动。这是彼时一个正常文学青年的作家之路。
那时候,人们做梦也想不到,十年后会有很多人比如当年明月,只须把文字发到网上,就有可能被广大网民关注,成为风行海内的畅销书作家。更想不到,一个少年韩寒,居然拒绝了进入作协的邀请。
那么换句话说,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文学杂志的编辑、文学评论者和文学权威,是一个文学青年成功道路上的三道闸门,你必须一一攻克。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先敲开文学杂志的大门。作为文学体制的一部分,到今天为止,全国各省都会有至少一本“纯文学期刊”。按照“文学圈儿”内的标准,文学期刊大致可以分为两级。一级是“省级”,比如辽宁的《鸭绿江》、黑龙江的《北方文学》,这些刊物影响比较有限,换种说法可以叫二流的文学期刊。另一级是“国家级”,其中也包括一些影响很大的地方刊物。大致有《收获》、《当代》、《十月》、《大家》、《钟山》、《天涯》、《人民文学》、《花城》、《作家》……大家心中公认的第一位,当然是《收获》。
和一般文学青年先从“省级期刊”投起不同,我第一次投稿,就把那篇《无处收留》投给了《收获》。
我决心要用这篇作品作为开头炮,轰开我的“作家”之路。相比当时文学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认为这篇东西绝不逊色。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它一定会得到编辑们的好评。稿件寄走后,我不停地幻想着这个大信封在收获杂志社内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我幻想着某天早晨,一位编辑打着哈欠漫不经心地打开这个信封,读了几段,他坐直了身子,又读了几页,他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连呼其他编辑来看……我幻想着这篇作品使中国文坛知道了有一个叫张宏杰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作家”,比余秋雨更善于讲述历史中的人性……我幻想着我的生活轨迹将从此变样。收到稿费、参加各种笔会、同事们刮目相看的目光、逃离这无聊的工作……通过写作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