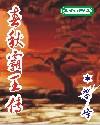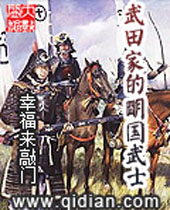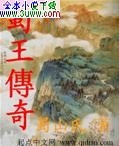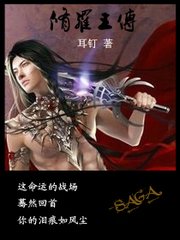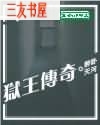渤海国武王传奇-第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琳叩头道:侄儿谢陛下隆恩。
接着许之元、大元义、大钦茂、大荣华、大松花、乌召度等人,都来给皇帝叩头请安。
玄宗皇帝特别把李琳和大钦茂叫到身边,笑道:你们两个可是有奇缘的。一个齐王的儿子,一个渤海王的儿子,都是金枝玉叶,贵为王子殿下,可都是老虎屁没人敢碰的。可是谁能想到,就是你们这两个没人敢碰的王子,却偏偏又双双做了囚徒,成了一对难兄难弟。今天你们见了面,有何感想啊?
李琳好奇地看着大钦茂,笑道:听说大钦茂给皇帝上过陈情表,我还以为他是个大人呢,原来是和我同样的年龄。
大钦茂低头说道:殿下在敖东城受苦了,我替父王大武艺向你陪罪。
玄宗皇帝笑道:现在讲和了,渤海郡还是大唐的藩属,四海之内皆兄弟,用不着陪罪了。你那道陈情表虽然有些稚气,却不失为一篇好文章。李琳要好好读一读,看看能不能做出同样的文章来。
李琳道:听了陈情表三字,就让我佩服不已。大钦茂学识在我之上,要是能和他一起上学就好了。叔皇陛下能不能给崇文馆下个旨,让大钦茂和我一起去上学?
玄宗皇帝笑道:这个主意很好。朕正在想用什么方法对大钦茂无辜坐牢给一点补偿,就让他陪李琳到崇文馆读书吧。
崇文馆是皇太子主办的贵族学校,只有皇家子弟才有资格入学。藩郡国王子都是在宰相主办的国子监上学。现在皇帝开了金口,破例恩准大钦茂入崇文馆上学,是一种破格的优待。大钦茂当即叩头谢恩。
大钦茂和李琳,两个同龄的年轻人,一个是渤海郡的王子,一个是大唐亲王的王子,却不约而同地成了战争的替罪羊,一个在长安遭软禁,一个在敖东城遭软禁,成了一对没有见过面的难友。现在和平了,两个人又一起到崇文馆上学,成了大唐朝贵族高等学府中的同窗好友。这件事本身就具有不同凡响的传奇性。他们由此开始的交往,对后来几十年的唐渤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更造就了许多神话般的故事。
大唐皇侄李琳平安返回长安,双方随即开始两军阵前的撤兵谈判。唐军阵前指挥官以后来者居上。赵含光是最新任命的范阳节度使,就成了河北和山东前线唐军的最高指挥官,幽州都督宋庆礼和平卢节度使薛泰都要听他指挥。渤海军方面的最高指挥官是大元帅张雨生。张雨生和赵含光就在幽州城外举行军事谈判。
政治谈判达成原则协议之后,军事谈判仍然有艰苦的路要走。谈得好,双方脱离接触,从此不再战。谈得不好,随时都可能重新亮剑,把政治谈判的成果葬送掉。。
这天晴空万里,气和日丽。在幽州城外平坦的草地上,有两支步兵卫队对面排开,卫队的后面各有一排彩旗飘扬,卫队的前方各有一面紫色文案,案后各有一张锦缦交椅。将近午时,有两支骑兵队伍簇拥着各自的首领从南北两方奔驰而来。北边来的是渤海军大元帅张雨生。南边来的是大唐范阳节度使赵含章。今天他们要在这里举行军事谈判。
赵含光在南面的交椅上就座。他做为唐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最关心的是渤海军早日撤离大唐土地。谈判一开始,赵含章就抢先提出撤兵要求。张雨生在北面的交椅上就座。他做为渤海军的前线最高指挥官,最关心的是完成战争使命,抓捕大门艺归案。两人各持已见,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赵含章想抢占风头,先发制人,开口道:既然是渤海军求和,请张大元帅先谈。
张雨生微微一笑,说道:今天是在幽州城外会谈,范阳节度使是主人。本帅不能喧宾夺主,还是请赵大帅先谈。
赵含章道:张大帅既然还知道幽州是大唐土地,就该知道兵犯大唐是反叛之罪。
张雨生针锋相对说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上,不容叛臣。本帅正是为了追捕渤海国叛臣大门艺才来到幽州。
赵含章说道:本帅接到廷报,说皇侄李琳已经返回长安,大钦茂也已恢复入侍王子地位,人质问题已经排除。请张大帅立即下令撤回渤海人马。
张雨生道:既然是停战议和,双方都要做出诚信的表示。渤海郡已经把李琳送回长安,大唐也该有对应的行动。
赵含章道:大钦茂王子不是已经恢复自由了么,怎么能说大唐没有行动?
张雨生回答道:渤海军是捕叛擒贼之师。只有大门艺归案,本帅才能下令撤兵。
赵含章道:请张大帅把部队撤至辽阳,本帅自会督促鸿胪寺尽快递解大门艺。
张雨生道:大门艺不归案,本帅寸步不移。
赵含章大怒道:既然你方没有和平诚意,本帅就只好拔剑相对了。
张雨生也怒喝道:李琳已经归返长安,我方的和平诚意早已昭示天下。赵大帅还想打下去,本帅乐意奉陪。
军事谈判陷入僵局。赵含章无奈,只好向兵部如实禀报,说不交出大门艺,张雨生不肯撤兵。是交出大门艺,还是继续打仗,请朝廷速作决断。兵部尚书薛纳不敢作主,立即向玄宗皇帝请示。
玄宗皇帝最头痛的就是大门艺,听了兵部的奏报,心情烦燥得很,说道:朕为了保护大门艺,已经吃尽苦头。这场战争就是因为大门艺而起的。现在要和平,必须把这个战争导火索拔掉。当初为了恩泽四海,法外施恩庇护了大门艺,却招来三年战乱,导致河北山东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早知如此,当初就不会包庇他了。可是现在真要把他送回去,朕还是有些不忍。双方协议刚刚成立,墨迹未干,朕又不能失信于天下。一面是不忍,一面是不能,让朕好生为难。大门艺的事是鸿胪寺惹出来的,就让崔忻来想个变通的办法吧。
鸿胪寺卿崔忻心想,把大门艺捉起来送交渤海郡,这是最简便的办法,陛下放着这样现成的办法不用,反倒让我来变通,这不是自欺欺人么。现在是既不能再留,又不能捉送,还想把事情平息下去,那就只好来个掩耳盗铃了。
崔忻奏道:依臣之见,可以派大门艺出任忽汗州长史,让他到敖东城赴任。只要他离开大唐,发生什么事情都与陛下无关了,大武艺也没有理由再来要人。
玄宗道:这样一来,就要委屈大门艺了。但愿大门艺能够理解朕的苦心。就按崔忻的建议办吧。
崔忻领了皇帝旨意,派人给大门艺送去皇帝圣旨和忽汗州长史的官服金印,要求他立即走马上任。
大门艺隐居在洛阳,天天关注着战局的变化。他忘不了齐殿逢给他出的好主意,盼望大唐军队大获全胜,消灭了大武艺,好让他回国称王。可是三年过去了,唐军没有打退渤海国的两路人马,张雨生也无力挺进到洛阳城下。双方僵持起来,大门艺的心也提了起来。他知道僵持是暂时的,结局总是要出现的,不知这结局会给自已带来怎样的下场,他开始为自已的前途担忧。后来,大武艺突然决定和谈了,大唐朝从皇帝到平民都欢呼和平的到来,大门艺预感到未日就要来临。他祈求上苍保佑,给他一个奇迹,让大唐皇帝再给他提供一个生存的机会。这天突然接到皇帝圣旨,让他出任忽汗州长史,就象一声晴天霹雳,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他知道这是大唐皇帝不肯再提供庇护,让他自已回去送死。他接了圣旨,知道再也没有活路,回去也是送死,还不如死在洛阳。大门艺走投无路,就想一死了之。他向长安方向跪拜再三,又痛哭了一回,再在忽汗州长史金印上写了一行字:愿以一死报君恩。然后就要拔刀自刎。
可是,就在他把刀架上脖梗的一瞬间,突然鬼使神差地向那颗金印上瞄了一眼,这一瞄就发现那印盒的夹层中露出一角绢头。他心中好奇,上前把那绢头抽出来,就看见上面有一行小字,写的是:欲求生,投新罗。
大门艺惊喜万分,把刀一丢,捧着绢条仰天大叫道:苍天有眼,我有活路了!
新罗国与渤海国是敌国。大门艺要想求生,投奔新罗国是唯一的出路。奔新罗国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经幽州,二是经山东。无论走哪条路,都可能会遭遇渤海军的拦截。他必须求助于唐军的保护才能通过。幽州方面的唐军统帅是赵含光和宋庆礼,他都不熟悉,不敢去求助。山东方面的统帅是薛泰,是保举他在幽州军中任职的恩人,一定会再帮助他逃生。他就打定主意走山东。当即收拾行装,向河南府剌史李长春告辞,说是奉旨出任忽汗州长史,要取道山东,渡海赴渤海郡。
河南府剌史李春来已经接到朝廷通知,只要大门艺肯离开大唐土地,就不必管他。这时李春来就派人暗中监视大门艺,见他确实离开洛阳往山东去了,就向长安发出快报。大唐朝廷上下以为他是去向张文休投降,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鸿胪寺立即把这一新情况通知赵含章。
幽州前线的赵含章接到朝廷发来的廷报,说大门艺出任忽汗州长史,已经离开洛阳,正在赴任的途中。赵含章当即约请占生来会谈,把廷报拿给张雨生看过之后,向张雨生说道:大门艺即将返回敖东城,请张大帅立即撤兵。
张雨生看了廷报,知道这是大唐皇帝不肯再为大门艺提供庇护的信号,大唐境内已经没有叛臣大门艺的存身之地。可是,现在大门艺毕竟还没有回到敖东城,捕叛擒贼 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岂能轻易撤兵。张雨生向赵含章说道:既然然大门艺已经离开洛阳,正在返回敖东城的途中,本帅就再等十天半月,一是有了确切消息,保证立刻撤兵。
赵含章忿怒道:大唐宰相府发来的廷报你还不信,是不是根本就不想撤兵?
张雨生不相让,也怒喝道:本帅早就说过,大门艺不归案,我军寸步不移。
双方又僵持起来。赵含章就暗中集结部队,作好战斗准备。榆关总兵许钦澹见赵含章有攻击渤海军的迹象,立即赶到赵含章大营来劝阻。赵含章则下令把许钦澹软禁起来。河北战场又一触即发。
第八十一章 小绢头指路 大门艺走海
大门艺离开洛阳,单枪匹马一路向东而行。他的心中一直在想着那个救命的绢条。他知道印盒中的绢条不会是鬼神送来的,一定是有人放进去的。那会是谁呢?是大唐皇帝安排的吗?不可能。因为皇帝要想救一个人会有许多好办法,绝不会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会是兵部尚书薛纳吗?有可能。因为薛纳最想看到渤海郡的分裂和衰落,可能故意放虎归山,给大武艺制造麻烦。会是鸿胪寺卿崔忻吗?也有可能。因为崔忻希望大门艺活下去,好对桀敖难驯的大武艺有所牵制。也许还有其他人,不一是是为了救大门艺,而是为了给渤海郡制造麻烦,故意要把水搅浑。大门艺越想越胡涂,索性不去想了。
他一路打听山东前线局势,知道薛泰大军在高唐州驻扎,就直奔高唐州来投薛泰。
薛泰二十天前接到兵部命令,要他原地待命,等待范阳节度使赵含光的指令。薛泰这些天见张文休大军也自动往青州撤去,料定和谈已经成功,渤海军就要撤离山东,他的平卢军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控制山东沿海。薛泰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时候大门艺会出现在他的营门前。这个人可是战争的导火索,是渤海军追捕的目标,已经列为和谈的条件。此时他突然到来,绝不会是好事。
薛泰把大门艺引进后帐密室,急切地问道:朝廷发来的廷报说你已出任忽汗州长史,怎么会到山东来?
大门艺不敢说出真相,扯谎道:正是要去敖东城赴任,才取道山东。
薛泰信以为真,说道:山东沿海各港口码头均被张文休控制,你要从山东出海,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大门艺不动声色地说道:请薛大帅为我寻一艘新罗人的小商船,把我偷渡过去。
薛泰满脸大惑不解的神情,说道:长史赴任居然要偷渡,岂不是太荒唐了么?
大门艺苦笑道:你把赴任和偷渡连在一起,确实很荒唐。
薛泰恍然大悟道:我知道了,你渡海不是要去敖东城,而是要投往别处去。
大门艺道:薛大帅心里明白就是了,不要说出来,免得惹出是非。我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磨难,如今仍是死里逃生,不得不走此险路。请薛大帅无论如何要再帮我这一回。
薛泰心领神会,说道:我只是为你寻一艘小船过海而已,其他事一概不知。
大门艺在薛泰营中隐藏起来,只等找到船时就上路。
因为双方的军事谈判还没有结果,渤海国的谈判大使乌召度一直滞留在长安。乌召度一方面盼望军事谈判早日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则切注视大唐官场上的动向,给张雨生提供情报。
这天早晨乌召度刚刚派人向张雨生送出情报,说大门艺已经离开洛阳去了山东。情报送出之后,乌召度到齐王府去会大元义,见大元义正和许之元激动地争论着,双方都面红耳赤,似乎遇到了天大的麻烦。可是乌召度来了之后,他们又缄口不言。
乌召度心中疑惑起来,严肃地向二人说道:二位也是来和谈的重要成员,如果有事应该向本官通报一下。
大元义看了看许之元,说道:许之元听到大门艺的消息,不知是否属实,正在和我议论。
乌召度道:实与不实,都应该让本官知道。许之元,你且说说看。
许之元道:刚才永王来访齐王,我刚好从厅上经过。我是无意中听到齐王和永王的几句谈话,说大门艺离开洛阳去山东之后,并没有向张文休投降,而是潜入平卢节度使薛泰的大营中,伺机出海逃亡。也不知得是否准确,还不知该怎样向乌大使禀报。
乌召度震惊道:这样重大的消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大门艺出海逃亡,不仅三年的仗白打了,我们的和谈也毫无意义。我们必须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张雨生,让他设法拦截。
张雨生先得到了乌召度早晨从长安送来的情报,说大门艺确实离开洛阳,正在取道山东赴渤海郡。张雨生看着这条情报,心中生出许多疑问。大门艺离开洛阳应该是真的,取道山东赴渤海郡却很可疑。他明明知道我的中军大帐在榆关,为什么不走幽州来向我联络,却要舍近求远绕道走山东?
张雨生正在纳闷,紧接着又接到乌召度中午从长安送出的新情报,说大门艺走山东是为了出海逃亡。张雨生这才恍然大悟,从山东出海,既可以奔渤海国,也可以奔新罗国,难道他要投奔新罗国不成?对了,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