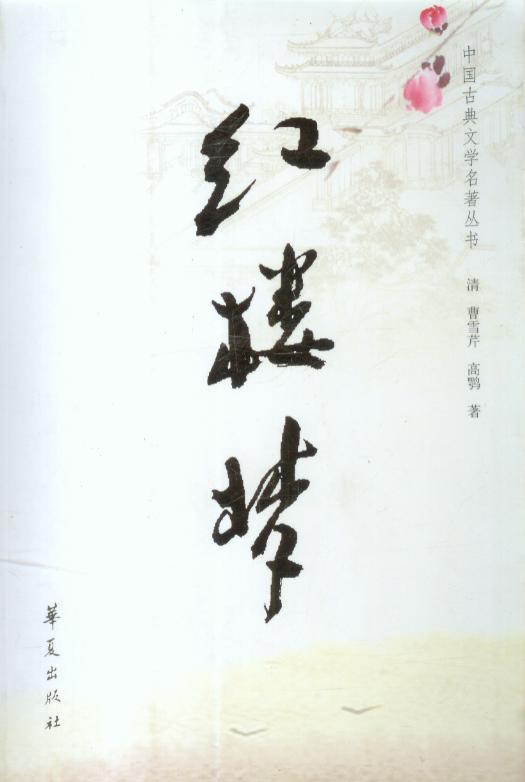沉默的钟楼-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时,老吴回家做饭去了,你在种马舍替他值班。老吴走后,你在马舍前后转了一圈,就回到屋里躺在了炕上。炕烧得正好,你躺在上面没一会儿便睡着了。
傍晚时分,你在睡梦中被老吴摇醒。
“快醒醒,迪克,快醒醒……”老吴使劲摇着你,惊叫着,“迪克,出事了!”他脸色蜡黄,浑身颤抖着,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上滚落下来。“出大事儿了!”
“怎么啦?”你一轱辘跳下炕来。
“马死了……”老吴手足无措地瘫软在地上,吓得嚎啕大哭起来。
你跑到屋外时,见那匹死掉的种马已经被抬到了种马舍前面的空地上。死马周围站着不少人,兽医也来了,当场检查的结果是:种马的胃里有一颗钉子,造成胃穿孔后死亡。
“这钉子是被掺进马料里的,”指导员刘大林神情严肃地说,“无疑,这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不然的话,钉子怎么会进到马肚子里去?”他指着老吴斥道,“这马你是怎么喂的?这不是存心破坏连里抓革命、促生产又是什么?”他说着,又转向人群,“同志们,看清楚了吧?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多么触目惊心啊!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典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敌人已经向我们下手了……”
“指导员,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马刚才还好好的……真的……上午还好好的……我不知道怎么会成了这样。”老吴摇着他那只伤痕累累的手,绝望地解释着,声泪俱下。
“你不知道?”刘大林阴森的目光扫视着人群,最后停在了你的身上,冲着老吴逼问道,“你是养马的,你不知道谁知道?难道这地方还有外人来过吗?”
老吴语塞。
“我在这儿,”你平静地说着,一步跨上前,按下了老吴那只不停挥舞的手,将他挡在身后。“刚才老吴回家做饭去了,我在这儿替他值班。”
“你替他值班?”刘大林狠狠地瞪着你,吼道,“难道你不清楚,种马舍里是不让外人来的吗?”
你没回答。如此场景已经使你多少揣摩出了一些端倪。这事是冲着你来的,是和那天晚上在连部发生的那一幕联系着的,事已至此,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了,你对此早有预感。
沉默的钟楼 33(1)
你在那时还不知晓,只要处在一个备受压迫的环境下,只要处在一个出于政治需要而进行的专政环境里,无论是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所有的审讯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找到你有罪的证据而非证明你清白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有导演、有演员,上场顺序不同,担任的角色亦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诱使或迫使你循着他们为你提前设计好的思路招供。一般情况下,导演就是组织者,就是你招供思路的设计人,他手里有两件迫人屈服的法宝——暴力和时间。你在十九岁的时候无法躲避地掉进了这一圈套里,担任的角色是受审者。
你被关押在连部,就是你发现刘大林和连部女文书乱搞的那间屋里。原来在这屋里的那张木床和办公桌柜等已被搬走,空荡荡的屋子里除了两个条凳和一把椅子之外再没有其它东西。你是在种马死亡后的第三天晚上被以指导员找你谈话为名先叫到连部后被关押起来的。审讯在午夜开始,审讯组由刘二林和另外三名积极要求入党的知青组成。坦率地讲,这样的组合无论是受审者还是审问者都不能算是内行,双方都想在实践中试图找到战胜对手的办法。但对方的优势在于刘大林在来到连里当指导员以前,曾在地方的公安部门干过几年,他懂得该如何下手和掌握火候。
第一次审讯是在喝斥和辱骂中开始的,他们除了反复逼迫你承认在马料里放了钉子之外,再没有其它任何旁敲侧击的方法,审讯的气氛一直绷得很紧,毫无节奏可言。这使得你原本紧张、惶恐的心情竟慢慢地适应下来,你在滴水不漏地解释完了你根本没有做那种事之后,便一直保持着沉默,任对方焦躁万分、歇斯底里,你始终以一言不发应对。终于,对方的神经和耐心像一根紧绷着的弹簧突然打开那样失去了控制,他们开始动手了。先是推搡、耳光和拳头,这些你都忍受了,接下来他们拿出了预先准备好的棍棒。当你的脑袋结结实实地挨了从身后袭来的一棒,你被打得眼冒金花、鲜血直流的时候,你爆发了。如果当时只是刘二林一个人在对你进行殴打,你想自己甚至还可以忍受下去,但你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那三名知青对你的殴打。因为你平常丝毫没有得罪过他们,甚至有时还在一起干活聊天,你觉得相处得还算不错。你真是无法理解,同是知青,无怨无恨,在你遭到了明显是陷害、起码也是一场误会的情况下,他们怎么能只为了自己的所谓进步、积极表现和阶级立场鲜明,就对你狠下毒手呢?
反抗一旦开始,你便失去了理智。你像一支沉睡着的猛虎突然醒来似的一跃而起,扑向刘二林。显然,屋里的所有人谁也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场面发生,混战开始了。五个人打成了一团。你不顾如雨点般打在身上的棍棒,机智地将头部藏在刘二林的胸前,死死地揽住他的脖子,用尽气力攥紧拳头,朝着他的腹部击打着。你感到刘二林的全身已经软下来了,脸色蜡黄,张大着嘴喘着粗气。终于,他再也坚持不住地从你的臂弯里出溜下去,瘫倒在了地上。你在用脚踩着刘二林的同时,又转向了另外三个人,用头撞,用肘拐顶,勇猛异常,像是要将长时间所受的压抑都在这一刻发泄出来。椅子倒了,凳子飞了起来,混乱中,那三个人手中的棍棒不只是打在了你一个人身上。你攥住了一支棍子,试图将它抢过来,争夺中,你清楚地感到了对方手指的松动,渐渐地对方快要顶不住了,你将要夺过棍子,终于夺到了,棍子已经完全攥在了你手里任你挥舞了。但突然你感到天塌了一样,一片昏暗,眼前直冒金星,你的头部被棍棒重重地击了一下,你倒在了地上。你感到那一刻似乎有无数只魔爪抓住了你,无数根绳索套住了你。
可惜你并没有失去知觉,棍棒那重重的一击只是将你打得瘫软无力,晕头转向。当你睁开眼睛,环视屋内时,感到自己正被压在地下,双手和双腿已经被结结实实地捆住了。他们将你扶起来,又拉过来屋内唯一的那把椅子,把你按坐在椅子上,仔细地将你和椅子捆成了一个整体。
“这下好了,看你这狗崽子还动,反了天了你!”知青们说着,掏出香烟来抽着,喘着粗气坐在了地上。
刘二林显然是被你刚才打得够呛,此刻他靠坐在墙角上,脸色依然蜡黄,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他一手捂着腹部,拿着烟的手在不停地抖动着。不一会儿,他扶着墙站起身,走到你跟前。
“你小子够有种的,还敢反抗……”他说着,抬手狠狠地抽了你一个嘴巴,然后将手中的香烟紧嘬了两口,一把扯开你的上衣,将手中的香烟摁在你的胸膛上,重重地捻了下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你到底说不说?”
你疼得浑身一颤,旋即闻到了一股皮肉被烧焦的糊味儿。你慢慢地睁开眼睛,瞥着刘二林。“再使点儿劲,”你轻蔑地说,“没准儿它能粘上。”
“给我打!”刘二林气急败坏地一脚将你喘倒在地上。
对方在休息中获得了体力,棍棒不停地、重重地打在了你的身上,捆绑在你身上的椅子都被打劈了,长长的木刺扎进了你的肉里。对方刚一开始还在辱骂着你,边骂边打,一下、两下、三下地为自己数数加油,但到后来全没了气力,嘴里不再出声,只是一下重似一下地杖击着你。他们脱去了你的鞋子,开始用棍棒槌击你的脚掌。你感到难以忍受了,那不仅是一种钻心的疼痛,更像是一股电流在电击你的身体,从脚心传向大脑,再从大脑传到耳朵、心脏、胃部、腹部、再到膝盖,最后在腹部和膝盖处集结处痉挛、绞痛。终于,你昏死过去。在昏死过去前的那一瞬间,你突然觉得世界一下子变得寂静下来,安静极了,似乎只有一群蜜蜂在你耳边嗡嗡作响,浑身上下没有了疼痛,什么知觉都没有了,你感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轻松。
沉默的钟楼 33(2)
窗外,黄方痛苦万分地闭上了眼睛。自从你被带到连部后,他一直就躲在不远处偷窥。他眼含泪水地看着你惨遭毒打,自己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真令他心如刀绞。他抑制着自己一阵猛似一阵的想闯进屋里的冲动,紧紧地贴在墙壁上,反复地告诫着自己,冷静,千万别冲进去,那样除了把自己也搭上,根本救不了你,什么作用也不顶,只会更坏事!沉住气,等机会,更重要的是想主意。
再一次的审讯仍然是在午夜。当你重新睁开眼睛,首先感到的是刺眼的灯光。你发现不仅自己的手腕和脚腕被捆着,而且你的腹部也被一根宽大的皮带缚着,上次被打劈了的椅子又被换成了新的,你依旧被层层缠绕的绳子结结实实地捆在椅子上,令你一点儿都动弹不得。你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觉得它很厚,你想嘴唇一定肿胀得十分可怕。你试着抬起眼皮,但上下的眼皮粘在一起,你想眼皮也一定肿胀的十分可怕。透过迷雾般粘住的眼睫毛,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你费力地辨认着,终于辨认出,站在你近前的人是刘大林!导演终于出场了。
“你终于醒了,这就好。”刘大林连着说了两遍,弯下腰,像一片云雾似的遮住了你。“这些人太不像话了,把你身上当成烟灰缸了。”他摸着你被烫得伤痕累累、布满了无数细小麻坑的胸膛,说,“我一定得处分他们……怎么样,想通了吗?”
你摇了摇头作为回答。
你当时还不懂得真正的审问者并不打人,他靠谈话、威胁、利诱和突然袭击。因为真正的审问者知道,高明而出色的审问并不在于肉体折磨,而在于折磨受审人的心理。因为他知道,遍体鳞伤的受审者一定会高兴地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仅仅用语言来折磨他的人身上。因为他知道,在经历过无数痛苦之后,受审者一般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对继续受到的酷刑的抵抗力,花样翻新和持续加重的肉体折磨,常常不会产生预想的效果,反而会增强你的抵抗心理。真正高明的审问者,总是在第一幕或连续几幕落下之后才开始露面。他和蔼地提出问题,耐心地等你回答,敏捷地研究和思考你们之间的对话,甚至能够长时间地、假装高明地容忍来自被审者的轻蔑和沉默。他能够吃透你的心理,从中发现被审者致命的心理弱点,并在关键时刻给你一击,使你产生恐惧、怀疑、无所适从,直至最后完全垮下来。不幸的是你遇到了这样的对手,刘大林尽管还不能做到十全十美,无懈可击,但对付你这样毫无受审经历的人,还是绰绰有余。
他坐在你的面前,悠闲地翘着二郎腿,吩咐打手们将你的双手解开,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没有松开绑在你腿上的绳索。他掏出香烟递给你,并为你点上,又递给了你一杯水,完全摆出一副聊天的架式。
看着你将那杯水一饮而尽,刘大林又向打手们吩咐道,“去打两壶开水,再到我办公桌上把从北京带来的好茶也拿过来。”
茶水沏上了,屋里飘散着茉莉花茶淡淡的茶香。
“事已至此这四个字你明白吧?”刘大林边问边在你手边放了一盒香烟和火柴。“我理解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承认现实。什么是现实呢?就是连里,不,是团里价值昂贵的种马被人故意害死了,而你作为一名主要的嫌疑犯被连里扣押起来,这就是现实。我说的这些绝不是没有意义的重复,而是一种完全出于善意的提醒,对于你来说,承认这种现实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处在你现在这样一种境况下,头脑并不是十分清醒,自负、固执、仇恨,整个人处在一种失去理智的、不计后果的、顽固对抗的情绪当中而难以自拔。”
他停顿下来,呷了一口茶,站起身来回踱着步子,后又坐在了你的对面直视着你。
“你沉默,这很好,沉默就意味着同意,就意味着咱们之间已经开始可以说上话了,不能说全部,起码你也是部分地同意了我的观点。我现在就来帮你分析一下你目前所处的现实,我逐条地分析,你看是不是有些道理。
我先来假设你配合连里工作,承认犯罪事实的好处。一是你可以尽快地得以解脱,只要你承认下来,明天就可以恢复自由。你还很年轻,今年才十九岁吧,今后的人生道路还长着呢。列宁都说过,要允许青年人犯错误,也要允许青年人改正错误。你何苦非要在此与连里较劲,与自己过不去呢?尽管你出身于反动家庭,但能否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啊。
二是可以令你的父母不至于因为你的问题而加剧他们本来已十分难熬的困境。他们都已经被轰回农村劳动改造去了,这些连里早已经掌握,如果我们将你的情况向当地的党组织和贫下中农们通报过去,那他们会得到些什么呢?
三是你不但可以救己还可以救人。案发现场只有你和吴树人两个人,非常清楚,作案者非你即他。平日里,我看你是个挺精明的人,怎么轮到这事就犯起糊涂来了呢,不但糊涂,而且还不够仗义。吴树人和你的身份不同,这一点你清楚吧?你是知青,无论你犯了什么事儿,也改变不了你的知青身份。对待知青,即便他是一个犯了事的知青,党的政策总还是教育为主吧。而吴树人就不同了,他是刑满就业的劳改犯,是阶级敌人,对付他和对待你,党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咱们今天是关起门来说话,要说吴树人这辈子也不容易,年轻轻的就进了监狱,这么大岁数了,手又被炸坏了,还拉扯着个孩子……我知道你们关系不错,你还教那孩子打球,你难道就忍心明天我们也把吴树人抓进来?
沉默的钟楼 33(3)
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将这件事承认下来,当然处理肯定是要处理的,就算是劳改吧,时间也不会长,半年,最多一年这事就算过去了,一风吹,你仍旧还是知青嘛!”
你抽动了一下。你心里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