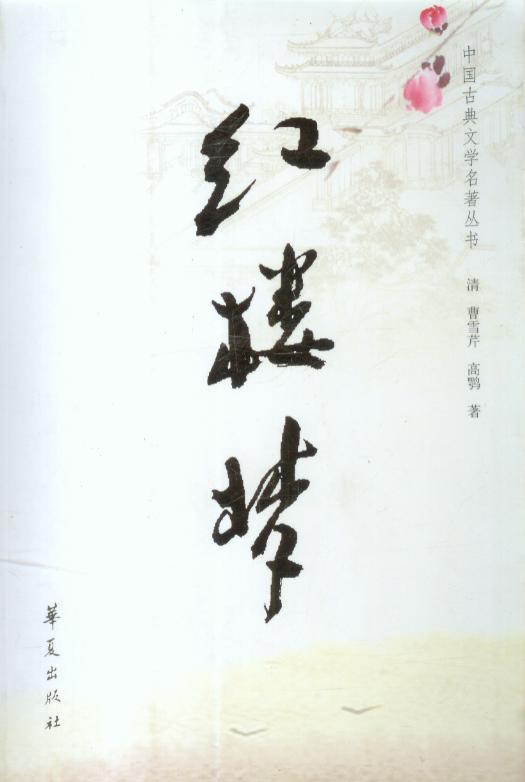沉默的钟楼-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地方住下来,先离开这里,一切都等到车跃进回来再说。
车跃进是一个星期之后回来的,几次见面下来,他便天天晚上来找尤菁菁了。车跃进那南方男人特有的细腻、温柔和体贴,令尤菁菁感受到无比温暖。另外,由于长期单身生活的磨炼,他还练就出一手做饭的本事,每次在一起吃饭,通常是由他来做。由于他俩都爱吃鱼,市场上又没有卖的,所以他俩就去郊外钓鱼。明媚的春光下,俩人依偎在青青的草地上,静静地注视着在波光粼粼的的水面上不停晃动着的鱼漂,安详得令人陶醉。一天,他还叫上地委领导的的小车,带上她去逛了趟平遥古城。一路上,他博古通今,侃侃而谈,兴致极高。历史知识,古今传说,无不被他讲述得有生有色,听得尤菁菁对他简直有些崇拜了。
她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他们的热恋,从心底里希望这样的时光能越长越好,但她又想找个机会述说自己的困境,请他想出一个好的办法。他曾问起过她为什么一直不去上班?她推说自己有病,又不喜欢那个学大寨组舞,所以才一直没去,他相信了。那段日子里,他们之间的感情升温很快,车跃进甚至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请求。
一天晚上,他俩终于冲破了恋人间感情的那道最后的闸门,忘我地陶醉在数次疯狂的做爱中。他那温柔备至的爱抚,强健有力的冲动,令她在感到无比幸福的同时,心中涌起一种深深的愧疚,她感到自己再不该对他隐瞒什么,而应当把深藏心中的苦痛和需求对他和盘托出。
她这样做了。
她眼含热泪地诉说着李秋龙的种种恶行和她艰难的处境,车跃进始终默默地听着,两眼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脸色铁青。
隔了一会儿,他问道,“你没有对其他人谈起过此事吧?比如团里的其他领导或地区的领导们。”
“没有,”尤菁菁说,“这事怎么能对别人讲。”
“那就好,”他叮嘱道,“这种事如果不想好了,千万不能采取什么动作。”
她依偎在他的怀里,紧紧地搂抱着他,轻声道,“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别多想了,如果你能帮我调出文工团那更好,办不成也没有关系,大不了我再回村里,反正我是不会再去那里上班了。我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有你,有你在我身边我就满足了。”
他双手捧着她的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突然,他翻身伏在她的身上,又一次进入她的身体里……
拂晓时分,他们吻别。尤菁菁恋恋不舍地拉着他的手半天没有松开。
“晚上早点来。”她说。
他“嗯”了一声,抽出他的手,走到门口时又一次回头看了她一眼,脸上带着异样的神情。敏感的她立即捕捉到了他那种复杂的表情,还没容她说什么,他就匆匆离开了。
那一天,她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她想像不出她对他说的这些会对车跃进产生什么样的压力,会对他们之间的感情产生些什么?她不敢再往深处想。想来想去,她反过来又找出了不少理由来安慰自己,但种种不祥的预感还是不断地在脑海里涌现出来。也许跟自己交往会影响到他什么,毕竟李秋龙的哥哥是即将上任的地区革委会主任,是车跃进的直接领导,和自己交往下去对他今后的仕途肯定不会是一件好事,更何况李秋龙是全团皆知的那种睚眦必报的人。她不敢再想下去,只盼着夜晚早些到来。
沉默的钟楼 49(3)
那一晚,车跃进没有来。
第二天他仍然没有来。
第三天,尤菁菁实在忍不住,冒着被李秋龙发现的危险,跑到地委办公楼里去找他,却没有找到。第四天她又去找,依旧没有找到。一个星期后,她终于还是从那位烧茶炉的老人口中得知,车跃进已经临时被抽调到省委、去太原上班了。
还有必要去太原找他吗?她反复地问着自己,一个在爱情和仕途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仕途,而将爱情丢弃在一边、毫无信义地背叛的人,难道还能指望他回心转意吗?也许他还会这样认为,对一个不干不净的女人、一个被别人强暴过的女知青,是实在值不得他去牺牲什么。
最终,尤菁菁没有去找车跃进。在度过了好几天以泪洗面的日夜之后,她将自己的全部东西都送给了那位待她不错的女房东,登上了返回北京的列车。
如果说,在她生活中的前两次噩运都是魔鬼给她带来的,那么这一次她的最爱给她带来的是更为惨痛的伤害。这种伤害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她开始了仇视,在不断地伤害着自己的同时也伤害着别人,她堕落了,自甘堕落,以堕落回报着这个使她备受伤害的时代和社会。
沉默的钟楼 50(1)
你终于又回到了北大荒,在别人都日思夜想地要永远逃离这里的时候,你回来了。一年多颠沛流离、心惊胆战、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使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过上有人管、有人问、有组织、有单位的日子。这要放在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举动,甚至会怀疑你是否弱智或无能,但你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原因很简单,时代不同了,如果说今天的社会能向人们提供一百种生活方式的话,在当时也就是一、两种。社会不允许另类存在,人们的思想全都禁锢在非敌即友、非此即彼的愚蠢之中,全都像木偶一样被一种思想操纵着,浑然不知所觉。
回到连里的日子踏实、顺遂,你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回连后的第一天连里还特批了你一天休假,令你睡了近两年来最安稳的一觉。几天后,连长还招呼你到他家吃了顿饭,酒酣耳热之际,连长对你历尽严刑拷打而终不改口,保护了老吴一家的事称赞不已,说你和黄方的为人都称得上是爷们儿,这样的人值得交。尽管你在回连之前就已经知道,刘大林因为强奸多名女知青而被判刑,但连里对你的热情还是令你出乎意料。趁着连长提到了黄方,你顺着话口提出想去探望一下他,连长很爽快地同意了。
那是你平生第一次进到监狱里,铁门、高墙、迷宫式的房子,你猜想这样的地方如果只走过一次,恐怕再放你出来,任你选择路线都很难逃出来。监狱座落在一片旷野当中,四面是庄稼,距离公路和铁路都很远,只有一条颠簸的土路通达这里。附近没有其他单位,土路上不时有哨兵游动。
你跟当班的管教聊得不错,毕竟你是兵团战士,所以他也并没有十分戒备。攀谈中得知他是从河北参军的,你又不失时机地攀起了老乡,并把你从北京带回来的高级雪茄烟塞进了他兜里。
“黄方这家伙表现得还可以。”管教说,“这小子挺聪明啊!当初他的案子有很多地方对不上茬口,疑点不少,说他是谋杀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关键是你们连里、团里的证明材料救了他,说他性格单纯,表现一直不错,根本不具备杀人动机。”
“那是,他确实是出于好奇,”你说,“在连里时他什么都想动动,可什么都做不好。”
“哼,不是那么回事吧?”管教怀疑地说,“我们这儿也种地,去年夏天拖拉机陷在泥塘里开不出来,这小子上去几下子就鼓捣出来了,我当时就看出来了,他是个熟手……”
“那是他蒙的……”你紧忙解释道,“他确实没开过拖拉机。”
“不说这个了,他的刑期都快完了,”管教说,“大概还有半年多吧,他就可以出去了,不管怎么说,离家在外的,他还是个孩子。”
“这包东西您留下检查一下,看着能给他的就给他点,都不能给您就收下。”你边说也将一大包从北京带回来的东西放在管教的桌上,“这么大老远的能碰上个老乡不容易,您也就别跟我提什么纪律不纪律的,反正这东西我是绝不拿回去了,不行您就都给扔了。”
会客室里,你和黄方隔着一道铁栏对视着,然后不约而同地冲到铁栏前,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你瘦多了。”
“你也瘦多了。”
会客时间规定在半小时以内。你不停地说着,黄圆的情况、连里的情况,你把外面的所有变化都告诉了他。黄方始终专注地听着,清瘦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
“太好了!”他说,“这么说,咱们的好日子快来了。”
“你一定要好好服刑,”你叮嘱黄方,“半年多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
“你放心吧,我这里挺好的。”黄方说,“这几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想了不少事,想得最多的就是出去后该怎么活……”他说这话时,脸上带着一种令你难以读懂的神情。
再次见到吴歌是在一个周末的傍晚,约会的地点是在过去你教她游泳的伏尔基河边。
乳白色的浓云遮盖了大半个云空,风呼啸着,卷动着厚厚的云层。你沿着长满了牵裳的羊草、牛蒡草和斑黑的野草麻的堤岸走来走去,心中忐忑地不时向远处张望着。忽然,你看见吴歌正低着头越过田野,踏着湿草,急匆匆地向你这里奔来。快到跟前时她才抬起头,一眼看到了你。“迪克!”她高声喊着,风一样扑进了你的怀里。
她浑身上下洋溢着的青春气息令人晕眩,她的头伏在你的肩膀上,发梢蹭在你的面颊上,嘴里不停地呢喃着,“想死你了……想死你了……”许久,她才稍稍平复下来。你拉着她坐在堤岸上,望着脚下湍急的河水,述说着各自一年多来的经历。
“我去师里打比赛了,今天才回来。”吴歌说,“你猜我拿了什么名次?”
“冠军,”你说,“送给别人了。”
“才不会呢,我就是得了冠军,你猜对了。”吴歌说,“我前几天就听我爸告诉了我你回来的消息,我就想得到冠军,把它献给我的老师,献给我日夜思念的人。”
“太棒了!”你高兴地恨不得照着她那红扑扑的脸蛋亲上一口。“你进步真快,在体育比赛中,冠军总是最好的。”
“比赛中我总在想着你,想着你的坚强,想着你说过的话。”吴歌认真地说,“真的,我现在懂得了一点什么是体育精神,就是永不认输。”
沉默的钟楼 50(2)
风住了,月亮早早地挂在云团掠过后湛兰色的天际边。吴歌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像是要把存在心里的话一古脑地全说出来。你边听边感到自己的思绪越飘越远,耳旁的话音也变得遥远起来,似神女轻柔的絮语,令人置身于一种幸福的宁静中。你想,和这样一颗水晶般纯洁透明、年青热情的心发生如此真挚的接触,并得到她的无比信任,任何人都会激动起来,都会产生一种甜蜜的怅惘和一种油然而生的责任。
“你在听我说吗?”吴歌问。
“我在听。”你边说边轻轻地拿开吴歌伸向你面颊的手。
“我爸爸说,他要被落实政策了。”吴歌又问,“什么叫落实政策,是好事吗?”
“当然是好事。”你说,“真要是落实了政策,你可能还会跟着你爸爸回北京呢。”你说这话时,心中立刻想起了你在农村的父母。他们是否也有被落实政策的一天?
“那太好了!”吴歌高兴地一下子蹦了起来。“我要是也能成为北京人,那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现在连里不少知青都在办什么病退、困退,我一直就担心你也会走,会看不到你了。”
“不会的,一时半会儿我可走不了,”你说,“办理那些手续是很麻烦的,需要很多关系和门路。再说,你还没有高中毕业,我这个当哥哥的怎么也不能撒手不管呀,等你上了大学,我才会放心。”
“我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吴歌骄傲地一扬头,“但是我有你这样一个好哥哥,一个无人能比的好哥哥,这是班上的同学们谁都没有的。”
看着吴歌那口无遮拦,清纯可爱的模样,你觉得她真是可爱极了。
沉默的钟楼 51(1)
你是在1975年夏天当上了排长的。在异常艰苦的劳动中,你以双倍以至几倍的付出赢得了连长的赏识和战友们的尊重。那时,你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目标,脑子里空空如也,你用不停顿的、苦行僧式的、近乎体罚的劳动来填充、麻痹着空虚的自己,你看不到前途,不知道今后会怎样?每天晚上,当你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爬上土炕,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睡眠里,像个动物一样,毫无思想地、日复一日地、机械地活着。
你不是没有思想,而是你不敢思想。面对危险,驼鸟将脑袋藏进沙堆里,而将对手们喜欢的它的身体留在外面任其吞剥。你也一样,面对自己无力改善的生存处境,你只好不去思想。那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几乎所有知青都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事件给自己的一生带来的是什么。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兵团长期实行的禁欲主义,露出了土崩瓦解的势头。另一方面,面对如此艰苦劳累的生活,知青们开始动用起了各种手段,泡病假、办假病历,私下里交换着对付各式检查和医疗设备的经验与心得,甚至自残,以达到能够办理病退回城的目的。有条件、有门路的知青家长们也纷纷开始活动起来,拉关系、走后门、力所能及地请客送礼,以达到将自己的子女办理困退回城的目的,一时间鱼找鱼路,虾找虾路,用各种贿赂手段消蚀着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给各自家庭和子女本人带来的磨难,开创着中国现代社会屡禁不绝、愈演愈烈、风靡全国的腐败先河。所有人都使出浑身解数,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由此而汇聚成的巨大能量,从根本上撼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文革式的、空前绝后的就业体制。
你无奈地远离着这一切,因为你的黑五类出身、因为你的家境,使你无法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在连里,知青们人心思动,人心思变,都想在活动和变化中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达到各自梦寐以求的回城梦想。而你却只能用劳动来逃避着。
所以,当连长问你是否愿意带些人去鹤岗市为团里拉煤的车辆装车时,你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
鹤岗市在当时与其说是一个市,倒不如叫鹤岗矿区更为贴切。在那里除了煤矿之外,少有其他企业,一切都是围绕着矿区生产生活设置的。你记得在当时的鹤岗给你留下很深印象的有两多,一是在没进城时看到的坟头多,几乎所有的山包都被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