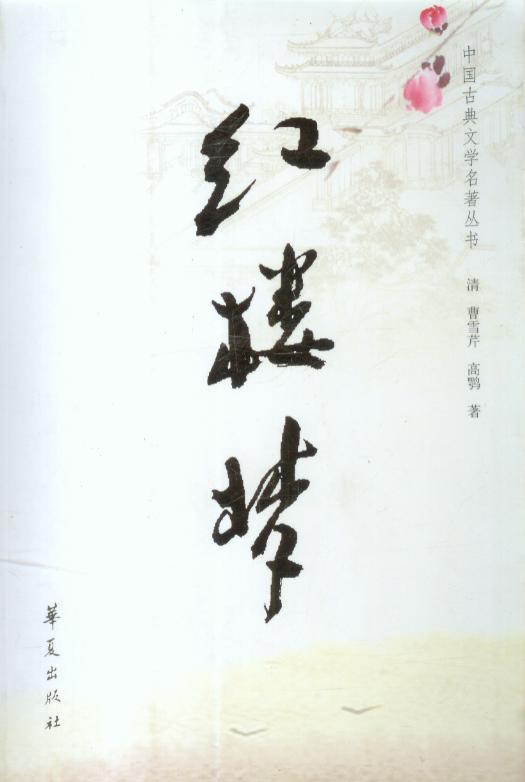沉默的钟楼-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置的。你记得在当时的鹤岗给你留下很深印象的有两多,一是在没进城时看到的坟头多,几乎所有的山包都被坟头占满了;二是进城后看到的小饭馆多,而且所有的饭馆都卖酒,像北京文革前星罗棋布在胡同口的小酒铺。
你们当时住在位于城市边缘的一个矿区内,矿井离生活区很近,矿工宿舍占据着很大的一片,基本上都是那种低矮破旧的、工棚式的房子。这个矿井是日本侵略东北时开采的,煤层丰厚,煤质优良。矿井很深,下面巷道纵横,最远的掌子面要乘电瓶车开出几十里地。
在你的带领下,你们一共十个人分为两个班次不分昼夜地为团里前来拉煤的车辆装车。尽管这活儿在外人看来又脏又累,但你们觉得比大田里的农活要轻省多了,毕竟这活儿还有个喘气的功夫。一来二去,你们同矿上的一些矿工们也开始熟悉起来,主要是些年青的矿工。趁着没有车来的时候,你曾数次下到矿井里,同那些矿工们一道干活。当时采煤的主要工具是风镐,端起几十斤重的风镐刺向坚硬的煤层,那种剧烈的震动会使你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颤抖不停,一天八个小时下来,生手会感到上井后自己身体的颤抖都停不下来,内裤都是湿的,因为尿液、甚至精液都会在你根本不知晓的情况下,从你那被震得除了麻酥而再没有其它感觉的身体里流出来。
矿工里和你最要好的是大白、二白和三白这哥儿仨,他们是亲哥儿们,都是在初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来到矿上干活儿的。三白告诉你,他死去的父亲是因为忌讳别人管他叫煤黑子,才给他们哥儿仨起了这名,小名大号全叫白。大白早已有了家,还有两个孩子;二白正在谈对像,光棍就是三白了,所以他同你们交往最多。三白告诉你,这鹤岗城里还有一多,就是寡妇多,造成的原因是矿区里几乎每个月都发生的工伤事故。在矿区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虽说不成文,但却被所有下井工作的矿工们遵守着,那就是每天下班上井后,必须先回家一趟,让你的亲人知道你活着上来了,才能够再去办别的事,任你喝得烂醉半夜回来都行,但绝不能让家里到了该上井时不见人影。
那时的鹤岗没有什么玩儿的,矿工们上井后最感惬意的便是喝酒,经常是上井后邀上几个哥儿们喝上一顿,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醒。不用养家糊口、兜里又有俩钱的,还可能去干另外一件事情,那就你是闻所未闻的嫖娼。你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曾在一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娼妓,但万万想不到在文革期间、在到处都是红色恐怖的高压之下,这里竟然会发生此等事情。然而,当你亲耳听到、亲眼见到了这些之后,你相信了这样的事实。
起初,你是在三白酒后听他讲起这种事的,你当时不信,他拍着胸脯说道,他马上出去,用不了十分钟就能给你找一个回来。你后来才知道,操这种行当的人都是暗娼,并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寡妇、矿工的妻子。在男人死了之后,家中断绝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在改嫁不成又得养家糊口的情况下,完全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同时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搭帮套”。这种情况是男人虽没有死,但因工伤致残,无法再继续下井挖煤,失去了劳动能力,虽说能从矿上领到一些工伤补助,但数目少得可怜,根本无法维持生计,这种人家里的媳妇如果被哪个光棍看上,自愿前来帮助,并成为家中的一员,就形成了“搭帮套”,也就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同时吃在一锅里,睡在一铺炕上。
沉默的钟楼 51(2)
时间长了,你了解到三白也有一个相好,是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二十四岁,比三白还小两岁。三白以自己的收入暗中接济着她家的日子,已经有一年多了。三白对你说,自打这个小娘们嫁到矿上的那天起,他就看上了她,所以在她丈夫在井下被砸死后没多久,他就爬上了她的炕头。他知道她是暗娼,除了他之外她还有别人,但他却从不去管她,因为他知道仅凭自己有限的接济,根本无法维持她那个家。有时,他还会买上些酒肉拿到她家去喝,喝完便睡在那里。一次,三白和你在一家饭馆里喝了一顿之后,走到街上时,他突然死拉硬拽地非要拖上你去她家再喝一会儿,你推脱不过只好随他去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时你的心里确实有着那么一种好奇,你想亲眼见识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俩在一片黑黝黝的低矮的棚房中七转八拐,走了好一会儿才来到三白相好的屋门前。屋门虚掩着,从里面透出一线昏黄的光亮。你们径直走进屋里,三白相好的正在灯下做活,见你们进来,她赶忙站起身,将你俩让坐到炕上。
“下午刚找来一拨活,我这儿正忙着呢。”三白相好的说着,用媚笑的眼神瞟了你一眼,“这位大兄弟像是没来过,白白净净的,不是本地人吧?”
“人家是北京知青,别又想勾搭人家。”三白说着,将手中的酒肉送了过去,“拿去热热,我们哥儿俩要在这儿喝会儿。”
你环视着屋内,见大炕上一头还睡着两个孩子,屋地上堆着一大摞矿工们的劳动服,整间屋里基本没有什么家具摆设,最乍眼的是放在窗根儿下面的那台缝纫机。
“那是我给她买的,”三白说,“这娘们儿聪明,愣是自个儿学会了踩缝纫机,以后你要是有啥缝缝补补的就拿过来。”
“是呀,有啥缝补洗的就都拿过来,千万别客气。”三白相好的走进屋里,放上炕桌将热好的酒肉摆了上来。
“这是给矿上干的活儿吧?”你问她。
“是呀,”她说,“给这些新劳动服上钉扣子,一件衣服钉七个扣子给五分钱。”
“那可太少了!”你说着又看了看那堆衣服,心中估算了一下,大概所有这些衣服都干完了,她的收入也不会超过十块钱。
“可不是太少了,央求人家半天也不再给涨一分。”她说,“就这活儿也还不好找呢。”
“往炕上一躺把腿一岔挣得多,”三白说道,“你上哪儿去找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傻子呀。”
“当着人家外人呢,你别这么胡咧咧。”她搡了三白一把,脸臊得通红。
那晚,三白并没有睡在她家,怕你不记道,他执意要将你送回去。路上,他对你说,“这娘们儿炕上的活儿不错,挺火爆的,你要是想了,可以上她这儿来放上一炮,给五块钱或是三斤全国粮票都行,那是帮她呢。”听了他的话,喝得醉醺醺的你顿时就醒了,目瞪口呆地望着三白,楞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这么看着我干嘛?”三白道,“我这是说真格的呢,你找她是帮她呢,你不知道她那日子过得有多难,要不是为了那俩孩子,她死的心都有。”
从那以后,你再没有去过她家,三白几次想拉你去她那里喝酒,你都回绝了。不知怎的,你一想起她来,心里便很不是滋味,甚至你想自己都害怕面对她那强颜欢笑的样子,害怕对视她那浪媚但又卑怯的眼神。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令你与她再次相遇了。
那火是在傍晚时分着起来的,当时你正在宿舍里睡觉。当你被屋外的喊声惊醒后跑出来一看,见矿工宿舍区一片浓烟滚滚,一些地方的火苗已经窜上了天空。当时你脑海里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三白相好的和她那两个孩子,你转身回屋抄起一把铁锹便冲了出去。
那个傍晚还刮着五、六级风,风助火势,使得大火在顷刻间就蔓延开来,肆虐的火苗舔到之处一片劈啪作响,火场中喊声一片,乱成一团。待你赶到三白相好的家门口时,见她家所在的那排棚屋已经变成了一条火龙,火光中人们绝望地叫喊着,碰撞着,抱着那点儿可怜的家当夺命而逃。正当你踹开房门要冲进屋里时,三白相好的抱着一个孩子跌跌撞撞地从里面冲了出来,一下子扑在了你的脚下。你赶忙扶起她,问道,“里面还有人吗?”
“大的还在里面……”她说,“我刚才没拽住她。”
你二话没说,脱下上衣包住头,冲进了屋里。屋里全是浓烟,什么也看不见,你只能顺着孩子的哭声向前摸索。这时,房顶上一根又一根带火的椽子扑扑楞楞地断落下来,你一边躲闪着,一边终于抓住了那个孩子的手,一下子将她抱住,搂在胸前,拼命地向外冲去。就在你冲出房门的那一刹,一根带火的椽子正向你的头顶砸下来,你下意识地抬起手臂挡住它,就势倒地滚出了屋子。你刚一出屋就听到随着一记沉重的闷响,房梁坠落到火堆里,紧跟着整个房顶哗啦啦地坍塌下来。在一片四溅的火星中,在一片熊熊火光的映照中,你依稀看到了三白相好的脸,随即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你是被浓烟呛昏的,你那挡住那根燃烧着的椽子的右臂也被烧伤,留下了永远的伤疤。但你救出了那个孩子。在医院里,三白和他的相好来看望你的时候,热泪盈眶,感激的话说个没完。
沉默的钟楼 51(3)
在你伤愈出院准备回连前,你独自找到了三白的相好。当你推开矿上临时为她安排的那间棚屋的房门时,她愣在了那里,显然她不知道你到底为何而来。
“嫂子,我来看看你。”你说着,没等她让便盘腿坐在地铺上,将手里拿着的一瓶酒放在那张由一块木板和几块砖头搭起来的小桌上。“我还想喝点儿。”
“那好哇,”她说,“我这就去给你把酒热上。”
“先不急,”你边说边掏出八块钱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递给了她。“这个你先拿着。”
这些是你当时能够拿出来的全部,那十斤全国通用粮票还是你在外流浪时期攒下的,一 直未舍得动用。
“这是干嘛,大兄弟,”她的眼圈红红的、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这些我不能要……我早说过,你什么时候想我了就来,什么也不用拿,拿了我也不要……你是我那孩子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嫂子,你错了,”你说,“我今儿没带菜来,你拿着这钱出去买些肉回来炖上一锅,我等着用它下酒呢,多买点儿,也让孩子们跟着一块吃。”
“这么说你今天晚上不走了?”她破涕为笑,脸上带着感激的神情,将身子软软地向你靠了过来。“这可太好了!你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香香地给你炖上一锅,我陪着你一块喝。”
她前脚刚出去,你后脚就走了,永远地离开了那个棚屋,永远地离开了鹤岗。那天晚上,你是坐在煤车上离开鹤岗的,一想到三白相好的因为你刚才的赠予,可以吃上一锅炖肉和几顿饱饭时,你的心里感到无比欣慰。你所能给予的只是这些了,你想,如果还有的话,你会给予她更多。一路上,你的眼前总是不断地闪现着三白相好的那出于心底的无限感激和渴望关爱的眼神。
那晚,当你们的煤车驶出鹤岗,再次经过郊外山岗上的那片坟地时,你和同伴们突然发现在路旁的坟莹之间,有一条美丽无比的狐狸。在车灯的照耀下,它呆愣在那里一动不动。那是一条浑身火红的狐狸,眉间有一块三角形的白毛,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浑身上下的皮毛被雪白的车灯照得熠熠发亮。
“停下别动,照着它。”车上的小于拍着车厢叫着,抄起步枪推上了枪栓,举起枪瞄准着。
“别打它。”你说着紧忙抬起小于的枪口。几乎是与此同时,枪响了,子弹射向了天空。那只呆愣着的狐狸听到了枪响,像是猛然惊醒过来,拖着长长的尾巴扑扑楞楞地消失在了草丛里。
从此以后,三白的相好总是与这只美丽无比的狐狸一起出现在你对鹤岗的记忆里,你搞不懂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是感到在忆起这事的时候,心中总是一阵释然。没有什么能够比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更好的事了,你这样对自己说。
沉默的钟楼 52(1)
黄方早就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他早就预料到并盼望着这一天。这一天早晨,当他下了火车走出站台,重又脚踏实地地站在北京路旁的树荫下时,他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
他不紧不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欣赏着记忆中熟悉而眼前又略觉陌生的街景,感到神清气爽、好不惬意。上班的人流开始出现在马路上,他们骑着自行车,一路说笑着,从他身旁擦过。他微笑着望着他们,嘟囔了一句,“妈的,北京真好!”
他脚步轻盈地走着,手中的提包也似乎轻了许多。提包里装着二十斤黄豆,这是他在北大荒用青春和血汗挣回来的全部。还挣回来了什么呢?他暗忖,似乎兜里还有十块钱,大概只够吃顿饭的,一想到饭他还真感到有些饿了。正在此时,一阵诱人的肉香随着晨风飘了过来,他抬头一看,这香味是从前面不远处的一家小饭馆里飘出来的,这使他回忆起,早些年这家小饭馆里的羊肉汤特别地道。这人要是精神一好,胃口马上就好,他想,回家先不急,先去喝碗久违了的羊肉汤。坐在饭馆里,他望着窗外的街景,听着车站钟楼那悠扬的报时钟声,感到他日思夜想的新生活已经从这一刻开始了。
为了迎接黄方,黄圆特地向学校请了假,一想到马上就会见到数年不见的弟弟,她的心里兴奋异常。几个月来,她一直在为黄方回京一事奔走,当然还有你,只是因为你要回京还牵扯到你父母的政策落实,所以办起来难度更大些。那是个令人振奋的秋季,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感受着新生活的来临,黄圆当然也不例外。她畅想着黄方和你都回到北京后,像从前一样在一起的日子,她对你依旧一往情深,在学校里遭遇到的来自各方的或直白或暖昧的追求,都被她回绝了,她在想念和等待中忙碌着,并用此来填充着她的生活。
“姐,”当黄方推开房门,站在她面前时,她简直不敢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英俊、潇洒的男人竟然就是从前瘦小枯干的弟弟。
“是你吗?黄方……”她叫着,一下子扑进了他的怀里,“你变了……长高了……变得我都不敢认了……”她呢喃着,仔细地端详着黄方,“你怎么好几年也不给我写一封信?”
“我去山里伐木了,那地方不通信。”黄方说,“我让迪克告诉过你呀。”
“他是说过,可我就是想你,”黄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