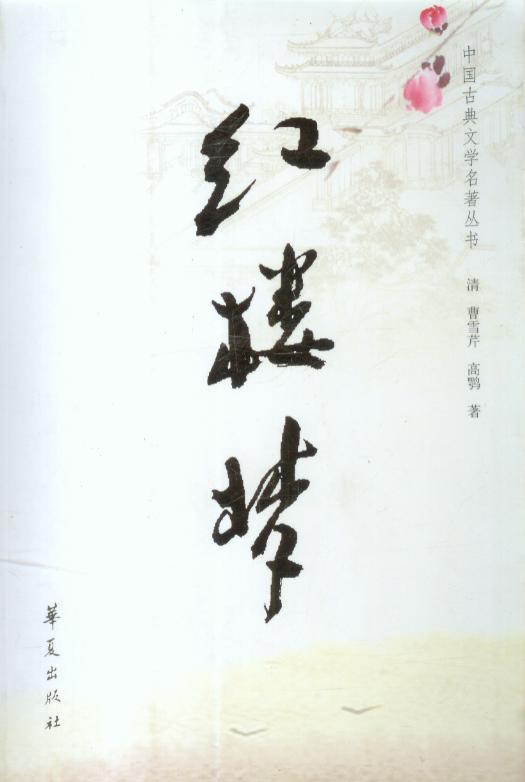沉默的钟楼-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里,显然是被眼前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蒙了。俄顷,他放下鸡食盆,又将手中的饭团扔到身旁的金鱼盆里,双手在衣服前襟上擦着,嘴里像是嗫嚅着什么,并谦恭地弯下腰,冲着红卫兵们做了个请进屋的姿势。
那个黑大头一挥手,十几个红卫兵跟着他进到了屋里,屋里随即响起了一阵乒乒乓乓砸东西的声音。正在午睡的黄圆和她妈妈随即被从屋里赶了出来,相拥着站在院子角落里。拴在枣树下的那只平时只知道睡觉、谁来都爱搭不理的大黄狗一改常态,疯狂地叫着,被一位红卫兵一垒球棒打下去击碎了脑袋,躺在地上一声不吭了。
不断有东西顺着被砸破的窗子从屋里扔出来,被褥、衣物、书籍……撒了一地。黄宗远直愣愣地站在院子中间,中午的太阳早已经将他晒得汗流浃背了,他不停地用袖子擦着头上的汗水。院子里的红卫兵们也在不停地走动着,将所有的犄角旮旯儿都翻了个遍。你注意到,红卫兵中只有一个人一直站在那里没动,他身材颀长,脸庞白净,长得挺帅气。看样子他是被黄圆的美丽吸引住了,他始终注视着站在那里浑身发抖的黄圆。
“怎么办呀?”黄方问你。
你无可奈何地回答,“能有什么办法。”
“不能就这么忍着,”黄方说,“叉子说了,如果红卫兵来我家就去找他,他有办法,他本来是说好今天要过来的。”
你们正说着,只见黑大头从屋里走出来,愤愤地将手中拿着的一个暖瓶摔了个粉碎,然后走到那个一直盯着黄圆的红卫兵面前嘀咕着什么。显然,黑大头(也包括院子里的红卫兵们)正在为没有抄到他们期望抄到的东西而气恼着,院子里堆着的全是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
“黄宗远,”黑大头问道:“你是不是资本家?”
黄宗远忙不迭地点头称是。
“那你剥削来的东西都藏哪儿去了。”
“吃了,我这人好吃。”黄宗远说,“我知道自己罪该万死。”他的话音末落,腿上便挨了重重的一棍,紧跟着十几条皮带一起向他抽去。黄宗远倒在地上抱着头,痛苦地翻滚着,不一会儿便被打得血肉模糊。
“起来,别他妈趴着装死。”黑大头分开众人,揪着黄宗远所剩无几的头发,一把将他拽了起来,斥道,“你就好吃是不是?今儿我让你吃个够!”“他边说边拿起一块砖头,将身旁的那个鱼盆砸碎,“吃,把这盆金鱼都给我吃喽,先捡最大的吃。”
鱼盆里的水四溢开来,几十条金鱼噼里啪啦地在地上翻滚着。
“快吃呀,”红卫兵们哄笑着,显然来了兴趣,“先吃这条,这条最大。”
黄宗远跪在地上,好不容易才将那条最大的金鱼抓在手里。他迟疑地将鱼送到嘴边,向上瞟了一眼,看到所有的人都正注视着他,他一口将金鱼吞进嘴里,使劲儿地嚼着。顿时,鲜血和泡沫顺着他的嘴角流了出来。
红卫兵们笑了。
正在这时,门外呼拉拉又闯进来一拨红卫兵,个个黄军装、红袖标,你看到,领头的竟是叉子。
“你们是哪学校的?”叉子问道。
“你们是哪学校的?”原先这拨红卫兵们齐声反问。
“这你他妈甭管,”叉子说,“告诉你,这片全归我们管。”
“谁定的?”
“我定的。”叉子指着黑大头说,“怎么他妈的就数你话多呀,找抽上外边儿去。”
“外边儿就外边儿,谁他妈怕谁呀!”两拨人相互叫骂着,推搡着,拥出了院子。
胡同里跟随着叉子来这里的人显然要比红卫兵们多,他们一个个手持皮带和棍棒,个个摆出一副大干一场的样子。混战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挨了几下打的第一拨红卫兵也没有还手,而是在那个长得帅气的红卫兵带领下,爬上卡车,匆匆忙忙地逃走了。
院子里,黄宗远在一片血泊和泥水中呆坐了好半天才吃力地站起来,他拍了拍黄方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黄方家那天的晚饭丰盛无比,鸡鸭鱼肉摆满了一桌子,能够买到的水果也都买来了,还有酒。黄宗远特意把你和叉子都请了来,对你俩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尝尝吧,都是我做的,我年轻时真正用心学过几手呢,今天都给你们露出来了。”他边吃边喝,兴致特好,像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不停地向黄圆传授着这些菜的做法,直到她表示已经全都听懂并记住了才肯罢休。下午嚼金鱼时被鱼刺扎破的牙床,疼得他不时皱起眉头,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食欲。
沉默的钟楼 6(2)
晚饭持续的时间很长,那是你一生中第一次喝酒,在座的所有人都喝了酒。临结束时,黄宗远对叉子说,“你是好心办了坏事呀,今天下午那事本来应该是一个涉险过关的结局,这事我想过很多次了,我知道他们早晚得来,我躲不过去,但他们从这家里什么也找不到,他们拿我没辙,大风大浪我见多了……让吃金鱼我就吃,吃完了他们也就没什么可闹的了,大不了再挨一顿打,我是九条命的猫,且打不死呢……但现在不行了,他们一旦知道了你不是真正的红卫兵,这事就大了……”
第二天早晨,在你还没有醒来时,黄方便来到了你的床前,他的两眼红红的,将手中的一张字条塞给你看。那上面写着:
黄方,家中的三万元存款单就放在你的枕头套里。记住,现在先不要去取,以后再说。面缸里有五根金条(暂时放在那里最保险),不要急于出手,现在不是卖金子的时候。永远照顾好你的妈妈和姐姐。你姐姐手里有几百块钱,先花着。
如果你长大后什么都做不了的话,可以试着去做些生意。记住,就是你妈妈的钱,也别忘了赚。
告诉黄圆,不要嫁给生意人。
不要再养金鱼了。
我先走了,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大概是青年湖吧,我在那儿参加过街道组织的义务劳动,哪儿深哪儿浅我都知道。我已经活够了。那地方不错,那是我自掘的坟墓、水制的棺材……
你俩赶到青年湖的时候,黄宗远的尸体已经被捞起来了,放在水闸的旁边。他躺在那里,脸上带着泥污,一群苍绳围绕着他,他穿的那身黄绸裤褂紧贴在身上,污秽不堪。你紧紧地拽住几次要冲上去的黄方,站在围观在那里的人群后面,看着公园里的环卫工人将黄宗远用一领破草席裹着,装在一辆三轮车上拉走了。
黄方的妈妈是在黄宗远死后一个星期死的。那天,赶在黄圆和黄方都不在家的时候,她躺在床上,用刮脸刀片割腕自杀了。她也留下了一份遗书,上面写着:
孩子们,你爸爸先走了,我也想好了,待会儿就走。现在,刮脸刀片就放在桌子上,我谁都不怕了,别提红卫兵,就是天兵天将来我也不怕了,我这一生都在担惊受怕,现在好了。
你爸爸他特自私,一辈子都是这样。他怕事情败露,红卫兵们再来时将他打死就先走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就把这份罪过扔给了我。我也不想受这份罪,这辈子我受的罪够多了。孩子们,暂时别回家了,藏好你爸爸给你们的东西,先到上海你姨妈家躲一躲吧。但愿你们的一生能够安定幸福,别像我们,自打懂事起就是让人家革命的。他们不累我累了,我不想再活着让人家革命了。你们俩相互帮助,各自保重吧。
妈妈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
你所以能将这两份遗书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它给你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像是用利刃镌刻在了你的脑海里,胜过你在学校里学到的所有诗文。
渐渐的,你似乎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惊恐万分,整日里惴惴不安的状态中走了出来,面对这么多重大的刺激,像是已经麻木了。在你的认识里,革命就是革命对象的泪水、流血和死亡,令你心痛或不那么心痛的泪水,你所熟悉和不熟悉的流血和死亡。
黄圆随同叉子一起到外地串连去了,你索性搬到了黄方家里。那段日子每天夜里你们依旧去捡破烂儿,小山似的大字报被你们每天准时地转移到废品收购站里。你把挣来的钱交给母亲,有时还给仍在“牛棚”的父亲买上一袋香肠找机会送进去。白天里你们无所事事,就和叉子的一帮哥们儿在街上闲荡。
叉子的这帮哥们儿大多是劳动人民的孩子,年龄大约都在十六、七岁,只有一位大学生显得有点儿鹤立鸡群。听说他是叉子的街坊,原先经常请他补课,所以叉子很敬重他。他混到这个圈子里来,是因为他家被抄,父母都被轰回乡下,他不愿意回去,而学校里又早就没有了他呆的地方,所以他就这样有一顿没一顿,东住一天西住一天地和你们混在一起。大家都很敬重他,都管他叫王老师。每到晚上,大家都会聚到一起听他讲故事。他的故事又多又新鲜,像是总也讲不完,什么科幻的、历史的、闹鬼的、二战的、皖南事变是怎么回事、抗美援朝时为什么毛主席称38军为万岁军……他还讲到了当时广为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说它是中国封建主义的现实翻版,本质上是反动的,理论上是荒谬的,所以得到了一些人的狂热迎合,是因为人们思想中的流氓痞子性和农民意识在作怪,是一种翻身算账,私仇公报的阴暗心理,是与人斗其乐无穷这种可怕的精神传染病的典型反映。他的这些话听得你们当时直哆嗦,又害怕又隐约觉得他说得对。他的很多话你当时并不懂,感到玄之又玄,像是天方夜谭,但你们还是爱听。现在回想起来,他就是当时你们这一群人中的精神领袖,他随时随地用他的言行在影响着你们,你们的精神依赖和寄托在他那里,他给你的干涸、混乱而又迷惘的脑海里,注入了许多与众不同的东西。他抽烟很多。有好几次你和黄方深夜捡完破烂儿回来,又找到他们的临时住处,想继续听他讲故事时,发现别的人都睡了,黑暗中只有他一个人手中的烟头还在忽明忽灭。他瞪大着眼睛望着远处,总仿佛是在思考着什么。
沉默的钟楼 6(3)
终于有一天,王老师失踪了。几天后,传来了他在北京站卧轨自杀的消息。这件事给北京带来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一时间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北京站也因此而军警密布,戒严三天。当时的铁路运输本来就因各地红卫兵蜂拥来京大串联而变得混乱不堪,这次终于彻底瘫痪了。据说,北京站直到事发后第二天的夜里才有一列客车发出。
在那段血腥的岁月里,一位流浪街头的大学生义无反顾地跳下站台,用生命中最后的本钱——年轻的血肉之躯卧在铁轨上,令疯狂前行的血腥列车遇上了一点儿麻烦,令策划于密室的阴谋和横行于阳光下的残暴,起码在北京停顿了一天。
沉默的钟楼 7(1)
1967年北京的冬天干冽而又寒冷,由文化大革命开始掀起的第一波革命热潮也似乎随着寒冷的天气,而在老百姓的眼里变得有所降温。表面看来,旧的革命对象已经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新的革命对象正处在培育和寻找当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一步将砸向哪些人,似乎暂时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和可以成为习惯的指向。很久以后你才知道,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过后,政治斗争才算真正开始和凸现出来,党内斗争、派系斗争、权力斗争等吸引了大部分较高层人们的注意力。原先那些老红卫兵们的父母们、相当多的高级干部们,似乎正在开始变为革命的对象,那些红卫兵们当然不能对自己的父母大打出手,当然不能对他们父母的革命事迹和享受的优越待遇加以批判和破坏。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成了保皇派,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沉沦下来,有的甚至转而开始偷尝爱情禁果。红卫兵们开始分化了,造反派们开始分化了,利益和家境的变化是引起他们分化的重要原因。这一部分人的父母或家人昨天还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转眼便身陷囹圄,生死难卜,家被抄得比谁都干净,甚至连一片纸屑都不放过。过惯了贵族式生活的他们被轰出了深宅大院,毫无生活保障地流落街头,成为了社会所唾弃的狗崽子。尽管在他们心里坚持认为自己的狗崽子称号与黑五类子女的狗崽子称号有着截然不同和本质上的区别,但现实中境遇上的相同,则使他们无暇也没有资格再对原有意义上的革命对象口株笔伐,大开杀戒了。老百姓们正是由于这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先头兵和最早行动起来的群众基础的涣散,才得以些许喘息的。
黄圆和叉子一行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北京的。那时已经临近春节了。他们这一趟走了三个多月,据说是到过不少地方,逛了不少风景名胜,吃了不少各地的美食,听说了不少风土人情,捎带着也打了不少架,几乎是全胜。最巧的是他们居然在昆明碰上了来黄圆家抄家的那拨红卫兵。是叉子最早发现他们的。跟踪了一天之后,叉子纠集当地的红卫兵,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他们一顿。这一架的好处是当时出了气,坏处是令对方从此结下了仇,而且双方都知道了对方的底细,甚至连名字和学校都被对方了解得一清二楚。叉子估计回到北京后,那拨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对叉子说,人也死了,家也抄了,再这样做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对黄圆和黄方没有好处。但叉子不这样认为,他说他可以保护他们。他说他跟红卫兵是死对头。他说他出身贫农,本来是可以参加红卫兵的,但学校里的红卫兵不许他参加,还说他是流氓,并被他们抓起来遭受过毒打。他说自己不是流氓,从没有做过流氓做的事,他只是打架,跟那帮欺负他、瞧不起他的高干子弟们打架。他的打架与好斗,是被那帮人欺负了好几年后逼出来的。他结交了一帮学校里的穷哥们儿,他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互相保护,不再被人欺负。叉子他们回京前给你发了电报,你和黄方去北京站接他们。刚一见面,你便把王老师卧轨自杀的消息告诉了叉子,他听后神情愣愣的,半晌没有说话。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他停住了脚步,仰望着巨大的时钟,嘴中喃喃着,“在外地就听说这件事了,但没有想到会是他!到底是在哪儿?”“不知道,”你说,“只听说他是从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