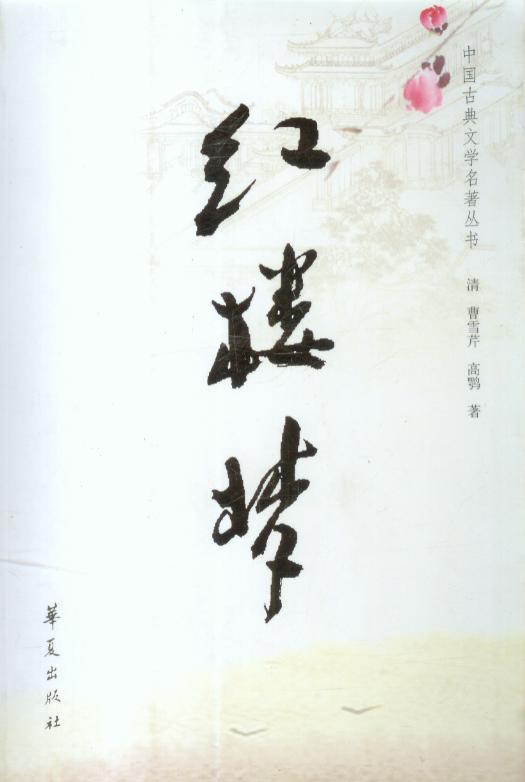沉默的钟楼-第5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别,您别这样想啊!”黄圆急了,“您要是不走,我也不走了,就在这儿陪着您。”
“傻丫头,你们都是有工作的人,在这儿呆着算什么。”老人说,“想来想去我还是不能跟你们走,我一个孤老婆子又不沾亲带故的怎么能去麻烦你们。”
“不麻烦,真的不麻烦。”黄圆说,“我会像对待亲妈一样待您的。再说,让您孤苦伶仃地一个人呆在这里,这事我一想起来心里就难受……能够伺侯您我的心里会好受些……”
“大妈,我们和叉子、和您的儿子就像亲兄弟一样,这您是知道的。”你说,“和我们走吧,您看黄圆哭的……再说,您可以去试一试嘛,如果您觉得不舒服我们再送您回来……”
沉默的钟楼 71(2)
老人无奈地叹息着。
“把这个也带上,”黄圆爬上炕头,取过那两个骨灰盒递给老人,“我知道您离不开他们。”
“好闺女!”老人说着一把抓住黄圆的手,一直噙在眼里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黄方是在翠翠母子来到北京的三天后才回到家中看望她们的。
“我到外地去了,没想到我姐她那么快就把你们接来了。”黄方边说边欣喜地看到,翠翠依旧是那么漂亮,黄圆的衣服穿在她身上显得挺合身。见黄方突然回来,正在收拾房间的翠翠显得有些慌乱起来,她忙着给他倒茶,手不停地颤抖着,脸上一片绯红。
见屋里没人,他一把攥住她的手,盯着她,低声问,“想我了吗?”
她“嗯”了一声。
“那就来吧。”他说着,一下将她抱了起来,向里屋走去。
……
黄方气喘吁吁地从翠翠身上滑下来,惬意地仰面躺在床上,说,“去,给我点支烟。”
她顺从地坐起来,翻身下床,赤裸着站在那里将烟点着,然后转过来俯下身将点着的烟放在他的嘴里,重又依偎在他的身边躺下来。他看到她依然还是那样丰满、白皙,窈窕的腰肢依然是那样动人,就连脸上的神情都与当年毫无二样。
“孩子呢?”他问。
“上学去了,”她说,“你姐姐在我们来之前就给他联系好了学校。”
“大傻呢,他怎么样?”
“他走了……”
“走哪儿去了?”
“没人知道,他把我们娘儿俩送下山后,又和你姐姐见了一面就走了……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那你们这婚算是怎么回事,离了?”
“我们俩就没结过,从来就没有起过结婚证……当年他在村里摆了一顿喜酒,就把我给带出来了……”
“噢……孩子叫什么名字?”
“我让孩子随了我的姓,叫刘山。”
“大傻他同意?”
“他同意。”
“大傻这个人其实不错……”黄方说,“刘山……我看还是别留在山里了,就让孩子留在北京吧,你呢,你打算怎么办?”
“我听你的。”她说,“你要是让我走,我就回山东老家去,可孩子我想让他留在你这儿,让他在北京上学。”
“这没问题,”黄方翻身坐了起来,“差点忘了,外头还有人等着我呢,我得赶紧走,你把刘山学校的地址给我,抽空我去看看他。我姐呢?”
“她和迪克一块去接叉子的母亲了。”翠翠说着,起身穿着衣服。“这就要走?我还有好多话要对你说呢。”
“那你也别走了,躺着别动,咱们有功夫说,”他说,“眼下这家里又是孩子又是老人的,我姐她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正好帮她一下。”
黄方坐进车里时,司机小王告诉他,刚才公司来电话说,原定在五点的谈判因对方总经理出交通事故临时取消了。
“那就去看看我儿子。”
“我见过您儿子,他和他妈到北京那天是我去接的。”小王说,“您儿子挺老实的,好像不太爱说话,当时您不在北京,是您姐姐……”
“他有多高了?”
“个儿可不小,随您,长的也挺像您的。”
他们到了刘山所在的学校。黄方让小王将车子停在胡同口,然后下车走到离学校门口不远处一棵大树下等候着。身旁那两个高大魁梧的保镖为他点上了烟。
下课的铃声响了,不一会儿学生们三五成群、嬉笑打闹着涌出学校大门。大拨的学生散去后,他们看到刘山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了出来,他低着头,沿着墙根踽踽独行。
“黄总,就是他,”小王指着刘山说,“那就是您儿子。”
“他还没有朋友,”黄方说,“不像我小时候,总有朋友在身边,总有一个铁哥们儿给我矗着。”
他们说着刚要迎过去,突然看到从路边的厕所里窜出来四个流里流气的学生,将刘山堵在了那里。
“乡巴佬,东西带来没有?”其中一个个子最高的问刘山,“今天你可拖不过去了。”
刘山神色惊慌地抬起头,双手紧抱着书包后退两步撞倒了墙上,“你要什么东西?”
“你丫的装什么傻呀,”另一个脸上长满了粉刺的家伙上前推了刘山一把,喝道,“钱,钱呢?你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可没忘,急等着花呢。”
“嘿,小东西们,还反了他们了。”小王说着就要冲过去。
“慢着,”黄方一把拽住了他。“先别急。”
刘山掏出了两张十元的钞票递过去。
“就这么点儿!”一脸粉刺的家伙将钱夺过去,拿在手里甩着,“这够干什么的,不是告诉你丫的多拿点儿来嘛。”
刘山哆哆嗦嗦的将衣兜翻了过来,说,“就这么多,我真的没有了,不信你们看。”
“明天别忘了带来,多拿点儿。”又一个上前帮腔道,“烟呢?你叔叔不是大款嘛,找丫要,不给就偷丫的,他那儿肯定尽是好烟。”
刘山又从书包里拿出一盒烟递给了他们。
四个家伙点着了烟抽着,一个夺过刘山的书包翻看着,另一个开始翻他的衣兜。“你还别说,乡巴佬这身衣服可真不错,还是他妈地道的外国名牌呢,你们看看,谁认识。”
沉默的钟楼 71(3)
“扒下来,让哥儿几个先穿几天。”几个人哄着,在刘山身上动起手来。
“等一下,小同学……”黄方喊了一声,面带微笑地走了过去。“这事看来得跟我商量商量,我是刘山的叔叔。”他边说边拿开搁在刘山身上的那只手。“这身衣服是专门为他买的,你们穿上它恐怕不合身。”
刘山怔怔地望着黄方,似乎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几个小混账,一下子都呆愣在那里。黄方身后那两个保镖话也不说,一手一个揪着他们的脖领子将他们推靠在墙角上。
黄方从一个家伙手里拿过刚才刘山给他们的那盒烟,又分别将还叼在他们嘴里的烟拿下来扔在地上,用脚踩灭。“我似乎记得,中学生守则上有这样的要求,中学生不许抽烟喝酒。”他说,“尽管我在同你们差不多大小的时候也开始抽上了烟,但那是我自己买的,是用我当兵团战士挣的钱买的。那会儿我们只能抽握手牌的,九分钱一盒,舍不得啊,每一分钱都是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但从不抢别人的烟抽。你们可要记住,抢别人的东西是能惹祸的毛病。”他瞟了一眼手中的烟盒,俯下身,态度温和地说,“再说,这个牌子的烟你们抽着也不合适,有一种牌子叫大嘴巴,你们看是你们抽啊还是我抽?”
几个家伙被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哆嗦,整话都说不出来。“叔叔……您饶了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我们这是头一回,”其中一个小白脸颤抖地说:“我……我们错了。”
“知道错了就好,”黄方说着转向那个一脸粉刺的家伙,“我刚才好像还看见你拿了别人的钱,拿出来吧,钱在有些时候不是好东西,尤其是别人的钱。”
那家伙赶紧将钱拿出来递给了黄方。
“这样才好。”黄方将钱接过来,转手又塞进刘山的兜里。“在你们可以走开之前,我还想问一句,你们觉得今天这事是不是就算完了?”
“黄总,跟这几个小东西废什么话!”小王说,“抽他们丫一顿得了,让他们也长长记性,这他妈叫什么孩子呀,整个儿是几个小废物。”
“别这样。”黄方拦住小王,双臂抱在胸前,依旧面带笑容地说,“说话呀,我等着呢。”
那几个家伙都低着头,不约而同地用鞋子使劲儿蹭着地。
“好了,我也不难为你们了,独生子女大概都是这个毛病。”黄方说,“这事算不算完的主动权留给你们,以后要是真缺钱花了,可以直接来找我。还有,你们可以放心,今天这事我不会告诉你们的学校。我们该走了,有顺道的吗,可以搭我的车走。”
两个保镖是最后坐进车里的。临上车前,他俩还是一拳一个把那几个家伙打倒在了地上。
车子拐出胡同,驶上了二环路。黄方靠在后排,刘山坐在他身旁。他看着自己的儿子,想不到竟会在这样一个场合中与他相见。他瞥了一眼刘山放在膝盖上的手,已经全然不是自己梦境中那双肉乎乎的小胖手了。在他刚会说话的时候就会叫爸爸,可现在却叫自己叔叔了。他感到了刘山的拘谨和不适,他想,也许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小汽车。这就是自己的儿子,他将目光移向窗外,从他一出生自己就没有管过一天的儿子。他觉得心口有点堵得慌,眼眶有点儿酸。
“那钱是你妈妈给你的?”他问。
刘山“嗯”了一声。
“烟呢?”
“我给他们买的。”
“有几次了,这样的事?”
“两次。”
“同学们都叫你乡巴佬吗?”
没有回答。
“学校怎么样?”
“挺好的。”
“学习呢,还跟得上吗?”
“有点跟不上……”刘山怯懦地说,“尤其是理科,什么三角函数、平面几何、还有圆……我一点都听不懂。”
“慢慢就好了,你刚来恐怕还不适应……你们那里也许没讲这么深的功课。”黄方说着,脑海里又一次浮现出那皑皑白雪覆盖下的原始森林、那点着油灯的小木屋……他的眼眶湿润起来。他爱怜地望着刘山,深情地拍了拍他,什么也没有再说。临下车时,他嘱咐小王,“今天这事别对刘山他妈妈说,对谁也别说。”
沉默的钟楼 72
你又一次脚踏实地地站在了北大荒的土地上,又看到了这里的蓝天、白云、山脉、河流、森林和一望无际的沃野。你是顺道来这里的,换句话说,是因为公司的债务你不得不来这里。此前,你的不断壮大的建筑公司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这里不远的地方,承建着一座现代化粮库的主体工程。你那时虽说也在密切关注着工程的质量和进展情况,但因为忙所以总也没能抽身过来,这次你终于来了。
公司红火的日子里,你们在不长的时间里承接了从南到北六项工程,而今都要因为还债而半途下马了。
“有些工程还真不好谈,”高成龙对你说,“毕竟我们已经先期投入了不少,而别的建筑公司却乘机敲诈,接手条件苛刻得让人无法接受,他们都看出了我们急于兑现的意思。”
“那也没有办法,咱们只能让利呗。”你说,“建筑业就这么小个圈子,什么事你也瞒不住。”
你们分头去做了,你选中了地处北大荒的这个工程。你干脆麻利地处理完了工程事务,急匆匆地赶到了这里。
你又一次呼吸到了北大荒沁人肺腑的空气,看到了那里繁星点点的夜空。当你下了火车,跨过铁路,走在团部那条笔直宽阔的大道上时,心里竟然不知为何“怦、怦”直跳。原来心目中庄严肃穆的团部营区变了,变得不伦不类,像一个毫无文化背景的小县城。
还好的是,当你走下汽车站在连队路口时,一种熟悉的气味和感觉扑面而来。当年在路旁种下的树已经长大,变得浓荫蔽日,主干道的路面上铺着沥青,最先看到的马厩已经破旧得几近塌垮,里面孤零零地站着一匹似睡非睡、老态龙钟的马。营区的变化不大,家属区倒是扩展了许多,出现了不少装饰俗气的小楼。时值中午,四下里静悄悄的。你看到了记忆中的营房、晒场、关押你的连部,还有你们当年亲手盖起来的、至今看上去仍旧高大敞亮的食堂。你沿着时而清晰、时而为浓雾所笼罩的记忆,寻觅着过去。你的心情开始平静下来,全然没有了刚到团部时的激动。脑海中的记忆像是自己的,又像是别人的,你无法说清自己到底为何而来,那或熟悉或陌生的景物,似乎给了你一种思绪上的梳理。
你找到当年住过的宿舍跟前,向里面张望,屋里变成了库房,堆满各式各样的农机配件。你来到宿舍的后面,坐在一块石头上眺望着远处的北山,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你在这里干嘛?”一个稚嫩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身旁。
你回过头,见一个小女孩站在哪里。
“我,”你冲那小女孩笑了笑,顺口说道,“我是路过这里,在这儿歇会儿。”
“你要找人吗?”
“不,我不找人。”
“那你来干什么?”
“是啊,我来干什么呢?”你犹豫着站起身,又一次地望了眼营区,自言自语道,“也许我该走了。”
沿着那条多少次出现在梦境中的田间小路,那条与袁萍擦肩而过、人生第一次见到了那种被青春情愫燃烧的火辣辣的目光的田间小路,漫无目的地走着。你想,刚才自己是对的,你来到这里并不是要找谁,也不是要找什么,失去的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你来这里也许就是要重新站在这片你曾经历练八年的土地上,审视一下今天的自己。
站在伏尔基河的岸边,你想起了当年自己在寒风刺骨的初冬时节,光着身子跳进结满冰凌的河套里打捞苎麻的情景。那些在秋天时沤进河里的苎麻已变得粘滑湿臭,每捆都要上百斤重。当打捞完时,你是被人从河里拽上来的,连冻带累,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望着公路上来来往往运送木材的卡车,你想起当年在小兴安岭伐木时,因为累得筋疲力尽而甘冒被摔死的危险执意坐在车上下山,无论司机怎样劝阻你都不听。结果,车子真的翻在了下山路上的一个急拐弯处,你被甩出去十几米远,重重的摔在了雪地上,当时你侧眼一看,就在离你不足一尺的地方,立着一根斜尖的、白生生的树桩。刚才,你还看到了当年你们建的酒坊和粉坊。如今那里的规模已经扩大了许多,变成了高大的厂房,生产着品牌白酒和出口到韩国的粉丝。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