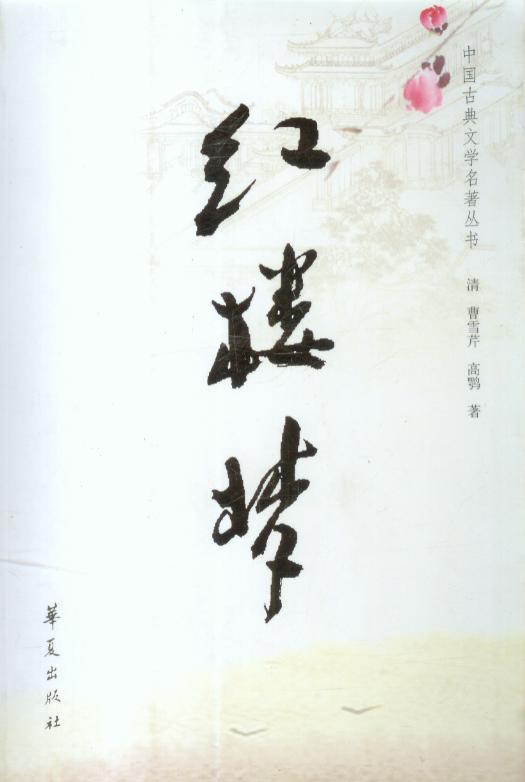沉默的钟楼-第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先别动粗,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嘛。”黄方制止着小王,“我跟刘总还有几笔账要算清楚。多少年前,在你还是红卫兵头儿的时候,你假借抓流氓为名,先是将一个无辜的女孩子强奸,而后又为了长期霸占她而欺骗她的感情,这算是一笔吧;同样,你又以打流氓为名,将一个不满17岁的少年扎死在德胜门桥头,这也算是一笔吧;再有,你利用自身官商的优势,欺行霸市,手段卑劣地将迪克的托运公司搞垮,这又得算是一笔吧;再说眼前,还是为了报复迪克,你将他的未婚妻勾引到手不算,还让她吸毒,把一个纯洁的女孩毁成了今天这样,这还得算是一笔吧。你丫自己数数,多少笔了,这账该怎么算?”
“你想怎么算?”
“那得看你怎么表现了。”
“我可以赔你钱,50万怎么样?”刘震亚说,“100万!”
“还有呢?”
“我可以让我妹妹嫁给你,我知道你一直在追她,回去后我就跟她说。”
“没啦?”
“你还想怎么样?”
“我想让你脱了,光着屁股给我跳一舞。”黄方说,“小王,帮丫脱!”
小王应着走到刘震亚跟前,挥舞着匕首“嚓、嚓”几下,将刘震亚的衣服撕落到地下。“方哥,让丫跳一‘北风吹’吧,那红头绳要是飘起来多好看呀!”
“先帮他脱干净了。”黄方说,“你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最喜欢跳的是忠字舞?今儿我就成全他,让他赤身裸体地重新回味一下他们这些人最留恋的、那个火热而又王八蛋的、在中国一去不复返的昨天。”
沉默的钟楼 75(3)
刘震亚仇恨地看着黄方,站立不动。黄方从小王手里拿过匕首,“怎么?不用我来动粗的吧?来,演出开始吧。对,挺胸昂头,精神要饱满,动作要舒展、到位,把对黑五类、黑帮的刻骨仇恨表现出来,预备……起。”黄方手上打着拍子,有板有眼地唱了起来: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黄方,你真恶心!”吴歌说着,站起身就要走。
“嘿,我怎么给忘了,还有专业的在这儿呢。”黄方一把拽住了吴歌,“这节目虽说女士不宜,但你还是不能走,转过身去等会儿吧,等节目演完了咱们一块走。”
就在黄方与吴歌撕扯着将她摁坐在沙发上的当儿,刘震亚一个鱼跃扑过去,从他放在沙发上的包里抽出来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并就势将吴歌揽进怀里,刀尖直抵她的喉咙。
“黄方,你别逼人太甚!”刘震亚说,“你们俩现在就给我滚蛋,马上就滚!不然的话,我就杀了她。”
“嗬,还有这么一手呐,行,将门虎子。”黄方说,“吴歌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你喜欢的刘总,到了裉节上敢拿你的生命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马上滚蛋!”刘震亚喝道。
“小王,去打电话叫警察吧,这事咱们摆不平了。”
“那我就先杀了她。”
“黄方,我求求你,”吴歌道,“千万别叫警察来。”
“刘总你真行,临危不乱呐。”黄方对小王说,“看来是没辙了,还是能力问题啊,多少次了,我总是好事办不好,咱们只能撤了。”
好一会儿刘震亚和吴歌才从歌厅里面走出来。他一手揽着吴歌,一手拿着匕首,站在门口神色紧张地四处环视着。街面黑黢黢的,诺大的楼群里只有几扇窗口还亮着灯,四下里杳无声迹。他从歌厅高高的台阶上走下来,将吴歌顶在前面慢慢地踱到他的车前,先警惕地围着车子察看了一圈,然后才打开车门坐进了车里。他长出了一口气,但又总觉得似乎哪儿有点异常。就在他下意识地朝后面望去时,一把匕首抵住了他的脖颈,小王从车内后排的座位下面露出身来。
“吓一跳吧,刘总,”小王说,“开车门对于我们修车的来说是基本功。”
车窗外,黄方从一棵大树后面闪身出来走到车前。他敲着车窗玻璃,对刘震亚说,“把门打开,先把你那把刀子递过来。”
刘震亚顺从地将手中的匕首递了出去。
“半天了,这玩意儿我就看着眼熟,”黄方接过匕首欣赏着,说道,“可惜当年叉子没用它把你扎死,多少年了,这回总算是物归原主了。小王,你和吴歌先回咱们车上去,我和刘总还有话要说。”
看着他们俩人走开后,黄方对刘震亚喝道,“下来!”
刘震亚趴在方向盘上半天没有动弹,就在黄方上前揪他下车的时候,刘震亚猛地从方向盘旁边的储物箱里抽出一支手枪,枪口直对着黄方。他侧身下车,两人近在咫尺地站在车前,枪口和匕首都抵在了对方身上,谁都不后退一步。
“你不是想算账吗?”
“没错。”
“想怎么算?”
“还是那句话,看你表现得怎么样。”
“现在不是刚才,主动权在我手里。”
“我不这么看。”
“跟你明说吧,”刘震亚用枪口顶了黄方一下,“我不会让一个侮辱过我的人活过今天晚上,尤其是像你这样的狗崽子!”
“你再说一遍,多少年了,这话我听着都耳生了。”
“像你这样的狗崽子……”
刘震亚话音未落,只听得黄方“嘿”的一声弓起身子,将手中的匕首深深地刺进了刘震亚的身体里。与此同时,刘震亚手中的枪响了。两个人都怒视着对方,但却说不出话来,彼此都试图站在那里,但却都像被重物猛击了一下似的,完全失去了平衡,重重地向身后摔去。
沉默的钟楼 76
你是在黄方死去的当天深夜接到黄圆电话的,第二天你便赶回了北京。
“子弹洞穿了他的胸膛,”黄圆说,“黄方扎破了刘震亚的肝脏,用的就是当年你送给叉子的那把匕首。”
“他也死了?”你问。
“没有,听说还在医院抢救。还有吴歌……她在看守所里关了几天后,被直接送进了戒毒所。”
听到刘震亚的死讯后,你和黄圆很快赶到了医院。死讯是刘冉通知给黄圆的。
医院太平间前的走廊里空荡荡的,长椅上只坐着刘冉一个人。
“他刚被送进去,你们要看吗?”刘冉低着头说。
你们沉默。
“我失去了两个亲人!”刘冉抬起头,泪眼迷蒙地哽咽着,“我看得出来,黄方是真心对我好,他是爱我的……本来我们甚至可以……都是仇恨,昨天的仇恨!”她说着突然站起身来,一把揪住了你的衣领,“你回答我,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是谁、是什么让你们这样彼此仇恨?回答我!”
“昨天,”你像是在自言自语,“你说的对,是昨天的仇恨。”
黄圆走上前,轻轻抚摸着刘冉的头发,说道,“回家吧,我们送你。”
“是呀,我们正好顺路。”你在一旁道。
你开着车子,沿着熟悉的道路来到了你们熟悉的那座深宅大院门前。“到了。”你说着,却不见刘冉有下去的意思。
“我已经不能住在这里了……这里已经有了新主人。”刘冉说。
“那你干嘛还……”
“我就是想再看一眼,”她说着下了车,“毕竟我在这里住了那么多年……”
你和黄圆随着刘冉穿过油饰一新的大门来到院子里,看上去这里的修缮工程已近尾声,两名工人正在拆除垂花门旁的脚手架。黄圆四处环视着,树木、花草、门窗、地面,甚至回廊顶上的彩画和各个房间雪白的窗帘都与她初次见到时毫无二致。
“你们是谁?”迎面走来的一位妇人质问着,其骄横的气势显示着她的身份。
“随便看看。”刘冉道。
“这里哪是你们能够随便看看的地方,”妇人向南屋喊道,“小高……”
“到。”随着话音,一名年轻战士从屋里跑了过来。
“轰他们出去,把门看好。”妇人说罢,转身向里院走去。
来到街上,刘冉与你们分手时说了句,“我好像明白了一点昨天的仇恨了……”
你望着眼前这座象征着权力、荣耀和富贵的院落,心想,历史和现实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啊!古往今来,自从这座院落建成之日起,在这里搬进离开的人们便不断重复演绎着过程不同、结果一样的轮回。
春日里月色溶溶的夜晚。你和黄圆、翠翠、刘山、还有高成龙几个人一起来到德胜门城楼下的护城河边。一行人就那么默默地走着,谁也没有说话。你们走下立交桥,站在水边上。悼念过叉子的地方。你们默默地伫立在岸边,久久地凝望着水面。河对岸,乐曲悠扬,露天舞场上的人们欢歌笑语,舞影婀娜,一家新开饭店门前的彩灯瀑布般向水面流泻着。
黄圆拿出两只折好的纸船,打开,递给翠翠一只。她们各自将一朵洁白的花朵放进纸船里,然后伏下身,轻轻将小船放在水面上。“这只是给叉子的,”黄圆说。
两只洁白的纸船在被岸边灯光映照得熠熠发亮的水面上缓缓飘动着,清风吹过,它们转了个圈碰撞在了一起,相拥着向远处飘去。
你们走上河堤的时候,又一次回过头向水面望去,那两只相拥在一起的纸船已经不见了。蓦地,你看到在那五光十色的水面上仿佛浮现出黄方小时那灵巧的身影,那清瘦的脸庞,那和你在一起时讨好而又顽皮的笑靥……你们一起跳跃在护城河石块搭就的浮桥上……你们一起在门头沟的煤窑里……你们一起在北大荒……原始森林的小木屋……夜幕笼罩的田野上……你出逃时,他塞给你的香烟和罐头……他当犯人……他当总经理……他那辆专门捡垃圾用的竹制小推车……他那辆豪华奔驰车……他那句令你们结下终身友谊的话语“其实我出身也不好,我们家也是黑五类,没人理你我理你,没人跟你好咱俩好……”反复在你的耳边回响。
街灯漫射下的路面笔直地向远方延伸着,望不到尽头。抬眼看去,不远处夜幕下的钟楼犹如一幅巨大的剪影,挺拔矗立,巍峨壮观。一轮金黄色的满月低低地挂在天际边,像一位历史老人,无言地注视着这座生活着一千多万生灵的古老都市。
“但愿昨天真的已经过去……”黄圆说。
“是啊,”你低声道,“昨天!”
初稿于1996年秋
改毕于2006年春
沉默的钟楼 后记(1)
1966年的那个夏天,随着中国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的来临,所有同我一样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在一夜之间突然失学了。不用上学,不再作功课着实令人兴奋。但短暂的兴奋过后,用现代法西斯来形容他们也绝不过分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正式获得了官方的支持,成为了在中国猖狂一时的邪恶力量。这一政治怪胎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令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中,那时的国家机器全部瘫痪,由红卫兵用若干号通令的形式管理社会,并迅速开始了针对〃黑五类〃的惨绝人寰的抄家运动,北京首当其冲。
尽管我生长在北京,但年少的我当时只熟悉安定门往南、天安门往北、东直门往西、西直门往东这么一小块地方,它是我观察世界的全部。血腥的“红八月”里,尽管北京时值盛夏,但街上却冷冷清清。如果那时你留着一个稍显怪异的头型或穿着一条稍显体形的裤子又不幸被红卫兵们碰到,毫无疑问地你会落个先遭到一通暴打然后被当街剪成阴阳头和提着被剪成碎条的裤子落荒而逃的下场。顺着派出所警察和街道居委会的指引,疯狂至极的红卫兵们或从单位或从家中一个不落地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白发苍苍的学者、平日里谦恭卑顺、颤颤巍巍的老人(只因他们曾被划作地主、富农、资本家等身份),有各种历史问题和海外关系的人、右派、所谓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甚至还有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所谓“圈子”(就是那些平日里衣着入时、爱打扮、或有男朋友的女学生),统统揪了出来,就在这些人的家门口对他们进行批斗、殴打,侮辱和折磨的方式令人发指。当场被殴致死的人,扔上卡车拉往火葬场了事,尚存气息的则连同家人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往农村劳动改造。
这就是当年北京的真实情景。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黑五类”,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在社会中划分出这样一个备受打击和歧视的阶层,他们不知道那些属于“黑五类”的子女从一出生便被决定的悲惨命运。但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确确实实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过很长时间,造成了无数家庭无数人的悲剧。大的不谈,仅就人们司空见惯的填写履历表这样一件小事来说,我相信当时所有出身于所谓“黑五类”的子女在每一次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时,都要经历一次心理折磨,都像自己给自己再一次贴上耻辱的标签。回顾这段历史,会让人深刻感受到今天我们社会的进步对每一个人所具有的意义。
那时的夜晚,我常常被噩梦或红卫兵们的打杀声惊醒,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一位位往日邻居总在眼前晃动。 1968年初夏,当一个朋友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起他亲眼目睹当时声震京城的×××(一个被称作流氓的男中学生)被红卫兵们活活打死的经过及其人的诸多传闻时,某种已在心头多时的念头忽然明晰起来——是一种想要写些什么或记录下什么的冲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在一个前面还有数学作业的本子上,写下了近两万字的一个故事,是以那位被打死的中学生为生活原型的。遗憾的是,在以后的数次迁徙中,那个本子丢失了。数年后,当我开始了自己的文字生涯,这个故事便始终在心中萦绕。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迟迟没有能够写出它。直到1996年秋天,在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酝酿之后,我终于定下心神,动笔完成了这份夙愿。
在这部作品里,最初那种强烈地希望“清算”什么的情绪随着写作过程的推进,慢慢地得到了缓解。我越来越了悟:“清算”什么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尽管我至今仍然认为,红卫兵当年的那些恶行应该受到清算;而对于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来说,真正深切地汲取那个疯狂年代的惨痛教训,永远避免重蹈覆辙,才是最最重要的。但我必须坦白地承认,这样一种属于理性的感悟,在我的主观心志中,尚没有彻底完成。因此,细心的读者大概不难体察,上述两种情绪在作品中实际上是交织涌现的。对此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