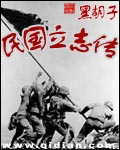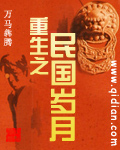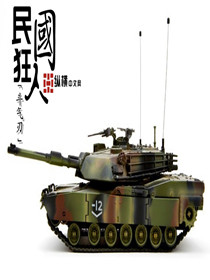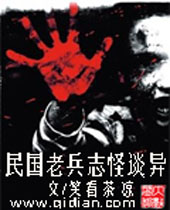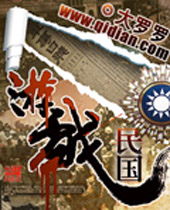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曹靖华记载:“当时社会上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起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进入北大要有证件,当时什么都不要。”
北大的旁听生、偷听生极多。一日,蔡元培、陈独秀、胡適晚饭后在沙滩附近散步,不经意间走到了“偷听生”们居住的“拉丁区”。他们好奇地走进一间屋子,只见一个衣着寒酸的青年正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身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陈独秀性急,上前劈头就问,青年惊惶不已,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一个穷学生,没钱办旁听证,但很想听豫才先生(鲁迅)讲课,所以……蔡打断了他的话,让他不要紧张,看了看那两个馒头说:“旁听证,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跟我去吃饭。”接着,三人便带着这个叫许钦文的青年到一个小饭馆吃饭。许像饿疯了似的大吃特吃,并对三人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的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了。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饭馆和食堂价格一个样。北大校园里还有三种学生,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摆地来校听课,我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
许多年后,许钦文深情回忆道:“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
冯友兰回忆他就学时的北大:“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
沈从文是北大庞大的“旁听生”队伍中的一员,学期结束时,他还冒充北大学生参加了考试,竟然还获得了3角5分钱的奖学金。这个浩浩荡荡的旁听生队伍中还有毛泽东、柔石、胡也频、李伟森等。
而曹靖华则是考上北大学生中的“旁听生”。因为曹交不起学费,便在北大旁听,学习俄语,后来得到李大钊的帮助,才正式成为北大学生。
陈顾远回忆,当时北大有一种“自绝生”,他们对蔡元培提出,要求废除考试。蔡答复道:“你要文凭,就得考试;你如果不要文凭,就不要考试;上课听你随便上,你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不上,但是你对外不能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同时你也不能有北京大学毕业的资格。”
蔡元培主张白话文,但他认为不一定要绝对排斥文言文;他主张新文学,但相信旧文学也有起不容否定的价值:“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正因如此,他既热心为沈尹默的新体诗集作序,也乐于为浦瑞堂的《白话唐人七绝百首》作序。
蔡元培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肯定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情,但同时告诫学生不要因政治问题而牺牲学业,他说:“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无能、科学无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
陆宗达在北大读书时,整学期在南京中央大学旁听黄侃讲课,一天,他对黄侃说:“我已拿到北京大学毕业文凭。”黄侃甚觉奇怪:“你在南方上课,如何能拿到北方文凭呢?”从此例足可见北大之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非难】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群情鼎沸,全国各地学生奔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立即抗日。1931年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正举行第四次临时常务会议,忽然会场门口出现了大批学生,他们愤怒地砸了门上的国民党党徽,缴了卫兵的德制驳壳枪,砸烂了传达室和会客厅。会议决定让陈铭枢和蔡元培出面救火。据台湾1986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记载:蔡、陈二人刚出会场,便闻呼打之声。蔡甫发数语,学生即将蔡拖下殴打。现场总指挥李时雨回忆,北平艺术学院的女同学薛迅打了蔡一记耳光。学生们又以木棍猛击陈的头颅,陈当即昏厥倒地。中央党部的职员警卫立即上前救护,但学生中有人向他们开枪,然后冲进会场,用木棍殴打众人,绑架蔡向门外冲去,警卫只好向天空鸣枪示警,并追出营救蔡。
时蔡元培年事已高,腿脚有残疾,学生们便强行拖着他向前跑。走了几百米,蔡的右臂即红肿异常,实在跑不动了,学生们先是把他放在黄包车上,后来又是背着他,沿荒野小路向中央大学一路狂奔。警卫们直追至玄武门附近的荒田中,才将蔡救回。
得救后的蔡元培立即被送往医院。当天下午,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予头部受棍击,似无伤害,惟右膀被暴徒扭拉,颇伤及筋络……”尽管挨了打,蔡却首先检讨自己的过失,他对记者说,“今日在场青年之粗暴如此,实为我辈从事教育者未能努力所致”,此次暴动,“绝非单纯爱国学生之所为,必有反动分子主动其间,学生因爱国而为反动分子利用”。他表示,对于合法的学生运动,“仍愿政府与社会加以爱护,绝不因今日之扰乱而更变平素之主张也”。
【忧国】
蔡元培主张革命、反满。1904年,慈禧生日,蔡发表时评《万寿无疆》,说:“每逢万寿,必定丧失土地。”
蒋梦麟回忆:“蔡先生年轻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清朝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清朝,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元培早年积极鼓吹革命。他曾办两所学校:爱国男校与爱国女校,他计划让男学生搞暴动,女学生搞暗杀(因为女生不引人注意)。蔡主持爱国女学校时,历史课常讲述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等故事,理化课则注重炸弹制造等内容。林语堂回忆,他到北大去请蔡元培为其文章作序时,北大校长候客室当中的玻璃架内,还陈列着一些炸弹、手榴弹。
蔡元培曾经是暗杀团的骨干成员。1904年春,他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准备利用暗杀,推进反清革命。为了配合暗杀行动,蔡元培自行研制方便、秘密、快速且容易伪装隐蔽的化学毒药。他让爱国女校化学教员俞子夷研制毒药。俞配制出氰酸,蔡给一只猫灌下几滴,猫即死亡。后蔡又觉得液体毒药使用起来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决定改成固体粉末,于是向日本购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法医学的书籍,自行研究,但无太大进展。不久,他又开始研制炸药。经过试验,他们研制出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蔡还让陶成章、龚未生翻译催眠术,以备暗杀之用。
蔡元培友人钟宪鬯研究化学,蔡介绍他入会,拼合炸药,炸药成后,又发觉无弹壳装盛。恰黄兴从东京到上海,秘携弹壳十余只。炸弹制成后,到南京雨花台偏僻处试验,竟不能爆炸。蔡下决心改良,与其介弟蔡元康等人废寝忘食研究,终于造出了一枚炸弹,用于暗杀出洋考察宪政的清室五大臣,投弹者为吴樾。
马鉴回忆,1904年,蔡元培办《警钟》时,已剪发易装,在中山装外穿了一件蓝色的棉大衣。当时天气寒冷,编辑室大而空,且无火炉。蔡右手生冻疮,手肿得像馒头一样,只能套一双半截露手指的手套,将左手放在大衣口袋中取暖,每天坚持写文言、白话文章各一篇。当时蔡不仅要负责编辑事务,还要负责报社的杂务,如伙食、印刷等。虽境况窘迫,但蔡总是心平气和,没有丝毫不悦之情。到了除夕,社中实在困难,蔡便向某君借得蜜蜡朝珠一串,让马拿去典当。到了典当行,朝奉说是假的,只能给一元钱。马回去告诉蔡,蔡只是微笑说道:“朝奉说是假的也没有办法。”最后这串朝珠没有典当,而年关总算挨过去了。
是年冬,蔡元培等人成立光复会,蔡出任会长。陶成章应蔡之邀入会。辛亥革命后,陶成章甫归国便被上海都督陈其美指派蒋介石、王祝卿暗杀。迫于陈的压力,当时沪上各报对此事不敢评论。唯《越铎日报》曾发表评论略谓:“陶之死,各方反应甚微,唯有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南京为陶举行之追悼会上致悼词,痛惜备至,甚至泣下沾襟。”
护法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主张应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统一。1918年10月,他与熊希龄、张謇、王宠惠等人成立和平期成会,通电全国,痛陈:“慨自国内构衅,忽已年余,强为畛域之分,酿成南北之局,驯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军暴露,万姓流离,长此相持,何以立国。”他亦致信孙中山,表达了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战乱,实现南北和平统一的观点。
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上台,蔡元培再次呼吁实现南北统一。他反对北伐,支持吴佩孚的建议: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职。
梁启超、林长民曾想拉拢胡適、蔡元培、王宠惠等人加入研究系。但胡、蔡二人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倡“好人政府”。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適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呢?”
蔡元培曾同情俄国革命。1923年,第三国际派越飞到北京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某晚,中国知识分子在北京撷英饭店为越飞举办欢迎宴会,蔡元培于席间致欢迎词道:“俄国革命已经予中国的革命运动极大的鼓励。”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捕。蔡元培支持“清党”,但他得知国民党清党委员会成立当晚,枪决了二十余名共产党人时,很严肃地对姜绍谟说:“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人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会才好!”此次清党运动,也成为蔡与国民党高层的意见分歧的根源。
1931年,蔡元培主持国民党的宁粤和谈,广东方面的代表李文范常很激动地跳出来骂,而伍朝枢则对王宠惠冷嘲热讽,但蔡在席上纹丝不动,处之泰然。当时国难当头,经常有人前来请愿,蔡亦不理会,只是让汪精卫去挡驾,并不过问这些事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步伐逐渐加快,国民党内主战派与主和派争吵不休。1934年,蔡元培在南京的一次宴会上激动地对主和派代表汪精卫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蔡一边说着,一边禁不住老泪纵横,两行热泪流到了西餐的汤盘里,他低头连汤带泪吞咽下去。举座动容,汪如坐针毡。
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任该同盟副主席。该同盟宗旨为保障人权,并不区分党派、国籍、罪或非罪。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蔡元培都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营救了许多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蔡元培对周极为佩服。1939年5月,陈翰笙途经香港时,去看望蔡元培。一见面,蔡便握住陈的手,激动地说:“周恩来了不起!”
蔡元培晚年,一度署名周子馀,其友周成曾问由来,蔡笑道:“周蔡原为一家,你不知道蔡也出自姬姓吗?”随即又正色道:“我母亲姓周,所以用此姓。”后其学生余天民道出此名的深意:周子馀兼含《诗经》“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之义,以暗示“孑民”二字。蔡早年用“孑民”一号,是表示在清朝统治之下,所余黎民,再无有遗类,有同仇敌忾之意;日寇清华后,民无噍类,故蔡始用“子馀”。
余天民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其师蔡元培避居香港,国内外人士屡邀蔡移居昆明,或到国外如新加坡、菲律宾等地旅行,蔡均婉辞。一次,张静江曾邀请蔡一同赴美,蔡亦当面辞谢,说己身负中研院职责,文化学术工作,关系国家百年大计,未可一日停顿,实不能远离,望其原谅。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