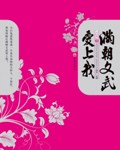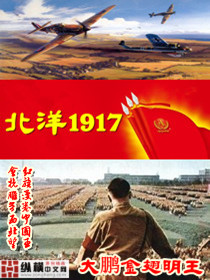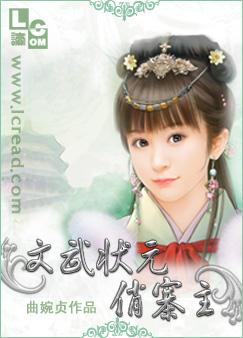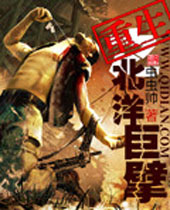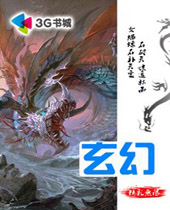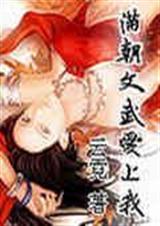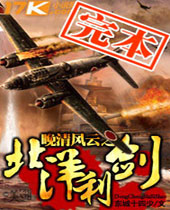文武北洋-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今人已经看不出八十多年前的“大总统”和“大皇帝”之间有什么不同了。
其实,二者之间决不仅仅是名分上的不同。
从封建专制到共和国体,从“真龙天子”到“民国公仆”,从向来一人专权变成议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这一切,对昨天还是大清国臣工的衮衮诸公来说,尤其对袁世凯这个前朝的首席军机大臣来说,是多么的不适应啊!不能指望习惯于跪地咚咚磕头的人们会适应比肩而坐投票表决国是,须知,西式黑呢高帽罩着的是刚刚剪掉辫子的脑袋。现在的人们,若不静下心来,恐想象不出当年的天大的不同。
对袁氏何以称帝,袁的亲属及亲信都说,主要是吃亏于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与所有的专制国度的君主一样,袁世凯到晚年最相信的也是自己的儿子。但就在其长子极力鼓动他当“中华帝国”皇帝的最热闹的时候,他才猛悟出自己陷入了绝境。
事情败露于偶然。
就在袁世凯屁颠儿屁颠儿地忙碌着登基的时候,全家女人们也都跟着乐呵呵地订制娘娘和公主服饰的时候,未来的三公主袁静雪瞅着丫环买回来的五香酥蚕豆傻了眼——老袁家法很严,自家的女人,无论大小妻妾还是哪房女儿,一概不准抛头露面,所以,袁静雪想吃蚕豆,只能令下人上街去买。袁静雪无意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与自家的《顺天时报》完全不一样!外边的报纸上多是反对父亲称帝的报道,而自家的“舆论导向”却全是拥戴老爸当皇帝的消息!三小姐懵了,当晚例见父亲时,就把包蚕豆的报纸递了上去。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一张销量较大的报纸,老袁公余之暇总爱读它,以为这就是民心所向。原来,老袁这段时间看到的,一直是袁克定为他单独印制的假报!联想到这一阵子老有“请愿团”(甚至妓女们也组成一团)到“公府”(总统府)门前“劝进”,各地总有电报请他改做皇帝,老袁恍然大悟:都是
他妈的大儿子捣的鬼!第二天,盛怒的袁世凯召来袁克定,越说越气,甚至亲自动手用皮鞭狠狠抽打了不肖之子,边挞边痛骂其“欺父误国”。
迟至此时,袁世凯才明白:他将国体改为帝制,并非“天下归心”。
也有人说,他是上了“筹安会”的当。湘籍才子杨度和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等拥护帝制的“六君子”组成的这个劝进组织,一心忙着把老袁往御座上推。他们欺上瞒下,大造气氛,终于使得整日呆在深宫里的老袁头脑发热,“勉顺舆情”,放着牢固而舒适的西式高靠背椅不坐,宣布要改坐满人让出来的又硬又冷的御座。他成了新朝“中华帝国”的皇帝,那班人不就是开国元勋了吗?
斗胆称帝,天怒人怨,老袁自此人心丧尽!他追悔莫及,一病不起。在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版的《八十三天皇帝梦》一书中,袁的第七子袁克齐详细回忆了袁的弥留之际: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看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袁后悔了。
徐世昌应召从隐居的卫辉赶来,见到相交四十年的好友在病榻上命悬一线,不禁老泪纵横。当着袁克定、段祺瑞等人的面,徐世昌轻声问袁世凯:“总统有什么交代的?”老袁费尽最后一点气力,吐出了两个字:“约法。”这就是袁氏的政治遗言。
他死了以后,总统府发布了“先大总统遗令”: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就在他尸骨未寒时,人们打开了他生前写就继任者名字的“金匮石室”——这套由上一任指定传位于某某人的方式,还在沿用清室的老办法,但中华民国的约法上就是这么规定的,只不过候选名单不止一人,而是三个,即大总统可以指定三个人为其继任者。所以,老袁是在依法办事。
看来,至少在最后的时刻,这个辜负过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总算尊重并维护了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
稍微出人意料的是,那张纸上并没有传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位。
老袁总算还明白:天下不是自家的。
漳洹犹觉浅(6)
但袁世凯至死没弄明白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称帝”大蠢事,实在怨不得筹安会的“那几个人”,要怨,只能怨你自己:在宦海沉浮几十载了,难道不知道别人支的梯子不能贸然爬?是你自己灵魂深处爆发皇帝梦了,想尽享个人崇拜了,想独裁天下事了,才扭扭捏捏半推半就地往回头路上跨了一步。这一步,就让自己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想想就知道了,对袁世凯这样一个满脑子封建意识且个性极强的人来说,他怎么会喜欢上七嘴八舌的政治局面?一次次不得不面对政客们的相互攻讦与掣肘,他实在腻了!
他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人表示过这种茫然:总统、总理、总长(部长),都是“总”,到底谁说了算?
他手下一位要员曾更精辟地大发牢骚:“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这话太中听了!
皇帝时代,哪个文人敢公开辱骂“当今圣上”?可改成民国了,报纸上竟总拿他堂堂大总统“说事儿”,公开点名指责不说,甚至有报纸公然刊登了一组题
为《老猿百态》的漫画,其中一幅,画着一只猴子举起写有“专制”两字的大刀横跨于北京城头,题曰“刀大杀人多”。猿即袁,如此放肆地攻击国家最高领导人,实是“恶毒”之极!
让你言论自由,也不让你这么自由啊!
满口河南乡音、一直习惯用衣袖擦鼻涕的庄户老汉一样淳朴的袁大总统,终于战胜不了自己的中国农民的天大愿望——自主天下事。内心一直涌动着这种蠢念,旁人再一扶一推,他的下水也就势在必然了。
看看他晚年的足迹,一步步都是往独裁的道上走的:先是把主要的反对党国民党生生取缔,再是胡萝卜加大棒地控制国会,让那些自以为是的各界名流们要么拿钱说好话,要么干脆滚回家;后来,连内阁也觉着碍事了,便把国务院取消,降为总统府里的政事堂,内阁总理成为国务卿,各部悉成为“公府”里的办事处;最后,索性是把总统任期延长到十年一届,且可以连任——那时,他已是五十开外的花白胡子老头儿,再干几届,不就等于终身制了嘛!
本还有能力为中国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上首任民选大总统,就因一个皇帝梦,终于走到真正孤家寡人的绝境。
袁世凯因称帝而成为全民族的罪人。部将蔡锷潜回云南首举义旗誓师“讨贼”,西南各省立时群起响应;而京城的政客们也无不怨恨他,因为帝制一恢复,人们推翻满清的半生努力全废了。就连他身边的人也一个个与他翻了脸:副总统黎元洪杜门谢客,面对他派去的说客一言不发;被从青岛租界里拉来当国务卿的老友徐世昌也以不吱声来表示内心的不满;他一手拉扯起来的北洋军首领、陆军总长段祺瑞更是急脾气一个,当面即拉长了脸,并干脆自我“下课”——怎么召也不来见了;而派到南方去镇压西南地方武装的另一位大将冯国璋不光按兵不动,反倒联络各军首领们来了个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通电!
他四面楚歌,他万般无奈,他穷途末路。他只好在宣布实行帝制仅八十三天之后——民国十五年(1916年)3月22日,即通电全国: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
为时晚矣!各路人马不依不饶,非要袁世凯退出大总统位子来不可!皇帝没当成,总统竟也保不住了,这一下,袁世凯绝望了!此时,死对他和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在此之前还算是英雄的袁世凯,由是成了“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乱世奸雄”。这些头衔人们让他一直戴到现在,而且,还将继续戴下去,诚所谓“骨朽人间骂未销”。
历朝中国多少雄杰,为圆一个皇帝梦,成了令后世冷齿的跳梁小丑!
侧身西望长咨嗟:皇帝梦,做不得!高丽朝代兴衰,过客毁誉,一部中国近代史真够人细细观赏、品味的。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无论是在他崭露头角的朝鲜生涯,还是在平定“拳匪”内乱的督抚任上,尤其在胁迫清皇退位的关键时刻,他都表现出了一个汉族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机敏与勇气。这种机敏与勇气导致的后果,也可以称作“功劳”吧?
先说老袁早年。
那时,老袁还是小袁,不爱念书爱骑马,所以也就考取不了功名。第二度乡试失败后,他既羞且愤地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付之一炬,慨然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随后,他便带着几十个家乡的弟兄们跑到了山东的登州府,投奔过继父亲的好友、“庆军”统领吴长庆当兵去了。
吴长庆显然未意识到袁世凯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还以为不过是乡里的一个落榜秀才跑来找碗饭吃呢!因而,弃笔从戎的袁世凯开始时并未受到重用。
空有一腔抱负的袁世凯,某天对人大发牢骚,而且,正是这一番抱怨,改变了袁氏的一生。他如许喟叹:
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越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把守海防重镇,亟需人才,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这话说得真够慷慨激昂的。这一番表白传到吴统领的耳朵里,他能不惊喜吗?于是,未久,袁世凯就开始受到重用,成了吴将军麾下的营务处帮办,之后,又随吴的庆军一道去驻军朝鲜了。
漳洹犹觉浅(7)
那时的朝鲜,与越南、蒙古等周边小国一样,是中国的藩属国。
在朝鲜,袁世凯凭自己的能力,很快就成为吴长庆所倚重的主要佐将。那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却表现出了卓尔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而又不失原则的处世手段。
抄两个有关袁世凯在朝鲜的故事可为佐证。
第一个故事:某清军军官因凌辱朝鲜人而违犯军规,袁世凯欲照章将其处以极刑。他刚入朝时,曾下令一次斩首七个清军兵勇,因为这些人在“属邦”掳掠百姓有辱我中华国誉。吴长庆知小袁治军严厉且执法如山,便亲至袁的住处说情。吴将军怕小袁不给面子,就坐着不走。袁请吴公翻阅案上的图书,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回来后,却向长官叩头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出去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愧为领军人物,非但不责怪部下不给自己面子,反而大笑赞曰:“执法当如此!”过后,吴大人常告诫在营中当兵的亲戚们:可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胡来,即使我能饶恕你们,袁某也不会饶恕你们!
这样一位铁腕带出的军队,能不纪律严明?敢不奋勇阵前?日后回中国,袁世凯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练兵,只四年就带出了一支海内第一劲旅“新建陆军”,靠的正是这股子六亲不认、执法如山的狠劲儿。第二个故事:彼时朝鲜政局动荡,偏偏李鸿章为防辽东半岛遭日本人染指,命吴长庆率三营人马回国驻防,余下三营清军由吴兆有、袁世凯和张光前三人统领。高丽人内部已有“亲清派”与“亲日派”之分。日本人正在那里拼命培植反清势力,觊觎取中国而代之,故亲日派正在磨刀霍霍,风传将于近日发动政变,推翻亲清的现政权。值此危急关头,朝鲜邮电总局落成,三位中国驻军最高长官接到参加典礼的邀请。不言而喻,此为鸿门宴。去则性命难保,不去则有失宗主国之国格,真是进退两难(不知这一次是不是韩国人利用宴席搞政变的发轫之作,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好几位韩国总统是在吃饭时被部下刺杀从而使江山易主的)。那二位胆怯,称去不得也。但袁世凯不惧,他怀揣手枪,提前一小时即突现筵席,令对方措手不及。酒席刚开始不久,他又突然起身告辞,并手牵政变头目朴泳孝一路谈笑出了大门。阴谋者的阴谋终于落空。两天后,图谋不轨者仍不死心,又宴请了中国驻朝商务与税务官员和各国公使(偏偏日本公使未受邀请,可见东道主用心之险恶)。席间,果然有人持刀而入,并有武装叛乱分子冲入王宫!袁世凯闻讯,未待请示中央政府,便亲率二百清兵前往弹压。岂料,朝鲜军人已直接出面保护宫中的政变分子,双方对峙起来,情势万分危急!好一个袁世凯,亲率二百清兵全力攻入宫中,一举救出被围困的国王李熙。
袁世凯在日本的传奇情节,若编成戏文传唱下来,岂不妙哉?只可惜主角晚年不保,“卖国贼”的腐恶名声早就熏臭了其整个人生,谁还会记得其早年的壮举?
袁世凯凭其超人的胆识和能力维护了该国的国政,受到国王的信赖与多数大臣的拥戴,该国的内政外交,一时悉尊袁意。为了维持政局稳定,他还为王室编练了一支“镇抚军”。是年,袁氏仅二十五岁。
小袁在两次政变中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令老领导吴长庆欣慰不已,他曾向分管朝鲜事务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袁氏请功:(袁氏)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朝廷果然授予袁世凯五品同知衔,并赏顶戴花翎。一直耻于没有功名的袁世凯,终于凭自己的实力,实现了为国效力的理想,并获得多少读书人奋斗多年而不可得的地位。
但一个袁世凯岂能挽住既倒之狂澜?后来,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虚弱的中国政府不得不让日本分享了朝鲜宗主国的地位!
但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赏识是毋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