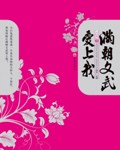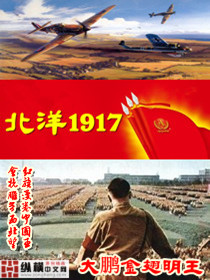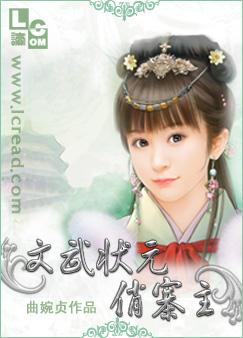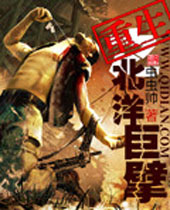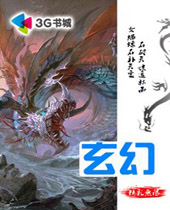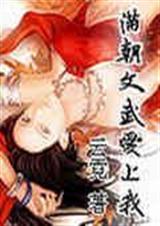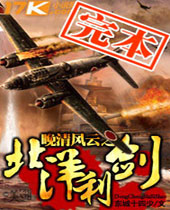文武北洋-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始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生涯。“经济”的本意为“经世济民”,与治理国家意思相同,与今日之“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清末,国难不已,满族统治者已经痛感人才之匮乏,而正常的科举制度已经无法为各级政权提供优秀的后备干部,于是,慈禧太后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绕开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由各部、院和各省督、抚、学政,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晋京直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里参加考试。已有“经济”名声的湖南才子杨度,入闱特科考场并不出人意料,让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总督锡良(满人)荐举给朝廷的。清时,湖南与湖北两省的一把手是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湖南学政等有关省领导没有向皇上推荐这位本土的才子,而偏偏让异地的旗籍蜀督抢了伯乐之功,足见当时满族官吏对国运之关切和对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总在告诉人们:皇权时代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经济特科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交上了答卷,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候选郎中”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此后话也。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的政敌、当过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数日后,他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杨度等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经济特科考试的人员,多系新党!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也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涛两次电奏朝廷,指名道姓地举报梁士诒与杨度与上海的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的,长诗被同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刊》上。此“歌”后来传回中国,大行其道,尤其诗中的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曾沸腾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在“东洋”,专心从事“经济”的杨度,受到正寓居日本的孙中山的青睐,孙亲往杨的住处,与他探讨挽救中国之良策,某日因谈话时间太长而不得不留宿杨宅,两人相谈至天明才抵足而眠。日后,他把湘籍知己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孙、黄合作之后,革命党才迅速壮大。留日期间,他还与另一位湖南老乡章士钊结下了终生的友情。后来,章氏不仅照顾了他的晚年,而且还在他辞世三十多年之后继续关照他的遗属。此外,他还与革命党干将胡汉民、汪精卫同窗求知。当然,“吾爱吾师(或吾友、吾同乡、吾同学),我尤爱真理”的老毛病又犯了,自负的他,时常与这些可以“对上牙”的人辩论救国方略。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就颇不以为然,认为孙氏革命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已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雄辩的孙先生纵有“孙大
炮”之绰号,也无法将其说服。杨度的政治才干和雄辩能力很快就赢得了中国留学生的膺服,湖南二百余学子投票选举同乡会会长,杨度得票八十二张,仅比公认的革命党首领黄兴少五张。日后,他又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馆干事长(相当于会长),可见人气之旺。因悉心研究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6年1月21日),随五位考察各国宪政大臣出访的湖南老乡熊希龄找到他,请他代五大臣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杨度遂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超众文采一并倾于纸上,写下《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纲领性文章。“答卷”上交后,得到了五大臣的赞赏,其精华悉收入“考察报告”中。对杨度来说,这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以致连住在养心殿里的那位老妇人也暗暗饶恕了他——慈禧太后同意光绪皇帝于是年七月十三(9月1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两年后,又接受了张之洞和袁世凯的联名保荐,传谕:
市井有谁知国士(3)
候选郎中杨度着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宪政编查馆,是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初名“考察政治馆”,由军务处的王大臣管理,至宣统年,竟由总理大臣亲兼一把手。所以说,此机构虽为新设,且是以编译和制订新法为主要工作的务虚部门,但级别很高,算是正部级编制呐!在内忧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满清政府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上宪政的道路。而杨度也应运而生,成为近代中华倡言宪政第一人。为筹建宪政党,他曾与熊希龄赶往神户,与梁启超“熟商三日夜”,由他本人出任宪政党干事长。所谓立宪,亦可谓政党政治。无多党,何来竞争?无竞争,何谈监督?无监督,何能不腐败?因内部人事纠纷,宪政党没能搭建起来,他又一鼓作气创建了“宪政讲习所”,后改称“宪政公会”,他任常务委员长,明确提出以“设立民选议院”为中心目标。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杨度回到湖南为伯父杨瑞生奔丧,仍念念不忘宪政大事,他发动湘省士民入京开展国会请愿运动,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今天,距这篇“宪政倡议书”问世近百年之后,我认真读着杨氏的激扬的文字,犹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标点与段落由笔者所加):
……国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国家之强弱,恒与人民之义务心为比例,断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尚可立宪者也。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几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即其当兵、纳税,亦纯出于强力之压迫,并不知人民对于国家之职务应如是也。东西各国,人思自救,举国一心,其忠君爱国之忱,我国人民实多逊色。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独不然者?即纯以民选议院之有无为之关键也!盖有民选议院,则国家对于人民,既付以参政之权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负其责,而彼此无复隔膜,且利害与共,意志自通,关系既深,观念自切。……今惟有利用代议制度,使人民与国家发生关系,以培养其国家观念而唤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后宪政之基础确立,富强之功效可期。否则,政府独裁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国家成为孤立,君主视若路人,虽日言“立宪”亦安有济乎?
多么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蒙课本!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被一个三十三岁的“执不同政见者”指着鼻子数落了一
通,并具体地教导了一顿,清王朝却并没恼羞成怒,反倒将这厮直接调入朝廷,让他专管宪政的普及和实施了!国运式微,当国者首先着急啊!然而,调入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的“反对党”干将一样的不“老实”,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以权谋私”,到处传播他那套宪政理论。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宪政道路的袁世凯,曾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僚们的相关质询。现在看来,这显然是足智多谋的袁氏为杨度摆下的一个挺不错的讲坛,要让朝中那班守旧的王公大臣们明白,“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勇,至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真是掷地有声,响遏行云!近百年前,杨度即有如许之见解,并有如许之勇气,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杨度的政治设计方案是,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即由国民代表们参与表决国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里的极少数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诺诺地称“皇上圣明”来决定国运。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形。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认定“国民会议”为灵丹妙药,仿佛这个会一开,南北就统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国就民主了,列强就知足了。从清末杨度开了头,直到整个北洋时代,此“会”成了朝野人士的一个心病,无论在朝的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也无论是在野的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当然更包括位于朝野之间的杨度,都一直在为开这么个会而孜孜不倦地奔走,结果直到“北洋”像老妪一样被凶悍的新妇国民党赶下台来,这个难产的“会”也没能降生。虽然杨度的政治理想一直未得实现,但他的才干却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民国三年(1914年),杨度着西式礼服留影。是年袁世凯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并亲授勋四位。
换地的人的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中山、黄兴引他为知交。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邀请孙、黄二位相继入京晤面,杨度即因与双方均有密切关系而专程从青岛赶往北京参与巨头之会。这样一位天赋很高且资望很好的政治家,却因笃信君主立宪而成了袁世凯称帝的头号帮凶。民国四年(1915年),他和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位颇有清誉的名士成立了“劝进”(劝袁氏当皇帝)的“筹安会”(时称“六君子”),他具体领导了帝制运动,由此得到袁大总统亲赐的“旷代逸才”匾额。是年12月13日,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翌年初,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刚好四十岁的杨度竟然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日后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子爵”还是“二等”;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追授了个“三等男”。杨度坚信自己会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甚至差人在法兰西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只会舞文弄墨的杨度竟如此煊赫,能不遭人忌恨?况且,他干的本来就是一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蠢事。于是,当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当家作主后,杨度和“筹安会六君子”立即成了新总统下令缉拿的“帝制祸首”——先总统是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死的,继任总统的通缉令是7月14日发布的。也就是说,杨度从九天之上摔入狗屎堆里,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若不是他犹豫之后终于遁往津门避难,没准其生命就中止于四十一岁那年了,因为有人动议开除他的国籍,更多的人则提议诛杨度以谢共和!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那些日子里,他不得不躲在青岛和天津两地的洋租界里,除了研究佛经,就是研墨临池——汉隶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活儿。后来每到潦倒时,他总能用自己的不菲的润笔费维持生计。那时的青岛,乃德意志帝国的远东租借地,非中国政府所能管辖。民国既立,逊清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前军机大臣那桐、前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一大批总督、巡抚、大臣、副大臣们,便纷纷成了胶澳租界的寓公。那时青岛的洋居民多而本土渔民少,而海边的房价兴许又太便宜,但凡北京跑来的遗老们都能买得起一幢依山面海形态各异的洋房。清末曾被袁世凯延揽入阁当学部副大臣的杨度,在众多“寓公”里,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毕竟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只是,前些年,青岛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煞风景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国洋房,现在剩下的寥寥几幢“原装楼”,哪有属于他杨度的只砖片瓦!他被解除通缉后,尽管曾出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甚至当过军阀张宗昌的总参议,但其名声之恶一直为人们所不齿。后来,南京政府成立,国民党对先总理的这位朋友并不领情,这个落魄的北洋名士,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惨兮兮地称“此后生涯正无住着,意在赴沪鬻文”。后来,他真的跑到上海滩住下,在老友章士钊的介绍下,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最后,竟正是为杜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但是,有谁能相信,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纵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这个委身于流氓头子门下的过气人物,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而他加入中共时,正是转入地下的中共被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不光国民党当政时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产党坐定天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一直拖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被亲历者似是不经意地披露出来!谜底是这样揭露给世人的——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