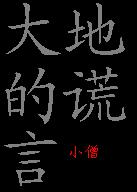谎言城堡-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有星星的。
我在喷泉旁站定,露天的青石凳上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湿水,冷冷的,我低头默默无语,像纪念,像决别。即使我有话想说又有谁人听?我兀自伤神。一个冰凉的水点扑入了颈间。哦!下雨了。我下意识朝那棵桂花树移了移身躲了躲。雨落无几,很久才在地面留下稀落的斑点。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出现,她的出现总伴随着雨落这好像是上天对她特别的眷顾对我的特别嘲弄。上天从不把视角投向我给我留一点点退路。因为天空下着雨我心底就有雨滴的声音。我忽然明白过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尽快离开此地,带走我来过这儿的身影。上天这次很吝啬,洒落了几粒雨点后就及早收回了对大地的恩泽,我抬头望望灰灰的天想走已以来不及了,上天童性未泯,再次拿我开玩笑。芷晴姐的说话声隔着几个草坪钻入了我的耳孔,接着是响起另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却有点恍惚的陌生。天色未明,有树,有花,挡住了视野。我快步走到假山另一侧,负着手假装对着一株长春藤发呆。就算她们不经意间看到了我,我也不是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其实我心里惊慌得无所适从,祈求没人知道我来过这儿。
柔软的脚步声踩着我的心跳,走过了我刚才停步的地方,又踩着我渐渐舒缓和失落的脉动远去,我暗松一口气,拼命压下了走出去看一眼芷晴姐她俩背影的冲动。
一个声音说不要虐待自己啦!
我说我没有虐待自己,只限于是走应该走的路。
那个声音就哑了。
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这些天,我都是早上出门, 回来后把自己关在家里的。
我很少有耐性从始到终做着一件事或者呆在一个地方。特别是不能容忍狭小的空间那令人窒息的压抑。在书房里呆过一段日子双眼看物品有了叠影后,我又有些不安分了。想去野外生存,但那是不可能的,自上次丛林遇险后,我们那个私自组建的野外生存爱好小组便名存实亡了。我又不情愿立刻回学校上课,离期末没几天了爸妈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推托说我的伤还没完全好。爸爸妈妈只好依了我。其实我的伤早就好了。转着篮球想去体育馆好好调整下自己又觉得没趣味,萧稣不在,谁和我对抗呀!
是否去“初初”酒吧我犹豫不决。余珏送给我的《信念欲坠》我一直在听。这天,我才想起要把它们存储到电脑里。原先我以为这张碟只有音乐,没想到打开后还有有图像。伴着第一首歌曲《信念欲坠》乐声的是一段流畅的动画,凄凉感伤。镜头开始时。漫天的花遮住了后面的一切。镜头前探,雪花渐少。一对姐弟蜷缩在一个墙角,衣服单薄。雪花在他们脚旁扑簌籁地落着,积压在墙头的雪仿佛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崩落下来掉在他们瘦瘦的的身子上。一阵风卷起,成千上万的白色碎片再次遮住了镜头。镜头慢慢向前靠近。小男孩的脸呈现,他正枕着姐姐的膝头睡着,睫毛跳动。嘴角挂着可爱的笑容,也许他正在做着一个甜甜的梦,梦中有通红火焰的大壁炉。衣服褛烂的姐姐一脸疲倦,口中喃喃说着什么像在哄弟弟入睡又像是在祈祷。镜头停住不动一会儿,又慢慢一往后拉,点点白影中,出现的是一片废墟,残墙颓壁,疮痍满目。那对姐弟就在这片荒凉的废墟中渐渐成为小黑点,最后隐灭在一瓣雪花后。最后一个镜头,是在一片冰原上,一只翅膀折了的鸽子正用红红的喙梳弄着伤处的羽毛。在它的脚下是一块透明的冻冰,冰块中赫然有一条橄榄枝。整段动画到此嘎然而止,音乐也落下。
我边惊叹边神往,石器乐队真不简单。余珏是个网络技师,这段动画应该是出自他手。后面的几首歌是用DV摄制的,有字幕。其中两首我想是在“初初”酒吧里摄下的宽大的现代厅堂,霓虹闪烁的乐台,台上石器投入的演出还有台下观众的欢呼。画面上,隐现一个网址,我很是好奇,迅速打开浏览器键入地址。弹出的竟是“回归石器”交友会的窗口。一段欢迎到词,一副帖图,正是《信念欲坠》最后那个震人心魄的掠影,上有一首浅色小诗:遥远/谁说是异梦恋人的心思/相随/谁说是人与影的分秒不离/咫尺天涯/是陌路不挽手相扶吗/天涯咫尺/你我捧出真心潇洒天下。
短短一首诗,就把“回归石器”交友会的宗旨道尽。进入内部要口令。我不是。只好悻悻离开。我想那里面一定有很多同龄人在交流,在逃离这个人情淡漠的世界,在那里,一定可以结识许多同在这座城市需要朋友需要理解的人。我想我是。
我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桌上:爸妈,中午我可能不回家了,我去一个同学家。若。
我不知道在我回家之前爸妈是否能看到纸条,我一出院,他们又天始进入了无序的工作中,回家的时间难有定准。有时是干脆不回家的。
找到“初初”酒吧比我预期想的要容易,一下公交车拉住一个站在街道边的小孩一问就问出来了。“初初”酒吧没有当街而设,是在一条干净的巷子里,与大街相连,大概是招徕附近的常客。当我走进巷子里时,身后跟上了两个人,一个中年人,一个年轻人。中年人打扮很平常。那位年轻人西装笔挺,轩昂的迈着步伐。我并没留意。我进了 “初初”酒吧,他们也跟了进来我便以为他们是酒吧的熟客。酒吧白天是很少有客人的,因为它并不提供高热量的食物。
服务生很是热情,仿佛我不是一个陌生的面孔,我选民一张靠里的桌子,要了一杯橘子汁。那中年人也凑过来说叨扰我了。问我可不可以同坐一张桌子。我不置可否一点了点头。对于陌生人的请求,不伤乎自己我不知道如何拒绝。但我心里奇怪,那么多空桌子,干嘛非要与我同一张?我双手捧捏着杯子,手肋支在桌面上,边抿着橘子汁边打量四周。酒吧很宽敞,现代风格很强烈,天花板低低的,那会促使人有想找人沟通聊天的欲求。最引人注目的是最里的乐台,上面摆放着金光闪闪的乐器,吧台后的两位服务生正在倾谈着,不时目光扫过来一下,顾客没几人。
中年人惬意地坐着,点了一杯生啤。年轻人也要了一杯生啤,不过他不像中年人安安静静地坐着,他的目光不住四处观察,很锐利。因为有几次我与他的目光相接,我首先移开目光投向别处。他的眼底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东东。
我不急于见到吴乐他们,其实是我抱着守株待兔的想法。对于面前这两位略略奇怪的人,我只用余光注意他们的举动,无论谁让陌生人黏上,心下都有所防备的,虽然我是男生。
酒吧内放的音乐是Bertie Higgins的《Casablanca》,感情说不出的深沉的一首经典歌曲。可惜,坠入爱河的不是我,可是,心碎的却是我。
“小兄弟,经常来这儿?”
中年人放下酒杯说。
和我说吗?我把目光从门口收回来,中年人笑吟吟地看着我,当然是问我了。
“不是,第一次”我转动着杯子答道。
“ 不上课?”
“休了学,出来透透气。”
中年人说是呀,现在的学生功课越来越机械了,把自己弄得像木头人似的,社会哪容得下那么多死脑瓜的人,纯粹是在浪费教育资源。
中年人一席话我使我对他好感大增,年轻人却似很不屑。
我说你们也常来?
不,不,也是第一次。中年人说。
外面挺热的。我心不在焉地说。
中年人说这家酒吧很不错,还有个乐台,不知道晚上是否有演出。
有啊,这儿有一个不错的乐队。我说。
中年人问我乐队的名字。
石器乐队。我说。
你认识?中年人问。年轻人停住了喝酒的动作侧耳听我俩的对话。我说认识,跟他们四人都认识,只不过一直没机会看他们的演出,贝斯手受伤了,最近可能不会来了。
是不是一次械斗把腿弄断了?一直一语不发的年轻人坐直身子问。
不知道。我说。我受不了他仿佛要看穿一切的目光,很不近心。萍水相逢我不需要倾心相待,不说真话也是出于防卫性的隐瞒。
那他们是否有一个什么组织什么的?年轻人穷追不舍地问。“不知道。”这次我更干脆利落地给他三个字。警惕性陡然提高,抬头望他,年轻人脸上有失望的神色。
这时,中年人吩咐年轻人说,小沈,帮我再叫杯啤酒。
我却清晰地捕捉到了他递给年轻人不要多说话的眼色。中年人手中的杯子里一半的液体正发着幽蓝的光,玉白的气泡滚滚向上窜着……
我感觉到眼前的两人并不单纯,他们想从我口中得到点什么,我揣摩着和善中年人和为疏锋芒年轻人的意图,跟“石器”乐队有过节?不会吧,不像呀!
中年人说,就你一人在这儿?没邀朋友来?
没有,一个人清静。我说。
中年人唉一声气说现在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太缺乏信任了,时兴什么思想独立,摆明是画地为牢呀!
我说不是朋友少了,我认为,人不需要太多的朋友,一两个就足够了。
中年人说说得好,咱们干杯!
好吗?我不太适应,但我还是拿起杯子象征性地与中年人的酒杯点碰了一下,那位年轻人似不太愿意但也草草一碰了碰。中年人一古脑儿把酒灌进了嘴里,我不知道是否也要像他那样才表示尊敬。干嘛学别人呢!我喝一点就放下了。
中年人说小兄弟你一脸失意,怎么了?
我说被人甩了,正伤心着呢!中年人说不像,情场失意该喝酒,你杯中是什么?
我说真的,不骗你。
中年人用一点也不相信的口吻说是吗?
我心里说谁求着你信呀!
中年人说没有朋友是最不快乐的,人生三大快乐,一是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二是能和自己最爱的人保持距离。最后嘛,就是别人在外面奔波的时候能躲在酒吧里点一杯自己爱喝的酒,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侃天扯地。
中年人笑了起来。
年轻人却立即反驳说,卞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第二大快乐怎么是保持距离呢?你蒙我们两个青头小子呀!
中年人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说,你嫩了点,天谁高?离恨天最高。病谁苦?相思病最苦,什么人最惨?围城里的人才叫惨,你越了雷池,要么病魔缠身,要么惨绝人寰,你快乐得起来吗你?
所以说和自己深爱的人只做异性朋友是最快乐的。我说。
对对,就他这意思。中年人指着我说。
我问怎样才能做到呢?
“这这。”中年人一时语塞,抓头挠脑说我还没仔细研究,让我好好想想。
我心里暗道不用想了,根本做不到,除非你爱她了。年轻人这时和我同守阵地,说,没辙了吧,卞队,叫老鼠守着香油哪有不监守自盗的道理?说出的话有时也砸脚后跟,小心些吧!
叫卞队的中个人横了年轻人一眼,说,你知道什么,我刚才是说溜了嘴,能躲着心爱的人把爱的人变成不爱的人才是人生的第二大快乐,总可以了吧!
我笑了,可是唯有我自己才明白那笑是多么的勉强。年轻人不肯就此放过中年人,他说,我总觉得你还是不对,没做亏心事干嘛要躲着?敢爱敢恨才是男子汉,卞队,你对着罪犯可从来没有退过半步。
中年人打断年轻人说净瞎说,我什么时候见义勇为了?说到这儿你就不懂了吧。你太爱她了,事事由她依她,向东向西全赁她,那我们的尊严何在?没尊严的快乐只能算是低级趣味。
年轻人不吱声了。
我说假如她是那样的人,并不值得我们去迷恋。年轻人附和着说是呀,卞队,你深有体会,我们可不会步你的后尘。中年人说我是吗?我只是提醒提醒你们而已。
中年人说小兄弟,还没问你姓什么呢?我说姓韩。中年人说你家呢?
我说在东城区。
中年人说你一个人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玩?
我说我来看我那位脚受用力的朋友,有半个多月没见他了。
你说的是那位贝斯手吗?他的伤是怎么弄的?中年人问。
我刚要回答,突然意识到在这之前年轻人也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里面说不定有什么文章,我犹豫该作何回答,说不知道吧。好像自己太无人性疑心病重了似的。
“韩若,真是你呀,怎么来了?”
一个声音在侧响起, 我扭头一看,鼻梁上架着黑边眼镜的何文不什么时候来到了桌旁。
怎么?不欢迎?我说。
哪能呢!脚好了吗?何文说。我说早好了。何文向着中年人和年轻人说这两位是……
中年人连忙起身说哦,我们来这这坐坐,这位小兄弟是你朋友啊,那我们就不打扰小兄弟了,有事就请吧!
那就不好意思了,请继续坐。何文说。
我总觉得中年人来这有着何种目的,想把中年人最后的那个问号当面请何文解释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又怕是我多疑,自上次误会了芷晴姐后,我对自己的直觉愈来愈不信任。
跟随着何文,从吧台旁的一扇小门进去,在狭小的过道间左拐右拐,路上断续可听到鼓点。从何文口中得知,余珏没有好好躺在医院,已经回来了。何文说吉它又不需要用脚来拨弦。
爬上二楼,强烈的鼓声金属打击声震和水泥地板都在发怵,不用猜就知道是吴乐在疯玩。何文说他们正为一首新歌编曲,都两天了还不尽人意。我说那我进去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就行了,别因我打断了余珏他们的的创作思维。
门上。有五个字。行书。“石器音乐屋”。
开门的脚步淹没在吴乐狂动的手中,不羁的声浪宛似滔天的海啸冲击,让我感到身子发虚。不得不佩服余珏对此可充耳不闻。房间很宽敞,建一个室内篮球场也没问题,四周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有几扇还用隔音材料覆上了。
第一个发现我进来的是吴乐,他展出一个欢迎的笑容。他坐在离站最远的一角正对着门。见我进来,他停下原来的节奏,有如咆哮的大海瞬息间风平浪静,反让人不自在。他看着我,盯着我的脚步轻抖他的双手,我脚一落地,鼓声一响,我还以为是我踏中了机关。我脚步一起一落,一种不温不火,收放自如的节奏悠然而生。一种特怪异的感觉在我心底升起,那鼓点好像不是从吴乐的手中迸飞的而是由我的脚步决定的。双足的点不由自主,有一种踩一曲踢踏舞的欲望,遗憾的是我没学。吴的欢迎方式很别出心裁。
直到我在一个不会打扰他们的地方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