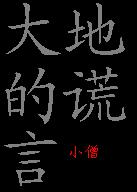谎言城堡-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吴乐说我说不过你,可我知道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是什么?余珏虚心地问。我是心急地问。
吴乐说移情别恋!
余珏说那你知道最笨的方法吗?
自杀呗!吴乐答道。
余珏笑着说错了错了,是一些爱情的白痴自以为情随时迁,就躲呀躲,看见对方的背影也转身就逃,以为一阵子不见面就一了百了,结果是什么?剪不断理还乱,神经质了见着自己的影子都想躲。
我脸上火烧地烫,余珏的笑他并不知道刺伤的是我。他的笑让我觉得自己特失败。我别过头望向窗个装没注意他们的对话。被人说成白痴我无所谓。可是当他接着说出了理由,一想,不错,还真的被他说中了,自己也承认自己是白痴了。同一件事上,当两次白痴就不可原谅了,我一定不会再当的。
余珏叫我一声,我噢地应了装回过神来。余珏说你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把一个人忘掉太简单不过了,我已经知道怎么去做了。
其实我什么也没悟出来,更不用说得了要领,我只知道,我当了一回别人口中的白痴,还不冤!
我从石器音乐屋出来时,石器乐队又在开始创作、修改上午完成的部份。看样子他们四人不打算下午走出音乐屋的门了。经过“初初”酒吧,那位年轻人的中年人不在。酒吧门口,意外遇上了冰初姐,一辆白色的玛莎拉蒂Coupe ,她依旧戴着遮光镜,不过不是浅蓝色的了,而是换成了淡紫色的。她正用后箱中搬着东西。
冰初姐。我叫了一声。
她抬头望我脸上的冰霜倾刻溶化了不少。
是你呀,见到了余珏和那三个小子吗?她说。
何文的年纪其实比冰初姐要大一二岁。冰初姐的年纪可能和吴乐差不多。可她却称何文他们三个小子别人听了心里肯定堵。何文他们三人有点怕冰初姐是真的,可是那不是心惊的害怕,而是一种甘拜下风的钦服。他们都知道冰初姐是个脸冷心热的人,所以总依了冰初姐有点像颐气指使的脾性也不唱对台戏。
我帮冰初姐把物品搬到音乐屋里去,几个大纸箱,封得严严实实似乎是一些很娇贵的东西,还有一个和何文一样的吉它盒。前天晚报上的消息看来所言非虚了。我默无言语地搬着,冰初姐似非常不痛快,用力往下砸车子的后箱盖。不过,她脸是上并没有愠怒之色,只冰冰的。我无法知道她心情的落点。
在公交车一路晕晕乎乎挤了回来,冲了个凉,窝在书房里,爸妈回来过,桌上的纸条不见了。在石器音乐屋中,全身的神经在强大的音乐冲击下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乍一回到家顿时觉得异常疲惫。在书房里坐着什么也没翻,出了一会儿神就跳到了卧室的床上躺着,品咂着自己当了一回白痴的味道,不知不觉阖上了眼皮,睡着了。
一觉醒来,夜色已开始浸染房间及窗外的世界。我起身到客厅冲了一杯速溶咖啡,打开窗子往外看,西方天空有一条绛红色的云带,一半隐没在暗青色的山峰下。云带的霞光,给远处楼房白色的墙壁涂抹上了一层柔和悦目的金橘黄色,就似旭日初升时,睡意刚祛的云气,此刻只多了一丁点儿欲眠的困意,要不是我深知此时并非早晨,亦要误以为是了。
我一个人朝着西方喝着微微苦意的咖啡,咖啡的味道宛若我心头泛起的孤独感,漂浮着被遗落的白色泡泡,一个人从睡梦中苏醒,窗外的夕景彤云遍飞,身边没人在,会有很深很深的遗落感的。我以前不是。现在是。我给不知要多晚才回家的爸爸妈妈留下纸条,直奔“初初”酒吧。
街上的人们行色匆匆,归巢温馨的窝。
也有孤单的鸟儿离巢,寻找暂时歇脚逃避孤单的枝头。像我。半路我下了车,想一个人走走。买了一个小风车,拿在手中对着它吹气,它就一圈一圈地转。
来到“初初”酒吧时,天空的晚霞的尾巴消失不见了。地上的人们像夜行动物走上了街头,一对对情侣搂肩揽腰亲密地慢慢信步着,路灯下他们的影子溶在一起分不出是一人还是两人的。我不明白,干嘛夜色下人们才有如此的亲近,是夜幕下的谎言更容易罗织誓言更容易相信还是夜本来就是爱情的缔约者?商店的橱窗内灯火通明,偶尔有音乐飘出,可是却不见钢琴弦管的。终于有一家茶室有一点格调,放的却是Kenny G的《回家》。悠淡的萨克斯声中的家很温暖,用一种无言的吸引召唤街头流落的人,我驻足听了一会儿,真的有点想家。
我理了理衣服,穿过街道,走进了“初初”酒吧。
夜女神光临的“初初”酒吧跟白天的“初初”酒吧皆然不同。顾客满了座,还不断有人进来,到处是笑声和私语,显得有那么一点点嘈杂,悠远轻扬的音乐使欢娱的宾客还有一片宁静的空间。灯光暗淡的乐台,没有石器乐队成员的身影,我略略失望,同时庆幸等一会儿可以从头到尾看石器乐队的演出了,虽然今天在石器音乐屋中我已领教了他们精湛的技艺,可是我还想欣赏他们在乐台上众星拱月的风采。
形形色色的人中,我看见了叫卞队的中年人和叫小沈的年轻人,与上午无异的打扮。中年人闲适地啜饮着酒,年轻人依然目光锐利地在打量。我看见了他们,中年人也看见了我,打手势要我过去。对他俩的疑虑我未消,可是只有他们一桌是最多空位的我不能总站着,就走了过去。
不等我坐下,中年人就站起来往下拉我的衣袖,说,小兄弟,真是有缘,坐下来喝点什么,我埋单。
笑里藏刀?口蜜腹剑?我脑中冒出这两个成语。在这个不面渐冷的世界他的热情很让人起疑。至少我会这么想。中年人的过度热情反使想坐的我此刻坐不下去,我迟疑着。
怎么?不给面子。中年人说。
“不是……”我一时找不出充分的理由不由语塞。
“别那么扭扭捏捏,其实很多时候跟一个心心相印的好友谈天说地还不如跟一个今天认识明天不相遇的人侃在扯地痛快,男子汉何必支支吾吾,坐下来欣赏欣赏音乐也不 枉我们相逢一场。”
中年人说。他的话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世界本质的思考。即使刎颈之交或多或少也有隐私,一吐为快最好是找个萍水相逢,朝识暮散的陌路人,把腹中的苦水、愤世嫉俗一泻千里。这样也不必担心明朝自己的脆弱地带遭人攻击。因为很多创伤往往是朋友造成的。
也许,陌路人只是时间上的陌路而不是感情上的陌路。
对中年人的疑云骤消我坐了下来,暗笑自已太年轻把世界想得太黑暗,凡一切不符合自己想像中必然的事都暗藏着陷阱。我保持着脸上的微微笑意,那位眼神似雏鹰般的 年轻人好像没把注意力放在我这个客人身上,始终未语一言,兀自喝着生啤,目光飘向酒吧一个紫光红光昏暗的角落,中年人是显出他健谈周到的一面,他接过服务生盘中的饮料,推到我面前,说,小兄弟,你家那么远,一个人晚上还来这?
我说今晚有石器乐队的演出,我是来为他们捧场的,石器那么优秀的一个乐队,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委屈他们了。
我明白初初酒吧只是石器临时歇脚的树枝,有一天他们会展翅高飞的。他们的理想是自由飞翔在音乐的天空里,BEYOND留过泪水的天空,他们会向更高更远的音乐太空飞去。
中年人说玩音乐的人应该让更多的人接受他们。
我说石器乐队不只是玩音乐还是音乐享受的创造者。
中年人说石器的歌我还无缘耳闻,听你一说,想必是天籁之音了,弄得我心痒痒的,今晚他们的演出我一定不能错过了,只是我年纪大了,没有年轻时候的激情,不像你 们小辈一样,喜欢听打击乐,摇滚乐对我们来说,还是太吵了一点。
听些轻缓的音乐可能修身养性,我们偏向金属乐,其实是不成熟的表现。我说。
中年人说对,到了参禅悟道的年龄才需要低柔华美的音乐,这种音乐会磨灭人的锐气,让人只想到感恩,朝气蓬勃的人还是要多呼些振奋人心的音乐。
中年人的话不觉又触动了我,让我想起了一个人,轻柔唯美。她的好友——我不知道她俩是不是依然各怀心事。也曾说她像一首飘渺的轻乐曲,难道她也到了禅意尽悟,心 如秋水波澜难起的境界?不。我想她用的是另一种方式。我们用嘈杂对抗纷乱的世界。她是在纷乱的世界中寻求一方宁静写意的净土,她曾无数次拿本书坐于窗台前沉寂其中忘掉了我也忘掉了整个世界。她也曾内疚过,也曾为好友的不交心苦恼过,也曾为爱憔悴过,她虽不是禅者却是圣者。
我的唇贴向杯沿,酸酸的柠檬汁化做一条冰凉的细线,从舌尖流向咽喉,或许,萧叶茗与我就像这柠檬汁,不去品尝就如没有开始的开始,没人期待结果,一旦流过味蕾,有的,是心酸的感觉。
突然想生余珏的气,干嘛不教我一个更容易遗忘一个人的方法。
余珏来了。
酒吧内突然安静下来,原先的音乐亦停止了,接着是掌声响起。刚才昏暗的乐台现已彩灯闪烁。石器乐队的四位成员已经各就其位了,余珏抱着贝斯从在轮椅中,掌声一 半的热烈是给他的。我放下柠檬汁跟着大家拍手,中年人也鼓了掌赞赏性地打量台上的四位年轻的音乐人。
坐在我左侧的年轻人也回了头,眼神恢复了犀利,仿佛要看透人心在想着什么似的盯着石器乐队成员。他的这种举动让我想起了电视中警察正盯着何机作案的罪犯,只要一出手就立马拿下。我心里特堵,冷眼瞥他一眼,哼!干嘛吗?以至众人的掌声熄了我还使劲多拍了一个节奏,故意的。
一身黑衣,长着一副斯文像的何文潇洒的对准了话筒。
“谢谢大家光临初初酒吧,你们的掌声使的感到很荣幸也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智者问一位老禅师掌声与梵音谁更去动听?禅师回答是掌声。智者说掌声是名 与利的认可,就笑话禅师还有名利之欲。老禅师笑着说梵音只能超渡方外之人,而掌声是一个人前世修的功果,是告诉来世之身自己前世是受过别人赞赏的人,于是来世之身就记住了前世的光荣,就不会做些被人唾骂的事了。所以说掌声救赎的是凡世之人。现在我们石器受了大家这么多热情的掌声,我们只有不息自强,让你们的掌声永恒,也使我们不至于哪一天被你们扔进音乐的垃圾筒。谢谢!”
何文鞠了一个躬,酒吧内再响起一片掌声,这时目光都集中在乐台上,可是我发现也有例外,同坐叫小沈的年轻人此时却并不关心乐台上的四人,大家全部一个方向独独他心不在焉。
“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想献给一个如天上星星般灿烂的人,她是我妹妹。最近她跟她的朋友们闹得很不愉快,结果散了,我想她现在心里一定不好受很痛苦。接下来, 我们把Blue Star的《别说离开》献给她,希望准备好明天的笑容,和我们一起分享快乐。”
何文深情的话落下,乐声随之骤然响起。当何文还没说完时,我就开始向四周搜寻冰初姐。石器乐队的第一首歌是送给她的,是她们Blue Star自己的歌。冰初姐肯定在酒吧内,以她不事张扬的个性,她可能在某个不稀少的角落坐着。吧台前一排高脚凳上没她的身影,乐台前更不见她。当我的目光转向酒吧中央紫光红光交汇处时,我看到了她。
一张靠墙的椅子,一副遮蔽感情的眼镜,一头长发下一张拒人千里的丽质脸庞,一身简约适身的薄衣衫,双手互抱着上臂,半个身子陷在椅子内,仿佛一尊美丽的塑像,木然看着乐台上的石器乐队。她为Blue Star付出的心血转眼成灰,她会非常难过的。今天我帮她搬东西进石器音乐屋,她毫无前兆地把一个纸箱摔往地上,玻璃玉碎的裂溅声把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摔碎的,是奖杯一类的物品。那是面记载着Blue Star光荣的过去,可是也如玻璃一样易碎。当时,大有都知道这并不是毫无来由的怨气。但谁也 没说,只让余珏一人去劝她。
……/让我们别说离开/只挥挥手说再见/再见的人还有下一次的再见面/别说离开/转身大步向前迈/地球是圆的/下一站的一处一世相遇在背面/别说离开/拥抱一次就已足够/为何却要用谎言掩盖/……
何文惯有的沉郁嗓音在酒吧内每个酒杯里的液面上回着声。Blue Star这首歌从石器乐队中走出来,有了自己的风格,毕竟全女子乐队Blue Star的歌曲有些地方不适合石器乐队演唱。我再次望向冰初姐时,她取下了遮光镜,似在偷偷抹拭着眼泪,复又戴上。我低下头也跟着她伤心。她听了Blue Star自己创作的乐曲,想到乐曲虽在Blue Star却不是从前的了,她能不揪心么?外表坚强的她,还是露出了女孩最软弱的一面。
我知道她落泪的这一幕她不愿被人看见,我喝了一大口柠檬汁却意外的发现身旁的年轻人神魂离窍。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正好看见冰初姐再一次取下眼镜,年轻人的神魂都在黯然神伤的她的身上,我刚才奇怪年轻人干嘛不言一句,原来他的心思全在冰初姐身上,打她主意?哼!没见过佳人落泪呀!一副不知该如何收敛夸张入迷的表情是不是想让冰初姐知道有人盯着她流泪而使冰初姐难堪?
我为之气结。
幸好我们离冰初姐还有一段距离,冰初姐是不会东张西望的。
我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说,怎么样?石器还行吧!
中年人说实力派,比花哨派好多了,你跟他们四人真的很熟?我说我跟台上坐在轮椅中的那位贝斯手曾是一个房间的病友,还算可以。中年人说他们好像有很多像你一般年纪的朋友?我说当然,乐台前那几桌大概全是吧,石器这点号召力还是有的。
中年人说现在这个星那个星的,谁没有一杆子乐迷影迷?只是可惜了石器还在这个小地方,有朝一日,他们一定会大放异彩的,我们为那一天的早日到来干杯!
我非常高兴,因为石器是我的朋友,听别人赞扬自己的朋友是一件开心的事,而且石器的光明前程正是我希望的。
中年人一口喝干杯中的余酒,问我说,听说他们样样在行,还有一个网站,你知道吗?
网站?好像有一个吧!我说。
那你知不知道怎么进入站内?中年人问。年轻人这时收回在冰初姐向上的目光,留意我们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