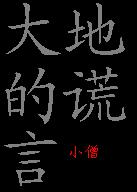谎言城堡-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哼,他们知道什么?一帮闲人,只顾眼前不看以后。”
“他们说是教育厅的副厅长叫你们放了他儿子,你们连其它人也一齐放了。”
我说。这不是假的,黄毛脑袋也承认了。可悲的是,卞警察他们竟要自欺欺人掩盖放人的真正原因,对于警察我由不已久的失望不是毫无缘由的。人类的天空,早已经不是清纯的湛蓝。
“绝对是在瞎说,破坏我们警察的形象。”沈警察紫涨着脸说,过份的激动表明他是个不知情的局外人但他应该听了一些风言碎语。“被我知道是谁在造谣生事,我不会放过他。”
沈警察和我突然不约而同望向卞警察。
“……,韩若不是空穴来风,没错,是教育厅的汤副厅长让局长放人的。”卞警察缓缓说。
“什么?”
沈警察不敢置信地说。抓一下自己的头发,他一定是想把警帽扯下来摔到地上,可是他过于激动忘了此刻他穿的是西装。
“世上没有圣人。”卞警察含义不明地说。
“小人。”沈警察也含义不明地骂一声,说,“卞队,我一直很崇敬你,没想到你也怕得罪人,跟他们串通一气,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你也睁只眼闭只眼。顺着他们的意思帮他们找理由放人……”
显然沈警察早就不满他的上司的同事。
“小沈,你听我说。”
可是,沈警察没有听,他说:“还像模像样满大街跟踪调查,把我一个人当猴耍,好,从今以后,我不干了,我是警察不是别人家的佣人。”
沈警察扭过头不理卞警察,也没抬脚走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是劝,还是添添乱。
“我经常对你说世上没有圣人,很多事不是你我说了算,更不能让人屈从我们的意愿。”卞警察无奈地说。
“为了迎合他们,我们就要丢弃原则的职业道德吗?”
“就是不让原则和信念一无是处,让抱负的责任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必须在小事上忍让,不能被孤立,懂吗?”
“那你怎样解释这件事?”沈警察不为所动。
“在大案上我们可以不让寸步据理力争,这种小事我们没有必要跟局长的同事们过不去。”
“我们还要把罪犯分等级对待?刑法上有对小犯罪特赦的条款吗?”
“小沈,现在的世界不允许我们当圣人,一视同仁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不要舍全求末,在小事绊住我们的手脚。”
“是,我们警察唯一目的就是破大案立大功,纵容一些不起眼的犯罪,使他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步步培养成一个死不抵过的人,到那时,再抓他,惩诫他,就算破了大案要案我们警察光荣吗?犯罪要消灭在初始状态,这也是你经常对我说的。”
沈警察吐出民大半怨气。
“你以为我就没半点怨气,就你看不惯权利交易,我干公安几十年,看得多了,没了你那种敢做敢为初生牛犊的冲劲,只想落个心静,可我能静得下来吗?你不是问过我这件小事为什么要我这个队长亲自调查,那么多案子还等着办呢!我告诉你,是钟局长直接叫人把人给放了,我只好将错就错把案子接手过来,我就是要试试,他们既然可以放人,我就可以再找理由把他们再抓回来。”
“怎么抓?刚才看见那么多人欧别人,你不管还好,干嘛拦着我,还让他们走了?”沈警察余气未消地说。
“你问这位小兄弟吧!”卞警察笑笑说。
我?我摸不着头脑。
“他怎么知道你算盘?”沈警察说。也道出了我的疑惑。
“你告诉小沈刚才你们揍的对象是谁就可了呢。”
卞警察说。我不好意思傻笑一声说:“他们就是你们钟局长放的五个人之中的三个,还有两个溜了。”
“你现大该明白我不让你去阻止的原因了吧,这是那几人逃过初一的代价。虽然我这么做有点违背警察的职责,但我是想告诉他们,并不是只有我们警察才能担负起维护社会安定的职责,即使侥幸躲过法律的制裁,也会有人站出来教训他们的。”
卞警察说。沈警察此刻的表情异常的夸张。
第十三章 弦
初初酒吧内。
见我走入,人群中的吴乐怪叫一声,十数道清澄的目光刷地朝我投来,宛如一道道微弱的电流击中了我,酥酥的。都是些生面孔,八九个女孩,嘴角含笑。我亦回报一 笑,学着她们随随便便打个手势。
我看看吴乐,很无奈。我如此受到G会员的瞩目,除了吴乐把我在巷子里的狂野曝了光外。应该无它。
韩若,快来呀,我正说着你痛打落水狗呢!吴乐嚷嚷道。
吴乐又让我无地自容了,他刚才向G会员们不是夸我英雄主义,而是乘人之危时的痛下杀手。他不算冤枉我,可是他不该在别人面前损我的形象,回归石器可不允许把别人的糗事当取悦人的笑料。被吴乐这么一搅,并没有影响我与卞警察冰释误会的愉悦心情。我耸耸身,像抖落尘土似的,大步走了过去。
巷子里有惊无险的一役,让卞警察对石器的怀疑之墙彻底瓦解,一役过后,所有针对石器的不利的理由都苍白无力。原因之一,那几个黄毛脑袋被证明与石器乐队无直接瓜葛,那几人是坚起回归石器的大旗,被抓后一口咬定石器乐队在背后策动,企图逃避法律,避重就轻,等待庇护网把他们接出去。第二,石器乐队所属的网站宣传不良信息,煸动情绪因为第一不成立也就不足为信了。原因之三,我留有私心,说助场的是石器乐队的乐迷和朋友,并没道出回归石器,否则卞警察真要以为这与帮派组织有不言而喻的暧昧了。
值得一提的是,卞警察原先以为我们修理那五个黄毛脑袋是由于他们在公安局出卖了石器。帮派中惩罚最重的就是出卖者,不过卞警察看到我们下手并不重,威胁的味道颇浓。当我疯狂时,吴乐反而拉住了我,卞警察说我一点也不像有肢体暴力欲望的人。他想不通,兼之受石器乐队《信念欲坠》的影响,所以当时他没为难石器。后来才隐约猜到什么,经过我十分不友好的解释。他说幸好当时没有拦下何文他们,要不就又要闹他们警察的笑话了。其实,我的开心不仅是因为卞警察和石器的误解冰消。还有我重新赢得了卞警察析信任。让我明白自己可以做很多事,而不是天天用幻想来弥补现实。
余珏何文他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我成功化解了卞警察对他们的误会,对别人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但我却觉得这是从我出生至此刻的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想想,都为自己以前的空虚痛心不已。或许为朋友排忧解难是人生中最在的快乐。生活的灿烂美好,是自己创造的,更是别人的笑容赋予的,真的。
回归石器的G会员是特地来慰问我们这群没有浴血但凯旋归来的B会员的,一身暑气进了酒吧,就有一杯欢乐地冒着珍珠似的泡沫的生啤在桌上等着,一旁有人托腮扑闪着眼睛倾听,难怪吴乐发出人生至此,夫复何求的感叹。吴乐十分忘形,在一片银铃笑声中,不断重复描述着那三位仁兄的窝囊。吴乐再一次迷失在G会员的甜言蜜语中。要是你以为他真迷失了那你错了,和他们这么久,我已学会了他们眼光的投注点。吴乐的迷失是一种心情的调剂,保留好的心情。真正的他,像石器另三们面员一般,在一半是在音乐中。
与死神错过一线,我走出了校园的束缚,入住了那一间有过无数幻想的温暖病房,或许冥冥中的命运之神在作弄人之后会给一些补偿,余珏就成为了我的病友,让我认识了理想不凡很阳光的石器乐队,现在可以和他们还有他们的朋友开开心心默契地笑着。不知什么时候,心冷到了极点,没有缘由的心冷,以为现在物质堆砌的城市里是不可能找到幸福快乐的伊甸园,一个人就学会了孤独,与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界线,天真而又固执地认为人是孤立的。孤立的人不需要别人手心的温度,一如星朗之夜月亮的清浑,皎洁凄迷,星光遮掩不了它,而阳光早已匿身于星球的另一边,我曾经面对着一轮弯月呆呆地想过,这孤独么?有一天我想通了,它不会。宛似雪山上的一泓潭水,纵然波光中全是太阳的笑脸,它的瞳仁依旧澈如寒冰。
月亮不知孤独是何物。
现在我终于明白,以前的我一直生活有孤独中。
在回归石器,忽然间我得到了自己一直默默寻找的东西,梦幻的纯净、自由的呼吸、无意识的狂想,和那些一样需要适度逃避的人一同诅咒世界的肮脏、城市的冰冷。一同用手指肚蘸着橙汁在桌面上写着愿望,摆弄心情,然后看着愿望理想慢慢从桌面上一点一点蒸发,心底一点一点萌生把它留住的欲望。
一个G会员说了一个笑话,趁他们笑得前仰后合我开了溜。奔往石器音乐屋看余珏,我们胜利归来还没向他报信呢!一阵行去流水的吉它声从音乐屋的门缝中悠悠飘了出来,我推门的手愣住了,石器乐队的吉它手明明还在酒吧,那是谁还有如此灵动的指尖弹出这么流畅华美的乐声,是贝斯手余珏?不会吧!
再一串美妙的音符从门缝中挤出来,争先恐后向外面自由的天空飞去。我情不自禁推开了门。何文那把白色的吉它在一双纤细凝脂般的手中微微暗晃动。修长手指的挑拨动作更是难以看清,那双手的主人冰初姐半闭着眼睛,长发一跳一跳的,她正如痴如醉,好似她全部的身心都溶入不敷出了六根弦线之中,所以我的到来她毫无所觉。坐在轮椅上的余珏侧对着我,咬着笔头思索着,也到了忘我的境界,亦没发现我的步入。连进入境界都这么默契,真是天生的相通心犀啊!
以前总是痛失机会看Blue Star的演出,认识冰初退姐后更是失落无缘目睹她在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表演。第一次进石器音乐屋那天,领教了何文出神入化的技艺,以为他足以傲视群雄睥睨本市的乐坛。此刻我才知道,出神入化后还有登峰造极,登峰造极之后也许有至臻完美。可以进步的东西都是无止境的。冰初姐指间的乐声没有任何一点生涩,听在耳中宛如握一把清晨的雨水,感觉不到砭着肌肤的突兀僵硬,冰初姐是Blue Star当之无愧的灵魂乐手。
其实成就一个灵魂乐手的付出。究竟要多少,没人说得清,曾经的Blue Star烟消云散又有多少人为之遗憾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最好的回答是那晚石器乐队在唱Blue Star的《别说离开》时独坐一隅的冰初姐眼中漫溢出的泪水。那几颗晶莹的泪珠明白其中有多少的辛酸。
Blue Star如一片彩云入暮,不再有绚丽的色彩。这给说初姐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她身上遍是创伤的余痕,昔日飘逸秀美的头发失去了交泽,微微的凌乱,衣角皱着,不像从 前那样讲究色调的搭配,随随便便一件棕色的上衣配蓝色膝裙。她脸很冷很平静,或许是因为她正沉醉在自己创造的魔幻音乐中而暂时消去了憔悴的踪影,音乐一旦停下,冰初姐将怎样是我不愿想象的。
我想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有一个信念支撑着他生命的一半。音乐是冰初姐的另一半生命,她爱音乐的程度甚至胜过对余珏的爱,余珏在医院时,她因和另四颗星星不和, 一连几天都抛下了行动不便的余珏。在那之前,她对余珏的细心照料一度使我认为余珏是她生命的全部。
我悄悄默站了一会儿,想掩上门离去,此刻我不应该鲁莽打断进入音乐圣土的冰初姐的思维。余珏他们最害怕的是冰初姐承受不了打击,从而消沉,那天在酒吧,冰初姐 笑着说她不可能成为酒鬼,我当时没说什么,然而她脚边的两个空酒瓶让我无法轻松,既然她们现在回归到原来的她,哪怕是一点点光阴仍然没有必要硬生生把她扯回现实中去。
门掩到了一半余珏看见了我,招手示意我进去,我苦着脸摇头指指冰初姐,示意说打扰她恐怕不好。余珏打出手势说没事,不要紧的。我复又推门进去,尽量放轻脚步。来到余珏身旁。
怎么样?顺利吧?余珏低声说。
我点点头。
余珏说他们三个是不是在酒吧跟那些女孩子喝庆功酒,吴乐是不是又在吹牛了?
我说是。
余珏的膝头的画夹上放着一沓A4纸,最上面的一张画了五线谱,还谱了一半曲,曲名是《蓝色流星》,下有一行小字:献给我最爱和最爱我的人。不用想就知道是余珏为冰初姐写的:
相遇的那晚你说你有一个蓝色的梦/梦中的花蕾结在遥远的星空/夜色下的城市有你灿烂的笑容/你让我感动/飞鸟飞过后的天空/也有我年轻的梦/未干的翅膀有高飞的冲动……
词没有填完,纸面上东涂西抹,从成形的歌词上可以看出,首歌的旋律应当很优美而带有微涩的伤感。蓝色流星,不就是殒命的Blue Star么?余珏发现我盯着他膝上的 纸出神,腼腆一笑,说,刚才突然有了一点点灵感,就随便画画,以前几首歌太注重感官上的冲击,我试着换一种风格。比较轻柔,节奏上会弱化一些。
是给冰初姐的吧!我说。乐理方面的知识我少得可怜,不能跟余珏谈音乐。
余珏说是啊!你看她,变得连我也有点不认识了,我想说服她加入我们的乐队,何文同意了,她就是不肯。
余珏望望冰初姐。眼中有种叫苦恼的东东。
我说过一段时间她会同意的。
余珏说希望是吧。
冰初姐离不开音乐,她会的。我说。
我知道,可是她现在这个样子叫人担心,音乐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余珏丢下笔说。全身的重量靠在椅背上,望向天花板。他该不会是指冰初姐有可能患上歇斯底里症吧!我恐怖地看看冰初姐,她瘦瘦的脸颊好像被抽去了灵魂。不是,是她的灵魂化作了美妙动听的音符。韩若你可别胡思乱想。我对自己说。
我说你怎么不劝冰初姐,她只听你的。
余珏说这次不灵光了,她太要强了,不甘心失败的人是不听劝的,叫她随遇而安我没办法。
吉它声遽然停下,最后那一挑清音如湖面渐散的涟猗,一重一重涌着湖岸,冰初姐怔怔看着吉它,忽然间脸上出现了浓浓的倦意,我心想总不能就这样让冰初把不快郁结在心头,漫过界限后,她会像摔纸箱一样把何文心爱的吉它摔个七零八碎。我扯扯余珏,他立即会意。
“冰初,过来,让我数数你眼角是不是又多了几条我喜欢的小皱纹。”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