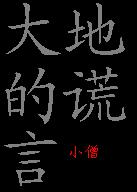���ԳDZ�-��40����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ĵ����������У����һ���ô�Ҳû�У����ȴ���ճ���������ۡ�������װ�����������հݷ����ùã����ùõļҲ������Ϸ�����·�Σ����ǰ���һ�磬��һ��С�Ӷ�����
���Ҷ�Ժ���̲����𣬷���ӵ�ء�һ�Ź��ϵ�ϸҶ����С���ౣ��ȳ��еĵİ������¶��ˣ�������������ʮ������Ұ�ԣ�������դ�л�ü���⾡ʧ�����һ����ľ������ϸС��ֱ������С���������ܣ��ر��Ƕ㿪�˳��еķ��ӣ���һ����ɽ��ˮ�Ե����ֵĹ����š�
������ʰ�øɸɾ����ķ�������˼����˶����յ�����Ũ��Ժ��������һ����������������������ŵ��صĵ���־���������һЩ��������ɽ�����ϡ����պ�����С���ã�����һ������������С��������һ���Ȼ����С�����������һ������ɽ�ĵ�ɽ��·ͼ�����������Ƿ���һλ����Ѱ�ü�λ�����Ϲ����Ʒ���ˣ����ʱ���æ��Ҫ����ԩ��·����·����ס�ˣ����Ӳҡ�������·ͼ�����е�����ӭ�ж��⡣
��·ͼ��ϸ�������е�Ծ����õ��Dz�ֽ����ɽ�ſ�ʼÿһ��������ÿһ��Ϫ������ǵ��������������Ȧ����������Ӫ�췹�ĵص㣬һֱ�����ζ�ǧ�࣬��˵�����ֲ������ˣ����ã�����һ�����ء��ڵ�ɽ��·����ʼ����һ��ͨ��Ͽ��ɽ´��·��������ɽ����ɽׯ�������ֱ�ӡ���ر�����������ף�������·ͼҲ��ʱ�����������Ȼ���εIJ������ר��Ϊ���Ʒ�������˲����ࡣ
����͵͵�����ң���������ǽ�ڵ�����ɽׯ�ܱ����������������������ʱ���ȱ�ڣ���ն���࣬����ͬ���ķ�����
���չù�һ���˺���ͣ�Ҳ�����飬���������Ǽ�ס��һҹ��һ���������Թ���ͣ�����ԭ�ƻ����Ž�ڴҴҶ�ȥ��
�����õ꣬�������ң����ϵ�ɽѥ��������������������ơ������һ�£�����˵Ϊ����������̽�ռҵ�����ɱ�����ЦЦ˵��Ҳ����һ������վ�������������ң�������ϵĻ���ɽ��˵��仰����������£�����һ��׳ʿ��ȥ����Ŀ�IJ����ݵĺ�����
�߳����ţ���ֹ�����ͳ���öӲ�ң���һö�����ա���˵����������гɹ�����֮��ʧ�ܡ���Ӳ��ƽ����Ĵָ��ָ���ϣ���סʳָ��ͷû�أ�����һ�����������������������������ʱ���Ķ����������յ�Ӳ�ҽ�������غ�����������ڼž��������������ղ�����û�ؿ��������ּ�⡣������॰������ϣ��ɹ��ֻ���ʧ�ܡ������ǿ���ʱ��̤�뷿����ʱ����ȥ��������ڤڤ�еĵ�ָʾ�ɣ�
������ֻ���˶�ʤ�죬û�����찲�ŵ����ˡ�
����ɽɽ���dz��е���Ϊ��ʡ�����������һ��ǰ������ɽׯ��˳·��������ɽ��ʡ����Ȼ��������·���洦�ɼ���ʾ�ơ���·�ڣ������������˳���
����ɭɭ������δɢ��Ҫ��Ҷ����ľ����Ʈ�������¶���ʪ����ɽ�ĵ�һ��·���������ģ���ɫ��ʯΪ�ף�̤ĥ����⣬��ɫ��֦��ҶΪ�ǣ�й�²���Ŀ��⣬��ϧ���������Ҽ��Ÿ�·��˫��ֻ�ܶ��Žż��ǰ�������ң������ʵǾ������͵��ķ羰��̫���˵�Ŀ��Ѳ����̾�ˣ��ں�����Ϊ��մմ��ϲ����������������ӹӹ�ĸо�������ſ�˫��վ�����Ʒ��ϣ��Dz���������ս�������ϲ�ã����羰������Ϊ�Ƿ�ϲ�ö��������ѡ�
�����������ձ��뾡���ܵ���ִ�嶥�����������������Щ������������ѵõĻ��������ź������Ǹ����ص�Ը��Ҳ��ȥʵ�֡�
��������ɽ�룬·�������ͣ���ׯ������û�ں�ɽ���£�һֱҧ����֣����˽�������Сʱ��������һ��������ЪϢ��ж�����������صı��ң����������������Ĵ��ȣ����տ������溹ˮ���ҷ�����Ц���Ҷ���ˮ�еĵ�Ӱ��Ҳ������Ц��
��������·ͼ�����ﺣ���߰��ף���������ɽ������ɽ�ţ�Ҳ����һֱ����ֱ�����Ʒ�ԭɽ�ţ��������ǵ��ٶȣ�����Ҫ������Сʱ���������DZ���ִ�������о���·ͼ�������ﺣ��һǧ������������Ӧ���ں��ζ�ǧ�����Ǹ���Ӫ�ع�ҹ��Ҳ����˵�������������֮ǰҪ�ϵ��Ƕ������Ҿ�Ŀ����ֱ������������߷壬������Ŷ����Ϊ�����·����ȫ�������룬����ʮ�����Ұɣ����գ���ο���Ҫ�������ˡ���
��˭��˭���ұ���û������Ż�ȥ��������˵��
���ҿɴ�Ӧ����ʫ��Ҫ��һ�����˻�ȥ�ġ���
������������ˣ���˵����������𣿡�����ͣ�¶�ʯ�ӽ�ˮ̶�Ķ������ʡ�
�����ᣬ��Ϊ��һ��ȥ�������Ѷ����������������������ܼ������ˡ���
����һʱû�����⣬�ҳ������С���ϵ�ذ�ף�������·�Ե�����С�
�������������������ǣ������ˣ���Ҳ���������õġ������������ذ�ʯ�������ң�û���С�
��һ��������������������������������������һ����
����·�ɣ�����˵��������������ջ�������ƽ���߹������һ�������˼ҵ�С��ׯ�����������ˣ�����Ҳ����û����·������·���ϴ���ԭʼɭ����û·��ʱ��Ҫ���Կ��أ�����ջ����·���Ե���ľ���ܴ����ߴ���������û���ܶ�ɹ֮�ࡣ����һ��㱻�������ڽ��£�����ֲ�����˱仯����Ҷ����ľ���������ˡ�
��������ÿ��һ��������ľ���˵һ���ڼ�ֵ���һ��ɽ�룬Խ�����ְ���һ��Ŀ�궨�ڸ���һ��ɽ�롣����֪�����������ս��û��������Ȼ�������ʱ����������������ʧ�ܣ��������ھͲ����ˣ�����ʧ�ܵ���ζҲûƷ������
һ�ҷ�Ȫ����·ͼ�ϵ�һǧ������Ի��Ȫ��������ǰ�������շ·��˾���һ���ɱ���ȥ��
���ۣ����ڵ��ˣ�����ʤ���ˣ�������˦���������е������쿪��֫���������IJ��ϣ�һ��ҶƬ��������Ϊ����ס�����⣬ֻ�м���СС�İߵ��������ϵ�Ƥ�����档
����Ԥ�ƵĶ����˴���Сʱ�����ҿ�������Ц��˵����������״�����ٶȣ������֮ǰ�ִ��ǧ������Ӫ���Ʋ�������ˣ�ɽ��̫���ˡ���Ҳ������������ͻ�Ƽ���֮˵����Ȼ��ͻ�ƾͲ���ν֮�����ˡ�
��ΪΪ�˾������Ḻ�أ�����û�д����ߣ�ʳƷȫ��ѹ����ʳ������֮�࣬������һЩ��ͷ��
�������ұ����ӵ�Ⱥɽ��Χ����Ŀ���Dz���ɫ��Ψ��տ���IJ����������ɽ����ΰ������ι����С�Ƕ���֮�����ڷ�ͷ��������Ϣ�������ҿ���·ͼ��Խ���ò��Ծ���������Զ���۲���һ��������ƽΡ�������֪���Լ����ˣ��Dz��������壬�����Ͼ��ܿ�����ֱ����ʵ�������ʵ�ǡ������塱������3113�����Ʒ廹�����ı�������ߣ������߳�������������ʮһ�ס�
���Ʒ��ֶ���һ�����أ�����������һ�֣��а�����������������
��·ͼԽ���Ͻ�˵��Խ������������ܻ����кܶ�羰���ĵĵط����ٴ����ǰ��������������Ȫ��ʹ������˸��衣Ȫˮ�Ǵӵ��ɶ�ߵ�ʯ�����к���µġ�����վ��ˮ�⻬�Ķ���ʯ�ϣ���ƾˮ������ͷ��������һ��������ˮ������˵��·Ҫ����Ҫ̫����ˮ�����ᡣ������������û������һ���������¿��ţ���������ϴԡͼ��������������Ҫ�������ʡ�
��ô�ߵ�ɽ���ǵ�һ������ɽ��ܴ�Ҳ���䣬˥�ԵIJݱ��������ض��������⣬�о�����̫�����¶ȡ����Ǻ���һǧ��ʱ�Ҷ�����˵�Ļ�����ʱ���������齵������͵㣬ֻ���Һ����������ظ��źܳ�һ��ʱ��Ҳ�Ѽ������������Ҳ����Լ������е����棬����������������������ڻ�����û�еĸ�ɽ�ϴ��У�̫�µ��ˡ�
��ǧ���ټƶ�����˵�����������������ʫ������Ц������û����Ȥ�������Ǿͳ��裬BEYOND�ġ��忪һ�С��������ǡ���ʯ���ֶӵġ��żŽ�ͷ�������������ɫ��������Blue��Star�ġ���˵�뿪��������ͱ�����ĸ�����û�нӴ����������ҳ�������ʱҲ�ɺ䡣
������˵��ɽ�ϵ�����Ī����ܣ����������������ˣ�ʮ��ʱ���ղŻ���Ӳӵ�̫����һ����ͱ�ɽ���ʪ����û��һ�����̣�ʱ��ʱû��ʪ���Ǵ�ɽ�״������ģ�����������ɢ����ëë�꣬��ëë���ܣ������������ϵģ��ם����ģ����߳岻��һ��СС��ɽ���ķ�Χ������������ɽ���ϣ����Ϻ����������ڼ����ʪ������ţ�ʱԶʱ������ؼ�ֻʣ��������Ϊ���ĵ�һ��ξ���������
���ɾ��������վ�̾�š����Ž����Ȧ������������
������������������ô����ϲ����ɽ����ɽ�Ǹ���ڣ����ܲ���������Ŀ�ģ����������Ȼ�����档����վ�ڴ��������泯ɽ�£�ʪʪ��ˮ����ɽ�������˵��ӹ��ҵ����������ҵ��ֱۻ����ҵľ��䣬�·��Ĺ����͡�ͷ������ϵIJ�һ���������չ��˫�ۣ������ۣ�ӭ������������磻��һ�̣��Ҹ��ܵ���ʲô�г��ѡ�
������ķ羰���Ƿ���֮�������˵�������������ǰ·��
�������ǻ���ʲô����������ģ���������ģ���
�������Ҵ�����һ��СС���漣��ʮ�˵��������ɹ����ҵ����Ǹ��������Ӫ�أ��ܸм���������ס�����ǵ�����Ҳ��ס������ɽ�Dz��ɳ�Խ�����ƣ��������������˵���С�ĸ�̾�����羰��һֱ����������ǰ��ǰ�С�������������Ŀ���ݣ����DZ���ȥ���������̽�������������������������ǰ�������������ҡ�
�ſ������¶����������������������߳��ҩ�ۣ��ֵ���Զ�����뽧ȡ��ˮ��������·ͼ�����һ����������Ӫ�أ����������ȣ�������������ʵ������·ͼ��ע���˴��Dz�������ġ���������������ȡů�ļƻ���գ���������·ͼ����ô˵���ž����ˣ�����ʪ��̫�أ���ľ������ˮ�֣�ȼ��������
�ѵ�������ʪ���д����ʪ��ѥ�ӣ��������Ҷ���˸���ů�͵������У���ſ����ͷ�����档���е�ѹ������ҧ��ɳɳ�죬��ɫ�����������Ӽ�����֪����Ļ����ʪ��ѹ���Ͽգ�������������������������ˡ�
�������������Dz��ǹ��ģ��������ܵ���ط�����������˵��
�������ˣ���
���Ų��أ����ﻹû��ԭʼɭ����ô�ֲ����þ��ɣ�Ҫ��һ��������ҲԸ�⡣��
������˵�ջ��ɣ���Щ�º�ֻ��ͣ����ż��һ�ε������ϣ�����������У��������ֵġ���
���Ҳ����Ǹ���˼������˵����ͦ���ġ���ϧ̫�����ˣ������ڳ��н����������³��ö�ð���Ҳ������ô���ࡣ��
�������ҿɲ�ϲ������һȺȺ���м俴�羰��������ȥ�������ˡ���ʱ���˱��������ɶ����Ҿ���Ҫ˵���˵Ļ����ˣ����Դ�ס��
�������ҽ�㣬�������������б�һһ�������ң����Ƕ�������ͺ��ˣ���ô�����ĵط����Ǵ����ˣ�����ȴ�����ˡ���
�Һȿ�ˮ����������˯����
��ι����������������˵���أ���ô���˯�������սе������컹û�ڣ����һ�������
����û����Ϧ�����ÿ����ڷ嶥�������㾫���������֪��ʲô��û����˵���ˡ����Ҵ��Ź�Ƿ˵������ɷ������ˡ�
�����죬�����������Ǿ�����ߵĵط����ճ���������Ҳ������˯����
û��ԭʼɭ����ҹ�ɵĿ���û�г����ܽУ�ֻ�з紵�����ĺ�����������һ������ô�ľ���������˯���ˣ��Ⲣ�����ѣ�ԭʼɭ���е������ҹ��Ҫ˵�ֲ��������̹��ˡ����ң��������Ҳ����������������ˡ�ɽ������ֱij����Ż��ˡ����붼û�롣
һ���꾪���˹���������һ�������ͣ�ˡ���ɽ��������IJ���˼�飬�˾���֮��˵����ꡣ�ҿ�һ�۱��������賿��ʱһ�̡��������������գ�����˯û�л�Ӧ�����Ѻ�һֱ˯���ţ�����������˯���˴�����Ϣ���˰ɣ���˯�����������˽����Сʱ���ͳ����ʵ�С������ںڰ��������ʹ����������¶ȡ����ԴӸ���ʱ���³�״̬Խ�����ѣ������������������ֵ�Ͳ������ѥ�ӣ��Ӽ����ף��ͳ�������
��ͣЪ�ܾ��ˣ�����������û��ɢ��������ϡ�ɱ�Զ��ɽ���ĺ�Ӱ�ͽ��²ݴԵĴ���ģ���������Ǻ���Ρ��ĵط���������ٵ�Ҳ�硣���쵽���ʱ��Ϊ���ĵ�ƣ��������û���Ĵ����ߣ�ɽ���϶��Dz�ԭ���������Ų�����һ��������ȥ����û����ϥ�ǣ�����ȥͦ�����ģ�ֻ��ʪʪ�Ľ����е���ľ���䡣��ɽ���²���������Ԥ���˱�ů����������������������ֱ����ǰ�ߡ�
���뵽���Ƶ����ᣬ�����ͳ���̸���������ľִ١��Ƶ�����˵����һֻ���꣬�������ų����Ŀǣ����ڵĿռ�����С�ģ������겻��û�������������������Ϊ�Ǹ��ض���������ͬʱҲ�Ǻ�����������ᣬ������Ҹ�������Ϊ����ôһ�������Ŀǣ�Σ��ʱ���Զ��ȥ����Ϸˮʱ���Ա������������������
�ҵ�ʱ���ŷ������ⷬ��������˵���е�����ҵ��������������������������Ĵ��ۡ���ɥ�����գ������������ף�Ҳ���Ǹ������Ĺ�ǣ���ʵ�������������������û�в�ȱ������ȴ�Dz�ȱ��
������ʱ˵�úܼᶨ���Ƶ������֪�����dz�����Ϊ�ҿ��ѡ�
��վ�ڸ����Ͼ�Ĭһ�����һ�����������س�������������յ����ϱ���紵����¶��һ�����������ȱ�ڣ�˲Ϣ���������ˡ�
�����ȣ������Ĺ���ô��
�ȵ�������������������������غ����ҵ����֡�
�����������������Ķ�����
����ƽ�գ�����һ����˵���������Ķ��ˣ������˼�����ĵط�������Ҳ��ɡ���������֡�
�Ұ�СĴָ�Ž����У�����һ���������ߵĿ��ڣ������һ��Ѹ��Զȥ���ӹ���ԭ��������
�����ߣ���;�������˴ҴҶ��������ա�
����ô��ͳ������뼱����ѽ��������˵����˫�ֲ嶵��ǰ����ҡ�
����˯���ţ�����ôҲ�����ˣ���
��һ�����������㲻�ڣ�����˯�����𣿺��䰡����
������ȥ˯�𣿡�
�������ˣ�˯���ˣ�����һ���¾�˯���ˡ���
�����أ������𣿡�
����һ��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