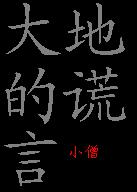谎言城堡-第5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就不得不佩服他们的精明,我更加忐忑不安。
蛋筒卷离开去买烟。
圆脸突然对我冒出一句说小兄弟你太聪明了,聪明过了头。我说我若真的那么聪明就能猜出你们带我到这儿究竟是为了什么。圆脸哈哈一笑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也是你的聪明招惹来的点点麻烦吧。
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说。
是的,因为你用错了地方。圆脸说。
我说我从不后悔我自己做过的。圆脸说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但你们却又想反,两种不同的自负吧,而你不是他的对手。我问为什么。圆脸抬腕看看表说因为你有时太幼稚了,坐车从这到你们学校我们只用了二下五分钟,而回来致函用了将近三十五分钟,这是你带的路,你看出了我们不是这儿的人,可是司机的计价器没坏,却比来时多付了十多元钱,第三,来的路上我观察了楼房投下的阴影太阳的位置,先在右后在左。持续时间都很长,也就是说你叫司机原地打圈子,可惜那个司机是个呆瓜。说完,圆脸大笑起来。
我脸上火辣辣的,问他当时干嘛不点穿。
圆脸说我那位兄弟的脾气不好不懂待客之道,也没必要,反正是邀你玩儿的,我们又不是黑道上的混蛋,专干遭警察追杀的事。
我耳根更加烫了,有点无地自容,觉得先前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他们想得太坏了。卞一一上午气我的话对,我太自以为是了。
圆脸说我还有一样东西给你,是你下车掉在车上的,以后要小心,要是当街掉纸片警察以为你在丢垃圾就得买罚单了。
他中指夹着一张纸片在我眼前晃一晃,我骨子里的傲气顿时矮了半截,SOS校徽在圆脸的指间的出现陡然增加了我面部的压强,似乎在从毛孔中迸溢出,耳根温度急剧上升,有点担心会不会烧着头发,我若无其事地接过校徽撕成碎片丢在了脚下。
圆脸说动物界是弱肉强食,人们是尔虞我诈,但你玩不过我们的。
我平静地说我输了,可我相信没有人会永远输下去。圆脸说好,你放心吧!每个人都有输的时候,人们总是给输的一方最大的同情的。
圆脸与蛋筒卷带我到一家生意冷清的旅馆,阴暗逼仄,径直上了楼,我没有了见机就溜的念头,他们也没挟迫我上的味道,从圆面积脸刚才的态度来看,好像并没有不妥的事等我。蛋筒卷瞅瞅后面见跟了人没有,敲了敲一个房间的门,里面传来了匆忙的脚步声,椐我在医院闲来无事听音辨人的经验,应该是两个跟圆脸他们差不多的人。圆脸掏出一条黑布说小兄弟委屈你一下,我那些朋友很害羞的。
我的信任被他的笑脸推下了悬崖,化作齑粉。
眼睛蒙住了的我在门打开后双手被反扭到背颈,接着肚子上被踢了两脚,脸上挨了两巴掌。他们狠狠的踹我后膝,但他们的试图并没有成功,我咬牙单膝碰地,始终不让另一只膝盖触碰尊严的大地。圆脸还有点人性,扶住了我,对施以毒手的人说别打了,等铭哥来再打他也不迟。打我的人才停了手,一个说没想到真是个嫩小子,胆挺大的。另一个抬起我的下颔说你以为你是谁,几斤几两,有我受的。我甩头摆脱那只令人作哎的手。作为这个不服气的回报,我肚子又被踹了一脚,耳朵被扇得嗡咐发响。
我承受疼痛的思维猜到了这几人可能的身份,但朦朦胧胧的不太确定,他们好像不愿让我知道他们所为何事为难我。口风紧紧的,这不是绑架勒索,完全是一种报复的快意,失败的一方总是对胜利的一方施加拳脚才能维持心理衡。他们不怕我大声呼救,用他们的话说,只要三秒钟就可以让我的声音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我不是英雄,听从了他们,但我还是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打我的人气得直跺脚骂我是不是哑巴,手打痛了都不哼一声。蛋筒卷似乎在金盆里洗了手,来这儿一直没沾我,这时他对打我的那两人说骂人别用国语,英文这小子才听得懂。一个人说蛋筒卷你不是物喜欢海扁人吗?今天怎么怕脏手了?蛋筒卷说Fuck you我跟月不缺早揍了他,全内伤,现在没兴趣了。
那人又问我Fucking are you hummy?
我说I don‘t fllow you;America dog 。结果又被他打了一顿,是的,叫他用英文骂人,他跟我来纯英文,忍不住嘲弄他,换来的是脚加拳踢。
他们要我反抱着一根水泥柱子,用绳子捆紧了我的双手。圆脸说小兄弟对不住了,我也不想这样,可是谁让你染指铭哥的女朋友呢!圆脸忽觉得漏了口,马上闭了嘴,随后与蛋筒卷出去了,说是上街看看有没有尾巴,也就是风吹草动,放风。走前,他不忘对另两人说手下要留情。
我舔舔被打出了血的嘴角,口腔内满是血腥的甜味。梁铭,没错,一定是梁铭才如此歹毒。他找到了晨,所以我才会在这儿。失去萧叶茗的梁铭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不甘心。芷晴姐告诉了他晨的存在后他是如何的咬牙切齿。我开心地咽下一口和阗鲜血的唾沫。我之前嘴上虽不说,但内心亦跟萧稣一样对他素有敌意,可是在希望他是不是坏心肠上我摇摆不定。如果是,萧叶茗也许要到受尽伤痛后才离开他,这不是我私心的期待,事实证明他不是,只是性格不适合,我又希望这种不适合无法消除。从圆脸肯定我的推测的那一刻断开,之前我还有另一种认为,认为梁铭并不那么可恶,只是我,萧稣和芷晴姐深存的偏见在作祟,过份的贬低他,现在呢?却说明我太天真了,梁铭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我刚才身上受的每一拳,每一个耳光和每一脚都有他的恨意在里面,变态的残忍报复!连吓带蒙把我弄到这儿以及每一分痛楚和每一块於块都是他那些好哥们的杰作。
他们也只能拿我这样,我不需要向梁铭低头。想明白了前因后果我很是高兴,喜欢梁铭落败的样子,喜欢看他于事无补的气急败坏。他先于晨退出萧叶茗的心湖天空。萧叶茗挤出了晨为她编织的梦茧是带着幽怨不得已的情怀,逃出挣扎的泪水走开的。 梁铭与晨雨一生守候的女孩化作蝴蝶飞去。留给两人不同的舞姿,也许不再飞回来。此刻两人同痛相怜才对。我不禁心下可怜梁铭,还有自己。
我一直想见见这位玉树临风的医大才子,现在只有耐心地等,其实耐不耐心已由不得我了。我想即使见到了他,他也不会说他是梁铭的,否则,他们蒙我的眼睛干嘛?可能就是随随便便捏造个莫须有的借口再狠揍我一顿出出气便了结了。他们不知道我窥破了他们的虚实。假如我不认识萧叶茗和芷晴姐,我就算被他们打到只剩半条命想破脑袋也不可能想出是谁干的。他们找到的是晨,对我他们一无所知。
我暗地对自己说佩服佩服,在危局中还有如此清晰的逻辑思维,一切仿佛都被我揣摩得合情合理,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的出现更加肯定了我的推测。
我怀疑打我的人有多动症,手脚不动就难受,所以他们对我的肢体暴力没间断过,鼻子被打出了血。浓稠的血液决了堤,一个劲地往外流,滑过嘴唇落个不止,我仰头止血,血流窜进了后背,热乎乎的,黏乎乎的。我差点主立下毒咒,放我后一定把他们送进号子里,要他们为此付出应得的。可转念一想我从不起誓,更不能因为仇恨破坏原则,誓就免了。但侮辱了我跟我使坏我不会便宜你们的。我心中恨恨道。
在这座城市。除了晨雨还有一个人曾让梁铭如芒刺在背,那就是萧稣,一个像跟梁铭有宿怨的人,梁铭倒霉,不曾想到萧叶茗有这么一个毫不掩饰爱恨的弟弟,萧稣邮了几封信给梁铭,我看过,画了一只大蛤蟆,油料的,很强烈刺目的色彩,黄色作底,远看点有点像凡·;高的名作《向日葵》,还有乌龟,画得有点像京戏中的脸谱,有四肢有头就是没眼睛鼻子。萧稣说那是暗喻不要脸。最绝的是萧稣磊磊落落地痛斥梁铭,把梁铭说成一文不值只欲对他姐姐不轨。然后不忌不讳嘱笔自己的名字就寄了出去。我想梁想折开看时的脸特好看,像纸上的那只乌龟,花花绿绿的。
我一直站着,腿酸酸的。大概是夜色将至的时候,圆脸与蛋筒卷回来,他们旋开门锁时我听到了萧稣的声音,他在抗议眼睛被蒙住,大声问蓝诗祺在哪儿。蛋筒卷威胁说再大声点,小心你女朋友的纯洁。接着是一阵推搡的响动的衣服撕裂嘶嘶声。可能是萧稣拼命挣脱他们的控制想过去给威胁他的蛋筒卷一拳。但那是徒然的。萧稣显然考虑了后果,因为他没有大声喊强盗,他不得不考虑蓝诗祺的处境。他和我一样嘴没被堵上却比堵上更难受。圆脸他们给萧稣的见面礼不是一顿暴打,反而客客气气地要萧稣合作。萧稣毕竟是萧叶茗的弟弟,这是当然。
我看不到萧稣,萧稣也看不到柱子上狼狈的我,能把萧稣与晨的我在这种场合联系起来的只有梁铭了,一个星期前萧稣为蓝诗祺离校出走,萧叶茗匆忙赶回,想必梁铭打探到了。他只要略施小计,用蓝诗祺作诱饵就可以不需大费周章地把萧稣骗到这儿。爱情使人愚蠢。萧稣真是个呆子!
圆脸向萧稣坦白他们并没有拿蓝诗祺怎样。顺便给萧稣他们这么做的理由,说蓝诗祺本是他们老大的猎物,却先让萧稣拔了头筹,萧稣现在受点苦是罪有应得。可是他们忘了房间里还有一个正为他们说谎都是神来之笔喝彩的我。既然敢绑架还遮遮掩掩干嘛,这可是宵小的行为呀!怕事后法律追究也不用花这么多心机。别作声,在暗角落里冷不丁窜出来暴虐一顿后扬长而去不是更好吗?嗯,不过,解气的效果好像……好像是没那么好。
其实他们先该把我的底细查清楚,竟然漏了萧稣与我是最好朋友这一关键至乎成败的信息。他们想演一出戏,我是他们选中的主角,可现在呢?我是台下的观众,他们在台上跳来蹦去说着笨拙的台词做着滑稽的动作,洋洋自得以为天衣无缝,那知是无缝天衣,穿都没法穿。蔽羞都不行。天下没白看的戏,我也要买门票,所以动不动就被揍得鲜血直流算抵了门票。台上玩的是瞒天过海的魔术,玩魔术的人是最忌别人揭底的,弄不好羞恼成怒我怕承受不了,所以尽管萧稣在我面前咫尺,我还是镇定地装不认识,从头到尾也不说一句话。只要圆脸他们没发现我对他们小丑般的表演了如指掌我就可以继续看戏,而且不会有太坏的后果出现。
圆脸他们用对我的那一手防止了萧稣的高音,萧鲧不是胆小的人,没被肢体语言粗暴对待的他喋喋不休地跟圆脸理论,说什么你们无权干涉别人的恋爱自由。说他对蓝诗祺是真心的。假如圆脸说的是真的,这些话无疑是火上浇油。可是萧稣竟然没发觉圆脸对他的话爱理不理,根本不是关心的对象。后来萧稣被带往了另一个房间,与我一墙之隔。萧稣是自己走的,他不许圆脸他们拉扯。圆脸说左三步,他就左走三步,一个人说再左三步,萧稣就碰了墙壁,那几人就哈哈大笑,萧稣无谓,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总算保住了自己的高贵的尊严。
圆脸说把他关一夜给点教训就可以了。从他们的对话中我听出梁铭正在来的路上,应该是从医大赶来,我和身后冰冷的柱子亲密接触了够呛久了。二个小时吧!他们几人就玩起了桥牌,有筹码。蛋筒卷与圆脸中立不拿我出气,可是另两个人输了就怪罪于我,就要在我身上练空手道。
梁铭来时,萧稣在隔壁的房间里踢桌子,乒乒乓乓的,我不知他是否也有柱子或是床脚陪他。也许他是一个人太寂寞了,就跟桌子玩看谁痛的游戏。我想着乏味的幽默抵抗屈服的情绪,我怎么能低头呢!特别是在梁铭面前,韩若,你在最骄傲的血统,你听了《千叶湖畔的莺语》,如果屈服,就应该把耳朵割掉,因为低头的人不配听萧叶茗的天籁,你约了云淡风轻,低头,就该把敲字键的手指剁掉,因为心犀相近的深夜屈服的手指不配触摸。
我自言自语自为自打气。圆脸接了一个电话出去了一会儿,后带了两个人直房内。他们顾忌我耳朵没堵上,互相说着暗藏机锋的话。来人中便有一位是梁铭,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声音是属于魅力值很高的那种,飞扬拔扈,凸显成熟磁性。在我想象中他既然指使他的哥们千方百计请我到这,他见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本性尽露狂揍我,再慢慢羞辱折磨我,让我的双膝承担不了他的愤怒而碰地求他。可是他没有,拿纸巾擦掉我嘴角的血渍,亦没说打我的人不对。同情弱者?我扭头一边不接受他的好意。假惺惺干嘛?
“你叫韩若,市立十七中的学生,对吧?”
梁铭说。我感觉到他身上有一团凌人的气息。我不置可否。
“很高兴认识你,知道为什么我朋友对你有意见吗?有句话说的好,世上没有付出只有代价,你今天只是在代价你以前做过的事。”
我想梁名现在该编一个名正言顺且会误导我的理由。就像刚才萧稣的礼遇一样。
“你身上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回家养几天就好了,心被扎了才是痛,你尝过那种滋味没有?背叛!耻辱!”梁铭一拳飞到我的左脸颊,“你最爱的人离你而去,伤心的是谁?那种只有自己才知道痛多深的感觉你有过没有?这么多天过去了,伤口依然是新鲜的,还有滴血,想一次心死一次,这就是爱一个人无法自拔的代价,你体验过没有?”
又一拳飞往我的右脸颊,这是梁铭吗?他干嘛说这些?为爱责难一个人我愿意承受他的暴力。可是,此刻的他,到底有多少真多少假?这不是梁铭,自负狂妄的人是永远不会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为爱憔悴的,何况我一不是他的朋友二不是他萍水相逢的陌路人,我是他的仇恨欲击碎的对象。
我迷惑了,脸庞上的痛仿佛也在迷惑。爱一个人,无怨无悔,当爱流去变成了曾经沧海的水,这份爱就一定会脱变成难灭的恨吗?就如爱那样真真切切的不顾一切?是不是许多年以后回想起爱无情破碎时的那一分秒,破碎的美丽的曾经洒满一地,划裂心口的第一滴彤艳的血仍像刚刚坠地?所以那份由爱的温床萌生的恨即使风吹烟散后依旧一触即发?
梁铭夹着愤怒的连问和挥拳的力度告诉我他对晨雨的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