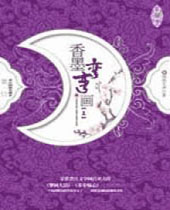香墨弯弯画by悄然无声-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封旭大睁着眼着孩子倒在自己面前,眼中的泪终于落了下来,
微微一滴。
半晌
又是一滴。
待到司徒府里已经声息全无时,封旭仰首看着门上龙飞凤舞金额大匾,仍是初见时的流光溢彩,缓缓道:“总得有个罪名,记得我朝有律法明文,商人不得穿苎罗绸缎。是不是,李参将?”
李佐慌忙应是。
封旭眼又从匾额上滑过,无甚痕迹。
“把这匾额给摘了吧。”
口气仍旧是满含了哀伤,从旁待立的士兵急忙闻言而动,寻来梯子将匾摘下,砍成了几节。
回到肯斯城,陈瑞如深潭般的眼睛狠狠的瞪着封旭,第一句便是:“奇笨无比的法子。”
语气严厉,眼底却不见有丝毫怒意。
封旭低眉顺眼的一笑:“将军教过,最笨的法子,往往是最有用的。”
十二月的东都,西北和穆燕的战报,捷讯连连,又赶上了连着几日的大雪,人人皆道是天降的祥瑞。而隐在这祥瑞之后的,却是地隘关司徒家的灭门和西北愈来愈盛的“青王”传言。
初九这日,下了几日的雪丝毫没有止住的迹象。
日水熔金的西厅,虽是白日,但因天色阴暗,七座塔灯,都点齐了。轩窗反常的全部开启,雪色进了满厅,不远处就可见条条圆木铺成的一组九曲十八弯的木桥,铺满了雪,弯弯曲曲如一条玉带跨在玉湖之上。
香墨在这里邀了杜子溪品茶。
因窗户打开,即便门扉处挂了灰鼠暖帘,还是冷的迫人。榻上设几,铺了两副裳褥,锦绣光华中两人围炉而坐。
杜子溪将烹好的茶自己斟上一杯,端在手里,并不饮,只问:“什么茶?”
时有雪片降在屋中,一旁瓶中的插满刚摘的梅花,有几瓣禁不住风落在地上,点着桃花胭脂一般。
香墨轻笑道:“说是茶,其实知道娘娘服药,所以就拿梅花晾干了,和了蜜酿的。”
“梅味冷冽,性寒,入口清爽。”
翡翠杯,琥珀色,梅香浅浅,偏清甜撩人。杜子溪好兴致的连啜了几口,笑道:“饮香醪,看雪梅,倒是人生快事。”
“娘娘也别高兴的太早。”
语时,眼波斜斜扫过杜子溪。
杜子溪心里便很不受用,不过到底还是经的事多了,面上仍掩饰得半点不留痕迹。
香墨轻笑:“一会儿娘娘会更畅快的。”
今日的她极随便的挽了一个发髻,不过用一根金簪固定,故一笑之间竟有别样的风情。
此时雪益大、风益冷,花气越香,绕在呼吸唇齿间,细腻融润,沁香入脾。
远处,那弯弯曲曲的桥上,一行人青毡套衣,戴着青毡斗筲,缓缓慢行,宛然一簇青花绽在水晶盘里。
香墨指与杜子溪海棠看:“瞧,魏贵嫔他们要给太后请安去了。”
说时,仍是止不住的笑,月白衣袖上隐绣着月白色的翎纹,唯起伏之间才能现个仔细。
杜子溪眼一眯,才放目望去。
青油伞下,一个妇人抱着婴儿,极小心翼翼的走着。妇人的前面不远,趾高气昂的宫装艳姝,正是新晋了贵嫔的魏氏。
桥上的一个转弯处,弯角紧窄,如刀削一般,仅仅能一人行走。前面几名内侍相继过去之后,奶娘踏步的瞬间,那段木板便断了,奶娘抱着皇长子站脚不住,便和柳絮似的随风掉了下去。已经冰封的玉湖,可巧就这一段有一个凿开的窟窿,雪压着,所以一时没看见。奶娘和皇长子坠透了积雪,就掉了进去,在碧澄澄的一泓水的挣扎了几下,零零落落虫儿似的几声厮叫,之后就再也没有浮上来。
只余下水面泛起一圈涟漪,
已过了桥的魏贵嫔愣了,好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半晌才尖叫着扑了回来,那只手从破了的朱红栏杆伸出,魏紫的袖直沿到断桥处栏杆外,空抓着,哀嚎着。
杜子溪禁不住把脸贴近窗口,听着那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一激灵,手中的梅花酿也泼了一些。半晌,狠狠道:“要是我自己的孩子,指定就随着跳下去了,才不会没用在那干嚎!”
说话间,又赶过来几名内侍,三两下扯了外衫,一手去了风帽丢在栏杆上,先后跳进了冰窟窿。
杜子溪眉头皱起,生出几分烦燥来:“还真有那不怕死的……好似康慈宫的,难怪……”
香墨一手套着个元绒缀水钻花苏式的双穗袖笼,一手拿双铜筷子,在熏笼内不急不缓的拨灰:“娘娘别急,这么冷的天,大人跳下去及时捞上来的话,还得去了半条命。”
雪下得更大了,忽又是一阵风,吹进窗子来,烛光影影憧憧,笼着雾似的晃着。魏贵嫔的声音,魆魆的,一声赛过一声好像鬼叫一般。
香墨身上穿一件皮袄子,罩上一件四盖出锋的紫貂背心,本极暖和,可此时仿佛觉得风刮在身上,透骨似的,不由侧了一侧脸,才道:“才两个月的孩子,准保是没命了。”
窗外,曲桥上,落雪如银箭。
好一阵子,内侍打捞了一团冻僵了东西上来。
她们隐隐约约的可以看见,小小的孩子,手指尖处已被冻得绿中含了紫青,犹自向上伸着,仿佛求救似的。
魏贵嫔此时紧紧抱着孩子,哭都哭不出来歪倒在断桥上,眼角的泪痕,被雪光耀的发亮。
一边丽女官不待杜子溪发话就转身出去了,不多时回来奏道:“回娘娘,没气了。”
风催着烈红的烛火,逐渐在阴霾天光下昏暗。
杜子溪微眯眼,将久久握着的翡翠杯搁回桌面,半垂着头,面前一杯梅花酿已然凉透,幽幽的浮着她轻笑的样貌。
“还是夫人聪明,太后防的滴水不露,你就提醒我借着晋封的法子,让她迁出康慈宫。”
抬脸时深黑的双眸里如幽潭一般盯着香墨:“话说回来 ,她要是不迁出来,我们还真是没有地方下手。”
声音轻得恍如一丝阴风,刺的香墨望住杜子溪。
彼此的眼中俱是烛影,幽幽的一层彤气。
片刻之后,香墨一字一句道:“娘娘何尝不是聪明人。”
然后,方才察觉月白的袖子上落了雪,忙抖净了,仍有几点沾湿了,冰寒的沁到了骨血里。
“魏贵嫔的永安宫,离着康慈宫即不那么远,也不那么近,偏巧又得穿过这玉湖……”
风仍是寒峭,杜子溪似是冷了,伸手把紫貂大氅往身上拢了拢。然月余之前的紫貂,如今也即宽且大,灿金纹线,瓴羽的眼纹,仍是渲了个半榻,锦花颓丧后的枯亵。衣袖之间露出白如温玉的一段手腕,竟是愈看愈有股子枯干的味道
此时日水熔金深掩无声,满瓶的梅,有的开了,有的未开,有的已谢了。
梅花摇曳,梅本无心。
扑漱漱落在屋内乌砖上雪,一片一片的腐化。
窗外的哭声,枭鸟般嘶呜,最终万物皆寂静。
曲桥上那一抹魏紫衣,在漫天的飞雪之中染开了般,泾渭不明,晦涩迷离。
转
几刻钟后,康慈宫内闻讯的李太后,身子一歪,伏在榻上一口气几乎喘不上来。惊得小青和李嬷嬷一人一边,慌忙帮她揉着后心,却都被狠狠挥开。
封荣头戴金冠,身披绛罗袍,坐于一边的榻上,手持碧玉环抛上抛下。
睡鸭金炉已是半凉了,那一抹龙涎方才燃尽,暗香烟丝,弥漫在华殿内。碧玉环晃晃的反出一层光,幽幽通透。
黄金有价玉无价,一看便是知是千金难求的珍宝,而他便只这么于手中上下颠着,挑眉挑眼的笑说:“真可惜,很好玩的娃娃呢。”
陈史记载:封帝皇长子降生月余,始终未得帝赐名。死后草赐封号,青。
夜半醒来时,窗外雪落不止,浠浠漓漓。
一幕流紫的帐外,始终燃着一盏烛,烛光摇曳,带着淡淡的红。
好半晌,封荣才觉出自己是在绿萼轩内。
窗不知何时仍是半开了,一阵寒凉的夜风吹了个透心,枕函如水衾如铁,不过是片刻功夫,已然是冻了个透心。
翻转了身,身侧的香墨不知何时早已坐起身,解散了发,冷掉的烛光细细揉在发上。帐上绣的牡丹,斜斜被描在她赤裸的胸前,如同淡墨纹身。
而那纹身轻颤着。
初时,封荣以为是床帐在动,细看了才看清,是香墨在哭。
闭着眼,锁紧的眉眼,泪流不止。
一下子就老了十岁一般。
风吹过,飒飒的音,愈发的透着寒气,
封荣有悄悄翻身重又闭上眼,人枕在枕头上时间长了便有些昏沉沉的。
身侧的人仍在悄悄的无声的哭泣着,如风中的竹,瑟瑟轻颤。
一切,恍然如梦。
初十这日,雪仍旧下的极大。
杜铭溪打了伞,站在曲桥上,一站就是良久。
随侍的宫婢俱都被冻僵了,但都不敢上前去劝说。
从这里望去,大陈宫一色连绵的明黄琉璃瓦,俱都被雪埋了,桥下的玉湖同样被雪埋了,漫天漫地银装素裹又有多少香鬓影花被埋没,她不敢想,只是不寒而栗。
陡地,杜铭溪扯下来自己的斗篷,扔在了地上。又扯下来自己的衣衫,扔了出去。
风极大,如意牡丹锦的外衫极轻,这种锦绣无论怎样堆绣,都只用胭脂、紫、绿、蓝四色,娇嫩的可以滴出水来,顺风飞去,缠绵于风间,长袖流水,波浪涟漪。
望着消失在大雪间外衫,不同于大惊失色的宫婢,杜铭溪心中说不出的畅快。
人人皆道她疯了,那么她便是疯了。
其实,一切的开始都是在这里牢狱般的皇宫,如果不曾进来这座宫殿,也许一切将会不同。
不过,这只是如果而已。
杜铭溪抬起头,天上一轮明日掩在风雪里,黯然失色。
只着了雪白内衫的她大笑,雪冲进了嗓子几乎呛的她喘不过气。无人看着时,闭上眼睛,总是有心头一黯的酸楚涌上眼睛。
然后,以泪洗面。
陡然,天空响起了沉闷的雷声。一下又一下。在宫婢的惊叫声中,回过身来,锦绣翻飞,她的视线里一片白,在封荣站在桥的另一侧,与她相望。
即便满面惊慌,仍是如芝兰玉树一般。
封荣紧裹住自己的,正是她那件如意牡丹锦的外衫。
一瞬间,九重惊雷,骇浪般又落了下来。
杜铭溪心口端的一惊,只得上前一步,强自镇定行礼。
封荣却比她更惊慌的冲进了她的怀中,攀住她的颈项。彻骨寒气起来让杜铭溪又咳了起来,头上虚虚实实的如意牡丹锦,胭脂、紫、绿、蓝揉在一处,和着风雪落雷如巨大的翼,飞扬在上。
宫婢们反倒不再惊慌失措,而是含着暧昧的笑,将他们引致了一处偏殿。随即,将整个殿阁的窗都关了起来,无声的消失。
封荣一直在杜铭溪怀中颤抖着,受了惊一般。过了很久,久到雪已经停了。
他们就坐在地上,封荣紧紧抱住杜铭溪的腰,趴伏在她的膝上。
冬日里,向来听闻不到什么鸟鸣声,倒是风吹过的时候还会扑漱漱的落下残雪来,婆娑的沙沙声响。透过镂雕了梅花的窗,满殿雪色。
杜铭溪垂眼看着孩子似肆意的皇帝,挑起来的眉眼间,有一丝疲惫的影子。
“陛下为什么害怕打雷呢?”
这么问时,她的声音带了连自己也不觉察的温柔。
封荣一愣,神色瞬间柔和。
回忆一经带起就犹如波浪,一重高过一重,不可抑制。
曾几何时,也有人这样抱住他,也是这样淡薄湿透的衣衫,紧紧却温存。明亮的好似在燃烧似的一双眼,让他藏在心底的喜悦和爱慕,一丝一缕的渗出。
只是如今,今非昔比。
封荣脸庞染上胭脂似的红,眼神迷蒙将醒未醒般,微抬起身来,衣衫便滑下,露出一段白皙脖颈,道:“我喜欢你。”
杜铭溪踧踖不妨,双颊染上一阵潮热,如九染的锦纱,挑起来,落下绯色。
垂眼时,仍是桃花一样的明眸,灼灼的,俊美的脸庞上依稀有些哀伤的痕迹。
“可是,你为什么不开心?”
“我还记得你的笑,开心肆意。”
“如今却很少见到了。”
“为什么?”
“我没能让你开心吗?”
封荣笑不改色,一句又一句,丝毫没给杜铭溪喘息的时间。
说他糊涂,眼睛却透亮近似犀利,与她相望。
杜铭溪颤动的心弦,好似商调反弹错了羽调,嘎然而止。
那一声接一声说于人听的,终究不是她。
盯着窗外的香樟倒过来的影,黑煞煞的从紧闭的窗子后,一点一滴的挤压过来,压得她无法呼吸。
一滴泪就如一朵霜花,凝结在了杜铭溪眼中。
在她膝间扬起头的封荣,仍在温柔的自顾自的絮絮地言语:“我不是已经封赏了很多了吗?我不是已经处处顺着你的意了吗?你应该没有什么不开心的。”
然后,粲然一笑,道:“对吗?”
本就不是在问她,所以也不需她的回答,就又静静趴在她的膝上。
内衫极薄,呼吸一下又一下轻易透过,吐在肌肤上,烫的杜铭溪眼睑一跳,含在眼中许久的那滴泪终于落了下来。从薄薄的白色内衫,流淌如墨化开,一点一点的洇湿白裙。
手抚上了封荣的发鬓,轻轻地、柔柔地摸索着,他再次茫然抬起头,迷蒙着眼。
朝去暮来时的雪光仍盛,自窗花缱绻而入,轻飘飘地在眼中散开,染着了黄昏。
封荣眸子掠过一丝迷茫,欲细看时,眼却被蒙住了。
即便如此,封荣还是不解的眨着眼。睫毛在杜铭溪的指下,如蜓虫颤动透明的翅。
杜铭溪俯身吻上了面前人冰冷的唇。
好似一丝温软的风卷过,微温之时竟然幽幽散出花的香味。
朦胧时,香息幽彻,直如软纱,入口绵长。
似乎知道她在害怕一般,那唇呵着的热气带着宠溺的笑意。然后,封荣就反身将她压在了身下……
裙裾褪尽,在青砖上滑过,发出丝绸的声音
身下铺的是那件被她弃了,却被他拾起的如意牡丹锦外衫。
敞开的身体,柔软的任君采撷,碎而凌乱的发,垂在她的身上,和他的嘴唇一起。
高亢的呻吟里,手伸到了封荣的腕上,从套着玉镯的腕间到胳膊,一一点点抚摸着……
恨不得交融而死,窒息而死!
封荣是冷火,是燃烧人着。而她杜铭溪,在那火焰中无法自拔,甘心情愿被烧成灰烬。
雪落的声音很大,安静的,无法停止这种燃烧……
唯有清泪,缓缓流过眼角,被牡丹锦吸取而去……
这一梦极沉,再没有搅得骨都痛的寒,她心中无比舒适,只愿一直这样陷落下去,不再醒来。
然而,庄生梦蝶,终归要醒。
杜铭溪睁眼时,日落西山,满眼沉沉的乌黑。
呼吸间满是佳楠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