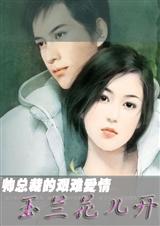花儿谢了-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进公司,就被派到了一个凭我的两条腿是走不回来的地方,可在地图上看,应该就在隔壁。
第一次听说她的名字就是在隔壁的一天午饭后。
那天,大鹏舔着他那油渍渍的嘴唇和我走在海边。
海风胡乱地吹着我那被刚才一阵海风吹乱的头发。
阳光将大鹏的镜片晒成一轮一轮的,大鹏就是透过这些绚丽的光圈凝视着前面那模糊的未来。
或许是未来实在太难看清,大鹏将眼光投到离他最近的我的脸上。
他看了好一会儿,这期间至少他自己认为还没能将自己的嘴唇弄干净。
也正是在那一刻,我确立了一项学说:人的眼光配合着舔嘴唇的声音可以在被照射物体表面产生热能。
“你现在的样子有点象一个人。”大鹏的舌头终于可以用来说话了。
根据刚才的经验,他的舌头是不会轻易停下的,于是我等着他的下一句。
“真的象,发型也象。”
我有些奇怪,因为当时的头发除了比一般男性的头发长以外,其他实在是无型可言。
也许无型就是一种型吧。
但这么高深的道理,以他的长相不应该在这种年纪就能参透的。我不大相信的瞟了他一眼。
没想到他更兴奋了:“这眼神最象!”
白痴的话总能让天才产生兴趣。
“是不是很象你偶像?”我不禁问。
“象燕子。”
“谁是燕子?”
“燕子都不认识?!”大鹏的眼神透出极端的不可思议。
“我为什么要认识她!她认识我吗?”
“她可是我们公司的五朵金花之一,你居然没听说过!”大鹏大有一种和我这种人为伍而有损他形象的感慨。
回到宿舍,我收到一封信。
是飞的来信。
一封有生以来见到的最薄的信,薄得几乎透明的信纸就足以能说明她的心意。
刚结识她的时候,我就曾考虑过她的名字:高飞的意思是不是指她终将离去。
吃过晚饭,为了不让宿舍的墙将我的拳头挡得血肉模糊,我决定出去走走。
这异乡有一种独特的天气,没有雨没有雾,但晚风能将你的头发和衣服吹湿。
我一个人走在街边,那晚的风不仅吹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还打湿了我的眼睛。
街边的霓虹无聊地闪烁,重复着它们泛滥的热情。
身旁的行人匆忙地奔走,忙碌着他们所谓的生活。
固执的我无奈地追忆,珍惜着一段被对方遗弃的感情。
以前多少为我的记忆力感到过骄傲,可现在正是这些记忆让我倍受煎熬。
人总是记得一些不该记住的,而且越不该记住的记得越清晰。
当我意识到带来痛苦的不是飞,而是自己的回忆,我明白了:我已无法解脱。
那天我漫无目的的走走结束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因为后来我有了方向——回去。
还没到宿舍,就有人告诉我,家和在等我。
家和在等我聊天,因为他很无聊。
其实和我聊天也很无聊,但他总认为用一种无聊去打发另一种无聊就是有聊。
“我贴了寻人广告找你。”他一看到我就开始无聊。
我只好跟着无聊:“找到了吗?”
“去哪了?”
“走走。”我无力地坐下。
“怎么,心情不好?”
人总爱掩饰自己的失败。
于是,我找到一个我们都有兴趣的话题:“你认不认识燕子?”
“当然!”
当然认识还是当然不认识?
“你看上她了?”他又开始无聊。
“她长得怎么样?”我想证实中午的时候太阳不仅晒花了大鹏的眼镜,而且还晒花了那镜片下的眼睛。
没想到接下来我看到了那一天中第二个别人不可思议的眼神。
“怎么,不知道她长什么样是不是很奇怪?”我有些难以置信这位燕妹妹的魔力。
“我们公司就这么几个屈指可数的活宝,你居然不认识,你太对不起我认你做偶像了吧。”家和一本正经地坐到我面前,然后就一直傻盯着我。
我心里直发毛:“就算不认识,你也没必要这样看着我。”
“不是,”他象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你的眼睛很象燕子!”
这下轮到我傻盯着他了。
那天起,在大家的印象里,我似乎真多了个妹妹。
我根本连见都没见到过她,她却象是我很熟悉的人。
而另一个人明明已经远走,但却又象从未离开过。
一年以后,我回到故里。
公司的一切都是新的,好象未来的一切都可重新开始。
但这世上有什么可以真的重新开始?
就如同那封最薄的信上所说的:“人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我们都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我们总是在盼不来的未来和回不去的过去之间徘徊。
我的城市依旧,市里的街道依旧,街边的树木依旧,树下却只剩我在独走。
“花谢。”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
不用抬头我就能知道是秋雷,据他妈妈告诉我,秋天生他的时候正在打雷,结果他说话也就象在打雷。
“我就知道,你一回来肯定会到这儿来,她呢?”秋雷显然是在问飞。
因为从前这条路上时常出现我和她出双入对的身影。
“走了。”我幽幽地答道。
看到了多年的老友,我脸上才露出笑容。
“那咱们回去吃饭吧,咱哥们儿可整一年没见了,今儿要好好聊聊。”秋雷搭起我的肩膀就走。
晚饭以后,秋雷已有明显的酒意,而我怎么样都无法让自己醉去。
“你小子现在可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啊。”雷声又起。
“工作嘛工作有了,老婆嘛老婆也快了。”雷声不断:“咱弟兄可羡慕死了!”
“她已经和我分手了。”经过一年的面对,我的语调平静得几乎没有感情。
雷声顿止,空气宁静得让人窒息。
显然因为我的这句话,秋雷已完全清醒。
“你下午不是和她一起在散步?”秋雷从未如此细声细气地说话。
“一个人走走。”
“她呢?”
“不知道。”
“你没去找她?”
“干什么?告诉她我回来了?”
“应该让她知道。”
“她想知道的话,会知道的,不用等我去告诉她。”
“什么时候的事?”
“刚到那边半个月。”
“你信里怎么从没提到过?”
“让你帮我难过?”
“那你这一年是怎么过的?”
“不是很好吗,没少什么嘛。”还没说完,我感到鼻子里有什么快要从眼睛里流出来,于是我连忙走了出去。
没有想到那晚的酒那么厉害,不仅让秋雷能小声地说话,还会让我的鼻子和眼睛都不舒服。
第二天晚上,秋雷仍在那条路旁的树下找到了我。
“她有没有说原因?”看来昨晚的酒精还没从他身上散去,因为他的声音仍很低沉。
“我没问。”
“为什么?”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即使无法挽回,但起码要知道她为了什么。”
“何苦逼她找个借口。”
我们肩并肩地走着,那是自从飞走了以后,我第一次感觉到温暖。
那天深夜,下起了雾,雾很大。
我们心里都希望这大雾,能将这条路变得模糊。
通向公司的是另一条崭新的道路,这条路虽不长,但却与被大雾笼罩的那条路交会在我的楼下。
可能是因为家离公司太近,更多的或许是早已习惯散步,我决定每天走着上班。
在这条路上,有很多女人,她们从事着女人最古老的职业。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挣钱的方式和她们一样。
我出卖的是自己的时间和体力。
庆幸的是在中午的时候,我有一段所谓的自由时间。
更可喜的是象在异乡一样,甄逸的桌子紧挨着我的桌子。
“休息了几天干了点什么?有没有去丈人家走走?”甄逸居然没利用这段时间补偿他亏欠了很久的睡眠。
“你有丈人?”我感到惊奇,因为甄逸的年纪比我小。
“有,好几个呢。”
“可惜大都过户给别人当岳父了。”甄逸另一边的江凡打趣道。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吧?”我替甄逸说道。
“他的问题是旧的没去,新的已来。”江凡说。
忽然电话响了,我和江凡同时望向甄逸,因为一整个上午,他的电话最多。
果然他变得柔声细气,耷拉着脑袋在角落里煲着他的粥。
下班的时候,我和江凡一同走出办公室,由于是第一天上班,我们才决定给公司的电梯一次荣耀——载我们从二楼到一楼。
电梯的门刚打开,江凡便和一个美女搭上了话,后来我才知道,她也姓花,可以说是我们公司的五朵金花之首。
“第一天上班?”她的声音和她的容貌一样秀丽。
“对,对,你,下班?”显然江凡在美女面前远不及甄逸自如。
“下班。”她的声音还很温柔。
“你是不是叫花谢?”这句明显是在问我。
“你怎么知道?”
“你的名字很特别。”她先走出电梯,回头说道:“我要去找燕子,你们先走吧,再见。”
目送她走进电梯对面的办公室,我转头找江凡,没想到他已走出了门厅。
斜阳依旧从去年的这个角度射过来,而今天的地上却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影子在摇摆。
早晨的这条路特别的安静,让人难以想象它昨晚的绚丽与精彩。
清晨的空气仍不能掩盖那纸醉金迷的脂粉气。
或许可以从地上破碎的酒瓶看出一点人们歇斯底里的激情。
我不知是该庆幸还是惋惜,我将每天都能呼吸到这代表着文明的空气。
跨进办公楼的门厅,不自觉地向电梯对面的办公室瞟了一眼。
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以后一年多的习惯。
我每天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早上和他们聊天。
“昨天的美女是谁?”我问江凡。
“什么美女?哪里的?”甄逸已迫不及待。
“小花,他本家。”江凡答道。
“你觉得是美女?”甄逸问我。
“难道算不上?”
“还可以吧。”甄逸抱着头趴在桌上,好象已失去了先前的兴趣。
“你们怎么都认识?”我觉得自己有些落伍。
“她和燕子住宿舍,就在我楼下。”江凡说。
“那你岂不成了近水楼台。”
“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名‘花’有主,据说连中国法律都同意了。”
这下我才明白了甄逸为什么会没有兴趣。
“名‘燕’也有窝吗?”我的感觉恰恰和甄逸相反。
江凡皱起眉头,好象在仔细地搜索记忆。
“以前是没有,现在就很难说了,毕竟过了一年了。”
“喂,说不定你还有机会。”我逗甄逸。
“搭燕子窝?我考虑考虑。”甄逸打着哈欠,迷迷糊糊地说道。
不知道昨晚的他在哪里过了一个狂欢的夜。
对于工作了半天的人来说,公司的午饭还算可以下咽。
我坐在靠近走道的桌子,这样有利于我看清楚进出的每一个人。
我惊讶地发现,公司里的女性岂只五个,或许他们讲的那五个比较杰出吧。
“这里有人坐吗?”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左边的座位传来。
我转过头,看到的不仅是昨天电梯里那张秀丽的脸,还有她背后一大片跌碎的眼镜片。
显然已不需要我回答,因为她已坐下。
但出于礼貌,我答道:“没有,你可以坐。”
我的脸上出现了那天在海边,大鹏舔着嘴唇盯着我的感觉。
我在心里推翻了那天我自己创立的学说,因为那种热能有时会自己产生。
“我也姓花,他们都叫我小花。”她开始自我介绍。
我不得不也来一句废话:“我也姓花,他们都叫我花谢。”
“你妈妈姓谢吗?”这可能是我身上她最感兴趣的问题。
“是感谢的谢,还好不是螃蟹的蟹。”
“我看到花名册上你的名字,觉得你应该很特别。”
从小到大,这名字一直让我引人注目,我已经习惯。
可还是担心她以为我过于特别:“只是名字有点儿怪,其他都很正常。”
她的笑声很动听:“呵呵,我又没说你不正常。”
“你为什么坐在走道边?”她感兴趣的可真多。
“我有点近视,坐在这儿可以把公司的女孩看得清楚些。”
“你倒很直接。”
“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觉得我眼睛的一部分功能应该是用来看女性,另外,那些女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如果没人来看,岂不是白费了她们一番苦心?”
“你这么为她们着想,她们应该来谢谢你。”她明显是在打趣。
但我仍作出一本正经:“那就不勉强了。”
“你好象不住宿舍吧。”
“对。”
“住哪儿?”
“家里,公司门前这条路走到头就到了。”
“那应该和宿舍差不多远。”
“宿舍在哪儿?”
“和你反方向,有空可以到我们宿舍来玩儿。”
还没等我回答,她又问道:“明天中午我还坐这儿好吗?”
我心里受宠若惊:“明天坐到我对面吧。”
说完了这句,我佩服自己的脸皮。
“为什么?”
“便于我更清楚的看你。”让脸皮厚就厚到底吧。
第二天中午,她果然大大方方地坐在我对面。
今天,不光是有眼镜跌碎的问题,我好象还听到有人嚼眼镜片的声音。
我先开口:“宿舍环境怎么样?”
“还不错。”
“几人住?”
“两人。怎么,你想住宿?”
“如果跟你合住的话,我可以考虑。”
她斜了我一眼:“美死你,有人了。”
“谁?”
“燕子呀。”
我暗自庆幸,她落入了我的圈套。
“燕子是谁呀?”
她果然正中我下怀地回头便指:“在那边吧。”
“咦!怎么不在?”她左右寻找着。
“可能今天出去办事没回来吃饭?”她解释道,但她还在继续张望着。
“算了,别找了,总有机会看见的,吃饭吧。”我假惺惺地说。
“她就在你楼下的那间办公室,应该见过吧。”
“我那地板不透明。”
“一定碰过面,可能你们互相不认识。”
我努力翻着记忆,这两天是不是在镜子以外的地方看到过自己,还应该穿着女装。
她看得出我想得很费力:“算了,算了,有机会的话给你引见引见。”
“谢谢,不用,我一定要自己认识她。”
晚上,秋雷将两本厚厚的日记放在桌上。
那是去年我远行之前放在飞那里的。
“我去找过她。”秋雷的语调沉重。
“谢谢。”我知道他肯定是为了我。
“她说她本来想帮你烧掉的,后来觉得由你自己处理比较好。”连秋雷的声音都在颤抖。
“她还说,她知道有些东西是抹不掉的,她只是希望你能少接触过去。”
我无言以对,空气又令人窒息。
“我还在她公司门前看到另外一个人在等她。”
尽管这早已是在我意料的事,但仍然让我觉得胃酸已涌到心脏。
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