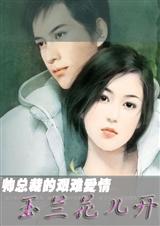花儿谢了-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既然很长,那么我告诉你一件事吧。”秋雷好象终于拿定了主意。
我们都停下,他准备讲,我准备听。
“我今天收到了飞的请柬。”
我的心又猛然一振。
一瞬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明白了他今天说的每一句话。
我感谢眼前这位老友,一直都那么关心我的感受。
但他并不知道我的胸口已经疼了一整天,而此刻更在拼命涌现着疼痛。
为了安抚他的用心,我尽力地装出并不在意。
“定在什么时候?”我问他。
“十八号,下星期一。”
为了让自己能抑制住伤心,我决定去闹市区的商场走走。
或许在人群里,我能感觉到一些温暖。
秋雷陪我走在长长的台阶上。
迎面走来一对恋人,在这闹市区里恋人的数量就象夜晚天空中的星星。
天上的星星我们无缘认识,但这对恋人我们却认识。
因为其中的女孩敏是我们的同学,当然她也是飞最好的朋友。
“咦,秋雷、花谢,你们怎么在这儿?”敏认出了我们。
我终于找到了打破郁闷的机会。
“好久不见,你们好吗?”我热情地问候。
“好,你们呢?”
“好得不能再好了。”我心里却在流泪。
“你们在逛街吗?”秋雷问敏。
“我们在给飞选礼物,她十八号就……”显然敏已经意识到了,于是她没有将话说完。
“没什么,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安慰敏。
敏一下子又找来了话题:“花谢,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走的时候没见到你,回来了居然也不通知我们,已经快三年没见了吧。”
“那年我是3月27日走的,26日中午我打过电话给你,你不在,我告诉了你妈妈我第二天就走,你竟然没打电话来,还说我不够意思。”
敏一脸的冤枉:“那天晚上我到家就打电话给你了,你不在,然后我又打电话给飞,飞的爸爸说她和她男朋友看电影去了,我不想扰乱你们的情调,才没有呼你的BP机。”
我仿佛一下子从梦中惊醒,我看到秋雷也瞪大了眼睛。
只有秋雷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因为敏打来电话的晚上,飞说她为了第二天能来送我,必须加班赶完工作。也正是因为这样,秋雷那天才有机会在他家为我送行。
我不再记得我是怎样与敏他们话别的。
我只感觉到我胸口剧烈的绞痛。
我的手不得不搭在秋雷的肩膀上,否则我会当着敏的面倒下。
望着敏和她男友去远的背影,我的脑海里传来的是自己空洞的心跳声。
我最后看到的是秋雷噙着泪水的眼睛,最后听到的是楼梯撞到我肩膀的声音。
当我再度睁开眼睛,周围都是白色。
我挣扎着坐起,才看到房间门的天窗上森然的反写着红色的“急救”。
这时我才注意到床边摆着很多的仪器,有的还发着和我心跳同步的声音。
“你别动,我去给你叫医生。”守着我的护士说。
于是我盯着那些仪器,回想着发生过的事情。
一会儿,刚才的护士带着一位老医师还有秋雷走了进来。
从老先生光光的额顶,便能看出他学识的渊博。
“你醒了,怎么样?胸口还痛吗?”老先生很慈祥。
“还好,不那么痛了。”
“刚才我向你的朋友了解了你的故事,我觉得你是个开明的人。”
我用微笑表示谢意。
“按照我们医务工作的惯例,一般不向患者本人透露他的病情。”
“但由于你的情况比较特殊,我觉得让你本人知道你自己的情况比较好,希望你静下心来听我说。”
“从你被送来的时候的透视报告和刚才你苏醒前的透视报告看来,你心肌神经有病状。心肌神经在出现痉挛时,会导致你心肌起搏无力,从而导致脑部及其他部位供血不足,你刚才的晕倒就是这个原因。”
“你现在是偶发性的,就是这种痉挛现象不是一直持续,在不发作时期,你就和正常人一样,一旦发作,短时间的话会呼吸困难,时间过长就会因脑部供血不及而死亡,所以你必须尽快得到治疗。”
“这种痉挛一般分为自然发生和刺激发生,你刚才的晕倒显然是受了剧烈的刺激,情况很危险。”说完他望了秋雷一眼。
“你是我们医院接治的这种病首例患者,由于我们医院设备及经验不足,我们决定将你转院到上海治疗,我们已经联系了上海一家专业的心脏病医院,他们也愿意你转院治疗。”
“但需要对你说明的是,你这种病极为罕见,这家医院也只治疗过一个病例,是个婴儿,出生时就存在这种心肌神经病状,由于婴儿心脏脆弱,不能施行手术治疗,医院用药物维持了婴儿一个月的生命。”
“你现在的情况要比这个婴儿乐观,但我们也不敢保证能够治好,让我们大家都努力吧。所以我想问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我可以为你办转院手续。”
“今天是几号?”我不敢确定我昏迷的时间。
“你只晕过去不到两小时,今天还是十五号。”
“那就麻烦您定在十八号吧。”
“好,十八号。”老先生站起来准备离开。
“我可以出院回去准备一下吗?”我问老先生。
“你现在就可以出院,你现在不处在发作期,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说完他准备离开。
到门口时他又转回来:“记住,一定要保持愉快的心情,你才有机会痊愈。”
我望着老先生离去的背影,默默地问自己:我能永远快乐吗?
1999年10月17日。
晚上,秋雷来到我家。
我倚在窗口,望着窗外的那两条路。
“我来给你收拾行李。”秋雷站了很久说。
“我已经收拾好了。”我望向桌上一只不大的紫色背包。
秋雷打开包,里面放着两本日记和一封很薄的信,还有一张紫色的贺卡。
“带点东西去吧。”秋雷几乎在哀求。
“我能带得走什么?”我仍望着窗外。
听到我的话,秋雷开始抽泣。
“那让我明天陪你去。”秋雷的声音已经含糊不清。
我仍望着窗外,幽幽地说:“你还能陪我走多远?”
然后我听到了久违的雷声,是咆哮嚎啕的雷声。
深夜,我无法安慰秋雷,只能眼看着他的泪水弄湿衣襟。
我站在楼下的路口,我很想再去那两条路走走,但我不知该先走哪条。
左手是燕子的路,右手是飞的路,身后是我和燕子放风筝的花坛,不远处还有那家“香菇青菜”。
我那一刻的心情却异常平静,是不是因为我知道我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两条路。
我甚至希望那一刻我的胸口能再次疼痛。
那么,只要在我离去的瞬间,我还保持着对她们的思念,那我就能让她们看见,这世间真的有她们都不相信的永远。
深秋的风,吹起一片枯萎蜷曲的梧桐树叶从街面上滑过。
树叶刮在路面的声音象是在说它想要留下,但它最后的执着远远抵挡不了秋风的萧索。
我回去的时候寄了一封信。
给秋雷的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
“如果我回不来,记得把墙上那只风筝烧给我。”
1999年10月18日。
上海一家医院的门厅里,出现一个背着紫色背包的少年。
他飘逸的头发却掩盖不了他苍白的双眼。
他径直走向服务台,告诉护士他想看病。
于是护士问他的名字。
只听他说:
“开花的花,凋谢的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