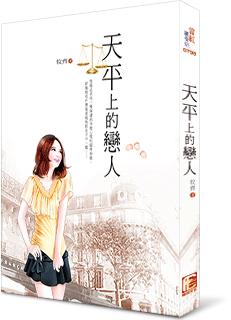地板上的母亲-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主要围绕在通过辨析语言本身的模糊性从而瓦解哲学问题的提出。不太理解,不过联想到日常语言的欺骗性和暧昧性,外加交流中的话语权的争夺,黑泽明在《罗生门》中提出的叙述的主观性等等之类的东西,不禁让人对话语本身感到很泄气,套用刘小枫的话,就是“编织语言”的能力本身是一件不连续和粗糙的事情,所以我不想多说,最多也是描述性的东西。
快乐,抑郁,实在是太粗糙了,再加上电视化和小说化生活的荼毒,使本来就苍白的感情体验更加像风干的鱼一样瘦小干瘪。程式化的感情体验用不连贯的语言表达出,当代人的生活真是让人无话可说,包括我自己。
就这样吧。祝快乐。呵呵
《凯尔特智慧》
亲爱的漫儿:
看你读那些艰涩的大书深有所获,看小星星读《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津津有味,我好羡慕!看来我这辈子说什么也跑不过你们了,就撩撩霜雪浸染的鬓发,找块石头坐在路边为你们喝彩吧……
今天天气晴好,阳台上的花木才浇过水。我坐在透窗而来的阳光里,随心所欲地看一本闲书。有两只燕子在对面楼顶上调情,翻飞盘旋,亲昵地叫唤着。我把书放在膝盖上,看着它们有两次飞向咱家的阳台,也许是长满绿叶的银杏和石榴树的招引吧?我的肩膀连同胳膊和双手,在看这对燕子的时候不知不觉耷拉下来,等我再拿起书本的时候,忽然醒悟到先前我是不由自主地端着架子的!这种不由自主的“端”,多年来累及我的颈椎和肩周,更累及我的心灵,就想如果我改变一种方式,把总是急煎煎的心情连同肢体一起松散开来,让风与雨与阳光自由出入其间,将会多么清爽而美好。就说刚才吧,我把书搁在膝盖上,手交叠着搁在书上,透窗而来的风和滑下银杏叶的阳光,虚泛着我的头发和我的心情,那个瞬间多么安好……
断断续续看完了《凯尔特智慧》,受益最深的有这样两个观点:一是“感知即现实”;二是“灵魂渴望统一”。你读过尼采,一定记得尼采说过,在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是当他把其所有的否定特性重命名为肯定特性的时候。
“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塑造生命最强大的力量”,这对于你来讲,不用说是老生常谈了。你眼见的,老妈这辈子吃亏就吃在不能平和客观地看待事物,有我这面镜子,只要你略微地想一想,就会明白“感知即现实”的深意所在了。
至于“灵魂渴望统一”,就老妈的浅见,是在明白了内心如同客观世界一样多元之后,彻底告别完美主义,欣然与自己内在的种种负面的东西和解,也就是换个角度,把所有的否定化为肯定。约翰在解读凯尔特智慧时说:“智慧就是平衡已知和未知、痛苦和欢乐的艺术,它是把整个生活用一种全新的更深的统一联结起来的方式。”这话让我觉得自己总是和自己过不去实在是舍近求远,得不偿失!比如你和小星星经历的考试,比如我写书和评职称,实际上都不过是一小段一小段的石阶,放在蓝天下层叠的群山里,放在脚底下,这才是正常的,之所以那么艰难那么吃力,全是因为我错误地试图把它们背起来。冥冥中有一种“大”囊括世间的一切,经见并记取了这种大,周遭的种种自然就小不可言了,进而也就“治大国如烹小鲜了”……儿子,从里到外放松自己吧,就像那一刻坐在阳台上享有燕子和阳光的老妈。土虚苗长,手不握沙不漏,筋骨柔软,才得如坐春风,你说是不是?
你天天去健身房,酸痛过后是松爽,不错不错。你说的竹林七贤遗踪就在焦作,等有机会咱们一起去游玩一番,定会是一桩快事!昨晚听到你欢乐的话语,就像咱们仨还在一个屋顶下嬉戏!躺在看书的小星星身边,无所事事望着他的身影的那一刻,是我今天享有的最美妙的幸福……写信给我好吗?
愿上帝天天赐福给你!
何不秉烛游
老妈你好啊!
在等一个电话,顺便写两句吧。
前段时间熬夜比较厉害,不负“夜长苦昼短,何不秉烛游”,结果往往是早晨从中午开始。后来开始调时差,现在总算恢复正常了,老老实实晚上11点上床,看一会儿闲书,或者一集探索节目,很快就睡着了。没成想有天晚上把被子踢掉了,半夜冻醒,癔癔症症地在床上坐了半天,恍惚不知何所在,再倒头睡去——都是事后同学告诉我的,我坐了半天,他喊我我也不应,把他吓得半死——早上起来就发现感冒了。现在差不多已经好了,勿牵挂,每年总得感冒一两次,锻炼一下免疫系统。
近来北京雨水充足得很,三天两头就打雷下雨,下得还挺大的。雨水打在窗外杨树叶子上,沙沙作响,直教人昏昏欲睡。就在三四天前,下过一场雨后,外地同学打电话过来,说要来清华看看我,我也不好推托,于是就答应了。大家一起吃了顿饭,聊了些这两年的事情,感叹时间过得快。别的事也没再说,吃完饭我就直接把她送走了,她说了一句,你这就把我送走了呀,我只是笑笑。那天天气凉爽,雨云低垂,却再也没滴下什么来,所有的植物都变得茂盛而阴郁,周围的人则只剩下的脚步声。
吃饭前,我又陪她去了趟荒岛,就是荷塘中间那个种着朱自清雕像的岛。岛上新养了孔雀,五六只的样子,就圈在一个四五米见方的铁笼子里,地上铺了细沙,顶上有凉棚遮住一般雨水和阳光。当天的雨打湿了半边沙地,孔雀也被淋得一塌糊涂,疲沓地呆立在那儿。我们围绕着孔雀会不会飞争论了一会儿,在归于沉默的时候,有个孔雀突然开屏。
又说到茗茗,不知为什么,她始终执拗地认为我还在喜欢茗茗,呵呵,奇怪的人。
关于湘云,其实事情很简单,也没什么可说的,无非是我表现得不合时宜,可能过于上杆子,或者其他什么,无所谓,离这么远,说什么也不可能,不否认曾经有过些想法,可已经过去了,这个世界,缺了谁都可以照常运行。
下个学期就要回深圳了,要面对的是冷清的校园和空荡荡的寝室,有好有坏,我会慢慢应付的,放心。
把同事处成朋友
亲爱的漫儿:
你怎么能拿感冒锻炼免疫力呢?想着我从山上下来,你就该好了,鼻子还是瓮声瓮气的,康泰克退烧还行,对付鼻咽处的炎症,简直就是助纣为虐!我上过它不止一次当。
原想小星星在身边,我已经学会少想你一点了,谁料母爱也有霸道的面孔,连我自己都感到恐怖,心中千丝万缕,即便自己弄出来的杯弓蛇影,也会把它催化成一张丑陋的鬼怪面具,屏蔽了你,也妖魔化了我自己!你恨我吧,离我远些吧……
我曾经认定:同事不可能成为朋友。这次跟着教育电视台的几个人上了一趟山,方知此言差矣!有个叫张萍的女孩子,也曾穿过情感的炼狱,竟然不留疤痕全身而退,依然活泼泼如同清水河上的阳光。她是个“驴友”,常常和几个同事一起,背着帐篷、炊具,带上挂面、绿豆、大米、油盐酱醋之类,往偏远的深山里跑。长沟儿、平沟儿、珍珠潭、西大河、核桃树……光听听这地名就够刺激的吧?这次我跟着他们去海拔一千八百多米的霍庄小学,去只有三个学生的桃林小学,真是长足了见识。去桃林是中午正热的时候,汽车沿着十八垛的盘山公路左拐右拐,胳膊甩得又酸又痛。两天时间,连来带回几百公里,与好山好水同行,一帮人忘了累,忘了热,只剩下山风一样的惬意了,名副其实的精神漂流啊!想起你推荐的那本《塞莱斯廷预言》,我觉得我找到了多年同事成朋友的答案:和大山手拉手,吸纳着大自然无穷无尽的能量,他们根本就不屑玩弄市井小人那一套相互榨取的“控制剧”。举手投足、一句话一个眼神达成的默契,就像一蓬共生的蔓草息息相关,逃脱了呼吸得酸臭的机关味儿,他们算是找到了五柳和竹林们的真情逸趣。
在霍庄露营那晚,吃过饭坐着说一会儿话,就听张萍吩咐道:你们快去打电话吧(爬五分钟的坡,就不是长话),记着看花盆啊!几个人走远了,她又叫上我一起去“看花盆”,我不明就里,她笑着说:“‘看花盆’就是上厕所啊!”
有个小伙子打呼噜,帐篷挨着我们的帐篷,夜深了轻声喊过来:张萍,张萍……听不见回答,才安心把他差不多能吹动一片大草原的呼噜打响。
儿子啊,世上什么都可以赠送,唯有爱情不可以,看了你的信,我心里忍不住痛惜那个姑娘,因为老妈也是一只
恐龙啊!没有爱情就给她友情吧,毕竟友情也是人间温暖,我想你还是给得起的。
等你回来,咱们也背着帐篷去一趟西大河好吗?
当你爱着的时候
亲爱的漫儿:
当你爱着的时候,你能在自己心中打开多少精神的宝藏,会有多少柔情、温存,你甚至不能相信,你会这么爱着。
——契诃夫
昨天看到这话时,心中惆怅了好半天!都是你那句“SM嫁人了,你还记得SM是谁吗?”勾引出来的。俗话说:“男长十八一朵花,女长十八老扎扎。”人家都二十四岁了,不嫁人更待何时?儿子啊,我惆怅的只是岁月流逝,让我的毛头小儿子也有了沧桑之叹!
今天中午,我去小星星的校园,在二门的铁栅栏外,眼巴巴看着孩子们成群走过,最终我要找的人来了,也没望见他的身影。转身向外走的时候,心里头湿漉漉的酸楚,像是谁一耙子下去连草带泥刨掉了一大块,草根子的断裂拽得我说不出的难受。这就是对儿子的牵肠挂肚,第一次这么强烈地在他身上重现,着实让我悚然心惊!昨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还没发现这陡然翻倍的危机,漫儿啊,你告诉老妈,我可该怎么办呢?
秋天最后的那个日子,有一会儿我和小星星在工学院西边的山地里闲散,这孩子不再欢呼雀跃,也不拣路,自顾自低了头,信步在拔棉柴带起的深深浅浅的土坑上慢慢往前走。我指给他看墓地里一丛淡紫色开成大花篮的菊花,他也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眼看就立冬了,柔嫩的茵陈蒿却逆着季节毛茸茸扑棱一地,惹得我眼馋手痒,只后悔没带小刀。忽然发现田埂上有一棵地宝豆,就叫小星星过来,拣果包儿干黄的摘了给他吃。紫色的浆果比豌豆略大些,剥了皮儿一咬一包儿酸甜。我摘得快,他吃得快,连说好吃,真好吃。
看着他馋嘴小儿郎的模样,我眼前忽然重现出武汉东湖磨山的光景:也是暮秋时节,比眼前的星星小得多的漫漫,一路拉着妈妈的手,走在落光了叶子依然密不透风的山林里,树木清冷的香气让人兴奋异常,母子们忘了太阳正在沉落,也忘了是向西还是向东!眼见暮霭四合,我才慌了神,抱起我那虎头虎脑、嫩包谷一样馨香的宝贝儿子,一路狂奔,总算赶上了最后一趟公交车……
我抓起地宝豆柔软的茎干,仿佛抓起了深深长长的岁月。我把地宝豆放进小星星手里,一仰一合的两个手掌,扣紧了这个秋色杂陈的荒山丘上的日子,也扣紧了你多年前留在磨山密林中的欢声笑语,扣紧了此生此世母子们的一往情深……
昨天上网浏览,不知不觉听了一晌《红楼梦洞箫音乐》,心里灌满了莫可名状的悲凄,晚上又没接到渴盼一天的那个电话,躺下来就掉进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我看着自己孤零零地走在旷野里,走在备受人与兽的践踏和风霜雨雪蹂躏的黄土大路上。谁能来到身边,为我驱除生老病死带来的恐惧?父母?丈夫?兄弟姐妹?即使他们躺在我身边,也与我相隔千里万里,奈何不了围困我的无边凄凉!
就在五脏六腑被冻成冰坨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凡尘的种种卑微,联结而成的是为孤苦人生保暖的温室啊,谁若是不小心洞透这灰土飞扬的保护层,他就会失落结在日子这根藤上的地宝豆——稠密的亲情与爱情的细节,失去灰喜鹊一样叽叽喳喳的温暖与快乐。
亲爱的漫儿,午夜和你通话之后,我终于安静下来,重温我和小星星在那口一人多深的大铁锅里舀粥喂狐狸的情境,重温鱼塘边上那个老人为我们看大黄狗的情境,重温吃晚饭时小星星偷偷往我碗里夹肉的情境……我把我的心安放在这凡常细节的织物之中,慢慢合上眼,进入了梦乡。
中秋即景
亲爱的漫儿:
你没有打电话回来,写点闲话儿在这里,贴给你看吧。
几天没去,池塘里的野芦苇抽穗了。因为是野芦苇,没有人经心照管,它们生长得随心所欲,却免不了像街头的流浪儿,黄巴巴的纤弱。香一样的细莛儿,举着半尺长的穗子,披头散发,紫得很淡。因为出莛儿,它们猛地蹿起一截儿,看上去比蒲草还高些。只可怜那些肥壮密实的蒲草,经不得秋气,还没下霜,就开始枯萎了。
最恼人的,不知从哪里爬出来两只蟋蟀,一只在阳台上,一只在
卫生间里。我不忍心赶它们,它们就越发上样,天傍黑儿开始振翅鸣叫,……一直到楼底下铲垃圾的声音响起来还不住声!“闻蛩唧唧夜绵绵,况是秋阴欲雨天。犹恐愁人暂得睡,声声移近卧床前。”千年之上的白居易,也曾被这彻夜清音如此折腾过吗?
那天下午,我站在大柳树底下,看风刮着半塘蒲草,刮过那些野芦苇,慢慢把心中的种种疏松开来,听凭柳树上的风和水塘里的风,簌簌沙沙,沙沙簌簌,轻轻舐着心田,卷去了连日的阴冷潮湿……
国庆节有人想带小星星去你那儿,他不答应,说:“学业为重啊!放完假就月考呢!”这话从他口中说出来,难能可贵呀。今天上午,我拉他出去转了一圈儿。没敢跑远,逛了逛花卉市场,顺便去看看热带鱼,小星星知道得还真不少!去了趟北京,跟着哥哥长见识啦。
我心里牵挂的,是大营那两棵树。坐在车上看见过N次了,一棵向东歪,一棵向西歪,不细看还当是一棵呢,一半儿叶碎些,看上去分枝儿;一半儿枝叶密实,浑然一团。
终于望着高大的树冠,穿过逼窄的巷子近前去看,却是铁门紧锁。隔着院墙观望,碎叶的是槐树,密实的是柳树。主干三人合抱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