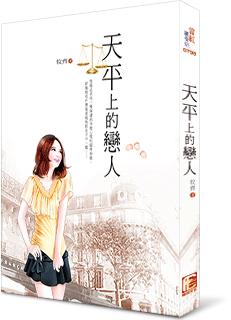地板上的母亲-第5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快乐爆响,捆绑我生命的无形结界炸裂,客厅里的景象拓展开去,迢递的是水,连绵的是山,山和水都是我躯体的延伸……
客厅里的田园,一刻千金,一刻千年。
我一瞬不瞬地看着他,看着那个上天经由我送来人间的孩子。
儿子,让我怎样爱你?
那孩子洗完澡,已是午夜十二点多了。我催他赶快睡觉,他皱着鼻子扮鬼脸儿,求我让他再看半个小时闲书。期中考试就在这几天,为了能拿到理想的分数,昨天从学校回到家,他一直都在复习功课,所有的娱乐都取消了。这会儿他想从睡眠时间中抠出半个小时,稍稍满足一下课外阅读的嗜好,我能忍心打他的兴头吗?
使劲搓了搓脸,把自己放倒在床上,疲倦扑扑掉落,酸软透晰四肢,麻酥酥镂空了沉重与浑浊,有一种清澈弥漫开来,洗除日间的昏暗琐碎与粗陋,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明澈了两个人的生命,明澈了儿子和我。
我乖乖地、听话地不发出一点声响,就这么一瞬不瞬地看着他,看着那个上天经由我送来人间的孩子。他就趴在我身边,屈肘支起上半身,翻看《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一本带彩图的讲述精彩历史细节的书,这怎么能算纯粹的课外读物?换个口味学习而已!
今生今世,我做了他的母亲,我为什么不是一座坐拥半天云的大山呢?如果我有那么高大那么富有,我愿意将我的生命消融成浩浩荡荡的江河,泽润出足够大的苇滩芦荡,让我的儿子自由自在,快乐成一羽无羁无绊无忧无虑的白鹭青鹤!我就是一片旷野也好啊,在蓝天下袒开灵魂与肉身,绵延着,舒展着,豁开所有封闭的幽暗,让阳光哗哗流淌,让季风畅荡来去,让我的儿子们撒欢奔跑,成虎为狼做羊做鹿,各自遂了各自的心愿……
唉,连一次考试我都帮不了,做这白日梦又有什么用呢?那么儿子啊,咱不读书不受这份罪好不好?咱们回乡下去,种麦种豆栽棉花,喂它一群羊,养上几头牛,门前屋后再栽几行树,每天看着太阳从东边地平线上升起又在西边地平线落下,呼吸着纯明的四季,眼看青杏一样的女孩儿闹着妈妈梳头编辫儿,辫着辫着成了喜气盈盈的
新娘子……
“妈妈呀,我哥哥要是上了哈佛,我就去考牛津,你说我能考上不能?”
这是着了什么魔?春节时还满世界疯玩连饭都顾不上吃,新学期没上三个月,怎么就成了如此“胸怀大志”的“好孩子”了呢?面对现实,我脑海里片时的温煦明丽,顿时冰雪消融了无踪影。
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并不复杂,那就是做一个倾心倾情的倾听者。
十六朵月季
我不止一次驻足在路边那片月季近旁,看那些娇艳的花朵儿交替着开了谢,谢了开。不是我喜欢的正红和淡黄,紫红色,有点浓,虽不俗艳,也与我淡淡的两不相关。下过几场霜之后,管理人员剪掉了花枝,可能是怜惜吧,一些颜色尚嫩和半开未开的花朵被留了下来。那天下班等车,残留的花儿被风吹动,如同即将熄灭却又拼命燃烧的火苗儿,一下子触动了我。我跳进枝条狼藉的花丛,连刺折了十六朵。回家插进注满清水的瓶中,供在电脑桌的右上方。不到半个时辰,它们就在温暖里缓过神来,吐出若有若无的芳香。
我不是一个爱花的雅人,促使我鼻眼共用去啜饮这些花朵,用粗糙的心触摸它们的娇嫩、丰满与细腻的,是近些日子心路转弯带动的那一抹柔软的弧光。我不单把它们认成是大自然的花儿,也把它们认成了大自然的心灵。
在一次成功心理学研究者的聚会上,我结识了一群智慧心灵的采撷者,他们带来各自捕捉的信息和思索研习的收获,一无杂念地相互分享,在思想碰撞的张弛疾徐里,让我领受到了春芽争相出土的愉悦,和一种籽粒般拱手的饱满。红湿于霜露之下的这些月季,成了我此番心境最恰切的投射。有位心理医生讲了一个成功的案例,让我平生第一次认知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并不复杂,那就是做一个倾心倾情的倾听者。
多年来在人海漂泊,我这个人最大的长处是嗅觉敏锐,差不多在别人还没来得及把心里话尽数吐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从前心到后心看个通透,且不懂韬光养晦,一开口滔滔不绝,恨不能把人家的五脏六腑都拿到消毒炉里蒸蒸。这不良习惯让我失去了无数静静享用心灵果实的机会儿,哪怕又苦又酸,只要结在朴素的心灵上,也会是极富营养的啊。骨子里,我又是一个心灵浆果的饕餮,目光不停地在人群里逡巡,只搜寻红熟黄透的果实,并且在每一次的暴食狂饮之后,立马感到说不出的乏味,随即把那个浆果的提供者弃之若敝屣!而对自己看不上眼的那些青涩和细小,从来都不屑一顾。由于错失了许多滋养自己的良机,我的心常常因干渴而龟裂焦枯,性情也越来越暴躁……
瓶中的月季,在音乐中微微颤动,是我心头那一层新近萌发的花苞。
亲情纯然如水,流淌出人与人之间曾经唇齿相依的况味。
自助工作餐
校区远离城区,小城还没有免费午餐,不知从哪天起,几个同事开始聚在一起轮流做午饭。早上出发前,根据需要买好青菜、肉、蛋和主食要用的米。中午11点多,轮值官儿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系上围裙儿,伴和着锅碗瓢勺交响曲,心儿欢快地跳动着,喉咙和鼻腔里发出甜美的哼唱,抬手举足,牵动的都是平日在身体里冬眠的快乐。等到青、绿、红、黄上了桌,雪白的米饭盛进了雪白的瓷碗里,食客们围桌而坐,说笑着共进午餐,轻松和谐从眉眼滴落心头再漫溢出来,亲情的温暖如同晒在草坡上的春光,说不出的妥帖、安适……几个人中唯一的男同事,在家是出了名的享乐派,几次小试牛刀,没承想女同事们对他的手艺赞不绝口,由不得眉舒目展,支棱棱活像一棵得了水的芹菜。等不到第二天,下午四点他就迫不及待做了一顿加餐,请大伙儿品尝。他自己抱着膀子歪着脑袋,站在一边笑眯眯地享用起女同事们大快朵颐的吃相来……
这是朋友告诉我的一个真实生活场景,这场景让我想起孩提时代在寥天野地挖地锅烤玉米、蒸红薯,你争我抢,锐声叫喊,惊得羊群四散,是一幕代代相传的游戏啊。还记得1975年逃水荒,一口大铁锅支在学校的操场上,那个黑炭似的驻队干部,拿着大瓢分煮麦,红红的灶膛把全村父老的心烘得透亮……最真切是那年下乡帮农民收麦,安排我和一位叫和尚的同事做午饭。我俩蹲在农机房门前的水龙头两边,洗菜,淘米,打鸡蛋,他身后的杨树被风吹得哗啦啦响,树梢上面是晴蓝的天,阳光明亮,人的心绪随村野辽远。滤过菜叶又从指间滴落下来的水珠,碎银子一样消失在碎砖碴里,说不出的畅快。那会儿,同事的秃顶一点儿也不显得苍老难看,整个人被周围看见和看不见的什么东西浸染着,氤氲出一种可以信靠的亲情,对了,就是亲情。
这亲情,纯然如水,流淌出人与人之间曾经唇齿相依的况味,胎衣一样包裹着我们,冲荡起生命原初的真纯和快乐。只可惜,它不肯留驻在都市灯红酒绿的繁华里。
我说的是忧伤,不是都市人在竞争名义下相互挤对所激起的难以排解的郁闷。
民工的帐篷
马路对面的广场,在市民们满腹牢骚的嘲讽咒骂中,经过两个多月铿铿哐哐的敲打垒砌,终于有了层次和立体感。沿着铺设在草坪间的卵石小径,我来来回回观看那些新栽的树木,呼吸着剪草机扬起的新鲜草汁味儿,这味道因刀口的不停切割而浓烈无比。
随小径转几个弯儿,不经意来到了民工们临时居住的工棚前。印有红蓝条条的编织袋一样的棚顶,半人高的木板挡在那儿算是门,棚内砖头和木板支起一溜儿连床铺。灰暗破旧的铺盖卷儿之间,有一床红线套的表里三新的花棉被。明明艳艳地叠放着,如同一团暖洋洋的喜气。有种怀旧的情绪在心中升起,大笼馍带着水蒸气的味道扑面袭来,夹杂着尘土飞扬的草末子的气息、马粪的气息,还有胶轮车骨碌碌滚过高低不平的简便公路的声响,和人们粗声喘息着呼喊与应答的声音……
我冲动地想要走进去,在那床新被子下面的铺板上坐一会儿,坐回我曾经的民工生涯。就在这时,多日来阴暗于心间的一块地方忽然明亮起来。《羊城晚报》上那篇煞有介事描写民工的文章为什么让人反胃?一个以笔为枪在都市楼林里狩猎为食的人,你是不能难为他去体味流淌在民工心里的快乐与忧伤的。不错,我说的是忧伤,不是都市里的白领、灰领们在竞争名义下没完没了相互挤对所激起的难以排解的郁闷。
我们假装精神和物质都比这些乡下人富足,可是只要回过头去,稍稍看一眼拖在身后的那一长串绵密得让人喘不过气儿的日子,看一眼那些我们不得不经受的种种折辱与自虐,就不会理直气壮地来怜悯这些干粗活儿的民工了。有一年从夏末到冬天的第一场雪,我目睹了八个有时是九个民工的日常生活,他们拉板车为人送水泥送砖沙,住在一家店铺的花岗岩门廊上。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一千出头儿,再差也能拉个七八百元。年龄大的六十多岁了,年轻的只有十八九。拉完一天,抽支烟躺在地铺上闲聊,说女人,说孩子,说他们汗水浇灌着的家常日月,说得津津有味,有时还会喊他几嗓子……
当然不能说他们没有烦恼,没有挣扎,可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谁又比他们的烦恼和挣扎少呢?
最终踏上了老妈和老师耳提面命舌头起茧的拼成绩、考名校的“人间正道”……
哥哥的金色童年
你哥哥小时候很胖,好心的邻居们都叫他“小胖孩儿”。不满月他就能笑出声来,两只眼睛清亮清亮,我叫它们月亮溪。只可惜近视了,变成了你看到的小眼眯,连双眼皮儿也变没了。
那时,我和他睡在一间办公室里,除了一张那年月流行的高低床,还有一张公家的三斗桌,和一把公家的靠背椅。全家最宝贵的财产,就是紧挨床那面墙上贴着的金陵十二钗。吃饱喝足又没有觉要睡的时候,他总是搬着自己的脚丫子一边啃一边斜着眼睛往墙上看,咯咯咯笑个不停。就是抱着他玩儿,这“小色狼”竟然也把软软的脖子扭一百八十度,依然对着墙上的美裙钗傻笑。没过多久,就看成了一双对眼儿!我只好忍痛割爱,三把两把将那些美人儿撕了下来。
你哥哥的第一个英雄壮举,是趴在隔壁大饭店的花坛上,曲肘撑起上半身,翘起右边的嘴角,非常努力地为自己留下一张纯真坏笑的照片。当然,发生在拍照前一天那桩事儿是不能算的:我在
图书馆当管理员,这个饭量极大的家伙每天早上七点半吃过奶,是万万等不到中午下班的,即便提前半小时也不行。九点刚过,他的小车就被推进书库狭窄的走廊,咕嘟咕嘟饱餐一顿,竖起身子打几个饱嗝,就开始不停地转动黄毛稀疏的脑袋,乱丢俏眼笑眯眯。有位叫贺京平的同事,西装革履,是单位里最上档次的“眼镜”。这文雅书生经不起他颇具杀伤力的笑脸引诱,就把他抱在手中高举过头,正此时,一线飞流落九天,他把人家从额头到下巴再到前襟,最后是前裆到后裆,兜底儿满灌!
“男孩儿尿是黄金,快请客啊小贺!”你瞧,他就用这一招儿为自己挣了个满堂彩。
你哥哥断奶后两次被送回唐河老家,留下两张照片儿让我想他。一张是裸体骑在童车上,一只手掌住车把,一只手高高举起,作挥手告别状,何等潇洒;还有一张一本正经的半身照,满脸都是无奈,圆睁着一双黑豆眼,无声的询问和抗议水汪汪地溢出来。害得我日思夜想牵肠挂肚,大年初一发神经,买两个氢气球儿,一红一黄,系在第二个纽扣上,又哭又笑,念念有词,旁若无人,招摇过市,把众人惊诧的目光拧成一股风筝线,飘飘荡荡放到几百里外,紫苍苍的村梢,虚飘飘的炊烟,村子中心的四间瓦屋,瓦屋院里的小胖孩儿啊!
后来,你哥哥在乡下玩泥巴玩上了瘾,就不要妈妈了。春三月,爬上邻居家的楼房摘榆钱儿,不小心摔了下来,把自己的脸摔个三尖口子,吓得你姨妈抱着他一口气儿跑到孟庄,又跑到县
医院,医生见不到妈妈不敢接诊,你华运姨夫雇个机动三轮,突突连夜往南阳赶。路上,你哥哥一睡着,他就吓得又摸鼻子又捏腿。我赶到南阳,坐着三轮转了一夜,找遍大大小小的医院,也不见他的踪影!妈妈又悔又恨,急火攻心,恨不得把自个儿千刀万剐再碾成灰……
打那儿以后,你哥哥用一年时间把一生的厄运全度过了。肾病综合征、烫伤、和火车抵架,然后是骨折……就在我心上千补万纳旧痂未掉又添新伤,被百身莫赎的罪感挤压得喘不过气儿的日子里,你知道他是怎样自得其乐的吗?手脖子上的夹板头天打上去,到了第二天中午,一锅面条没下滚,转眼就找不见他了!怎么喊也不应,你知道他干啥去了?河堤上挖有十几个树坑,一米多深,他架着一条伤胳膊,跳下去再爬上来,一个也不放过。
夏天睡午觉,我把这个破布娃娃一样的小人儿贴墙圈牢,也挡不住他趁着大人睡熟的时候迈开腿脚溜出去。你看他呀,手里拿根小树棍儿,一路邦邦敲着铁栏杆桥,优哉游哉,过了铁桥,穿过树林,顺着河堤向西去,一走二三里,细脖子支着个大脑袋,东瞅瞅西看看,骨碌骨碌!蒸笼一样的炎热硬是被这小人儿搅成了碎片儿。一直走到西杨村河有两个小亭子的木桥上,无限惆怅地注视着哗哗往下流的浊水,看了也不知多久,腻了,回转身原路返回。还是那闲散的步态,还是那优哉游哉的神情,一路敲敲打打,若无其事地推开虚掩的家门,轻手轻脚爬上床,贴着墙装睡……
下面是他自己的笔供:
“附近好玩的地方有好几处,第一是河滨公园,那时的河滨公园远没有现在这么多娱乐设施,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也就是游乐场和动物园。游乐场里只有滑梯,滑梯也就热天时能玩,而且人多的时候竟然还需要排队。排了几次之后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