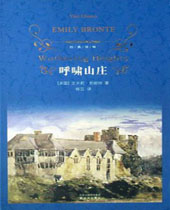歇马山庄-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腮时,牙在嘴里有力地咬了一下月月舌头,那意思好像是在强调快乐的程度,欣喜的程度。月月此时却变得烟雾一样虚无缥渺了。月月几乎是晕倒在买子怀里,月月心里说,天呵,这是怎么了呵?那声音近乎一种哀叫、呻吟。然而,蓦地,月月又真实起来,强大起来,月月被一种强大的东西支撑着突然挣脱出买子怀抱。她低着头,但她能觉察出对方那迷茫而疑惑的寻视。她说晚上我来看你烧砖,好吗?买子俯视着月月在柔软中挣扎的发丝,颤巍地嗯了一声,说我等你,就放开月月,像放飞扑进窗中的蝴蝶似的帮月月扶起车子,看着月月依依地离去。
留下一句相约的话月月其实毫无准备。一整天月月都在为这句话欣喜着,激动着,甜蜜着。临近傍晚,一家人都回到院子里,月月才为这句话感到恐惧。然而,这一点儿都不影响她为这句话负责,为自己负责。那样一个发自骨髓里的呼唤、推动,使月月无法抗拒。为了不让小青缠她夜里散步,月月在太阳还没落山时就谎称为张小敏补课走出家门,并骑着自行车。月月拐进沟谷小道时,西下的日光为她的后背染了一层绚丽的、迷人的色彩。买子想不到月月会真来并来得这么早,他欣喜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将月月径直引进西屋,简陋的、只有一张炕席一床被褥的大炕向月月展示着无限诱惑。月月羞涩地低下头,说我先过去看看老人。买子会意地努着嘴,堵着那个言不由衷的发音的渠道,买子疯狂地吸吮着那里的汁液那里的朝露,小眼睛细眯着看着月月,月月确实同庆珠不同,月月欢喜时目光也是阴郁的,并总用眼睛说话,那深潭一样的眸子有一种不可试测的秘密,不像庆珠,语言总是走在情绪前边,所有的心事都写在眼里,清澈见底。月月几乎什么都没跟自己说就大胆地闯进家门。
买子尽管并不知道月月对他的感情有多深,她的行为却让他懂得他们将要发生的一切已经在劫难逃。其实这一天里买子的心情极不平静,他一方面一幕一幕闪现着与月月接触的过程,月月的家庭、丈夫,一些混乱的缠绕搞得买子大脑疲惫不堪;一方面又一刻一刻地等待夜晚时刻的降临,一个清晰的盼望搞得买子神魂颠倒。买子一早在沟谷边看到含情脉脉的月月时,心底里的兴奋多半来自于对自己的肯定,月月的友爱像一面镜子,让他照见自己。而这一天里的下半晌,买子便由兴奋转为焦急的等待,买子在焦急地等待着并怀疑那一刻是否会来时,自己是否优秀是否有魅力已经不再存留心中,从村部回家以后,买子已经没有理智,完全被一种感情占有,月月在慌乱中走进他的家门的刹那,买子血管里奔涌的是做男人的幸福与骄傲。
买子迷醉地看着月月,粗粗的喘息声仿佛胡同口的西北风,呼哧呼哧。一会儿,就把月月搂进怀里,说,你是一个多好的女子。买子本是为自己的骄傲寻找着言辞,却不经意地刺疼了月月的心窝—;—;这么好的女人却要遭遇不幸……因为心疼,那不可抗拒的诱惑突然被撕扯了一下,像一张润在水中的纸,似有些面目全非。少许,当买子把月月抱上炕沿,那面目全非的诱惑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月月从炕沿上委下来,两手狠抓着买子的下颏、脖颈、肩膀,月月在抓紧它们时心底里回荡着烫心炙肺的语言:爱你,爱你呵买子—;—;月月一双匀细的手指越过买子肩膀向胸前走来时,狠抓变成了轻抚,轻轻的抚摸。月月的手指在买子健壮的肌肉块上抚摸,月月对男人的身体从来不感兴趣,即使当初与国军相爱,肌体接受了国军那富有节律的疯狂,她也从来没有主动爱抚过国军的身体。现在不同了,现在她那么想将买子全身亲吻个遍,那么想将他所有的存在都变成自己的,自己的一部分。这种抚摸的快乐,这种令人心疼的抚摸的快乐,简直令月月不能想象。顺着买子下移的手指,买子脱掉上衣,又结开裤带,裤带带动裤子咚一声落到脚下。月月的手却在买子腰间停下来,月月沉吟地唤一声买子,就坐在炕沿任买子摆布。
焦灼的渴念轻而易举就打破了残余在心灵边缘那点理念,事实上那理念在这间草房屋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他们年轻的身体一旦全方位融在一起,就在炕上来回滚开。火本点燃在他们心里,燃烧在他们相互挤压的身体里、他们却仿佛火烧在了他们裸露在外的背上、臂上、腿上,因为他们在床上滚动的样子像要扑掉身后的火。买子对男女之事毫无经验,月月的牵引和配合却使他畅通直入勇往直前。买子平生第一次体验那种快乐,那种让人有些绝望的感觉,买子一次次颠簸着身躯,一次次在迅猛的冲撞中险些流离失所。动时买子犹如下降的直升机,螺旋桨不住地转动,身子不住地倾斜颤抖;不动时便像一只孵卵的母鸡,在燥热的气体中用手和嘴频频地啄着蛋皮一样光洁的乳峰。月月顺从着颠簸,冲撞时,感受了一千次一万次的毁灭。月月呻吟着,为这满目焦土满身洪水,为这一切的不复存在一切的毁灭。然而,当那最后的颠沛和冲撞终于浇铸成一个结局、一个美丽的瞬间,月月感到一个女人,一个完整的女人,在毁灭中诞生。
月月哭了,月月的泪水珠子似的一串一串。他们并躺着,买子用嘴亲吻着月月眼角的泪水,亲吻着她的额,她的鼻,她的脖子和胸脯。买子说,你给了我骄傲,月月老师。
月月抚着买子肩膀,边哭边说,不,不是这样。
买子说月月老师,你不是可怜我吧?
听到这话,月月泪水流得更欢,月月说,我爱你,爱你,你懂吗?
买子点头,再一次俯身拥住月月,你怎么能瞧得起我?歇马山庄谁想你我都不敢想你。
月月用手梳着买子头发,连连说不,不,这么说对你不公平,你和别人很不一样。
是的。没有根底,没有家教,没有……
不待买子说完,月月打断他,不,不是,你不能这么说,你的根底不在祖威里,在你自己的血管里。
此时此刻,月月最想听到的话和最想说的话不是这个,而是我爱你。可是她的柔情,并没得到买子的准确领悟,买子的话表明了买子并不知道她对他的爱有多深,这令她有些难过。月月突然有些难过,放下手,在黑下来的幽暗中静静地看着买子,不再说话。见月月脸和眼睛一同忧郁下来,买子有些惶悚,他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错在哪里。买子把手放在月月圆润的肩膀上,摇晃着月月,说怎么了?有什么不开心?你,你觉得我不值得是吗?月月不说话,眼角的泪再一次涌出,月月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委屈,为他,为她。她轻微侧了侧身,静静地看着买子,看着买子身后的墙壁。屋内已经彻底黑下来,视野浑呼呼一片,突然,在这混浊的影像里,月月感到窗玻璃上好像有个物体在闪动。月月兀地爬起,寻找衣服,月月说我要走啦。买子抱住月月肩膀,说还会来吗?月月先是点头,而后摇头。月月迅速地穿上衣服,好像大梦初醒似的,慌忙地亲了亲买子的额,走出西屋。当月月走出西屋,走进黑黝黝的院子,月月初始知道,她在这一天里做了一件对自己是多么重大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她才知道她所做的事情是多么可怕。刚才窗玻璃上那一团闪动,其实不是什么真实的物体,是被遗忘了的现实在向她发出警告。
因为现实的提示,月月执意不让买子送她,月月顾不得分手的痛疼,她头也不回带着小跑推车上坡下坡,在切入屯街街头的岔路口,月月险些被上坎绊倒、那并不很高的坎基挡了车子后轮把她使劲往后拽了一下,当月月终于在仓皇的心跳中走上屯街,月月脑袋嗡一声涨大,浑身毛孔往外起粟—;—;就在她近前路旁,站着一个幽灵一样的小兽—;—;火花。
小青和买子
小青终于以崭新的面目在歇马山庄村部卫生所上班。尽管许过诺言绝不在歇马山庄长治久安,上班的日子她还是神采奕奕神清气爽。她身穿红花短袖衫削着短发,乳房挺得高高的,她的与山庄极不和谐的装扮使许多人不敢看她又想多看两眼。最初引她打开卫生所屋门的是村委刘海,刘海看见小青眼睛里闪出一团阴霾的雾气。潘秀英到来之后,买子才从村部过来。这是小青和买子的第一次见面,小青对替换爸爸的村长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没有对话没有握手只是相对一笑。买子要潘秀英领小青下屯走走,熟悉熟悉情况。
跟潘秀英走完歇马山庄之后,小青在卫生所里迎来了第一个漫长而孤寂的日子。前来拿药扎针的人寥寥无几。山庄女人男人不在家的时候极少有病,即使有病也要等到她们的男人回来再治。
一整上午,卫生所的屋门只响了一下,下河口厚明远女人领十四岁的儿子前来看病。那个干瘦的男孩一张小脸像泡了黄胆水,小青一见,扒扒眼睛就断定是黄胆性肝炎,叫他赶紧到乡卫生院治病。小青目送一对母子灰秃秃的背影消失在小学校房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滋味再一次告诉她,绝不要在乡下呆得久长。
送走一对母子,卫生所的门就再也没有响过。小青对打发乡村日子有着充分的准备,比如绝不与家庭妇女同流合污,绝不在乡村找对象结婚,可是当那一片片从山脉里、野地里延伸过来的漫长、孤寂的时光袭扰而来,小青心底里便不时涌出烦躁、烦闷。这烦躁和烦闷是不期而至的,是她在县城里用想象的触须抓摸不到的。漫长的寂寥的现实是那梦醒之后的长夜,小青不知如何打发这与乡野连着的,却又是独立成章的空间的长夜。她常常推开屋门,站在门口,看村部几个村干部煞有介事地出来进去,看那些锤打农具的不刷牙的铁匠龇着黄牙在那里开怀大笑。
这是小青心底烦闷却又无比空洞的日子,买子因为一连几天没有见到月月心情开始烦躁,他在村委砖场筹建方案结束时,趁大家走出村部的当口笑着来到小青跟前。小青看到买子就像看到天边一朵云彩,没有一丝反应。买子说林小青怎么样?
小青斜睨着这个黑黑的男人,什么怎么样?
买子说听庆珠讲过你。买子的话不连贯,听出并不是非要小青回答,只是一个见面礼,像城里人的握手。买子瞥一眼小青,轰隆隆开门进屋,说,这活其实干好不容易。
小青说你以为你容易,你更不容易。买子的黑龙江口音给小青带来了意外的兴致,早在县里上学时就有这种感觉,普通话像一件漂亮的外衣,能够无形中给人带来一种档次。买子的普通话刺激了小青的说话欲,小青说你可是出尽了风头。
买子说,那多亏了你爸,还有翁老师。
小青噗哧一声笑了,假话。你这种人不会感谢别人。
买子说,我是什么人?
小青说自以为是,苦大仇深。
买子说越苦大仇深越能记住别人的好处。
小青说,那是记给别人看的,其实心底里觉得全世界都欠你的。
买子愣住,好像在说你这女孩目光真毒。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青说,从我爸那里,他就是那种人。
买子不说话,一边想这女孩挺有意思,一边去寻走合了道的话题,停一会儿,买子说,翁老师是哪一种人?
小青瞅一眼买子,不假思索,和你恰恰相反,出身优越,却偏觉得自己欠所有人。
你了解她?买子问得很投入。
小青说当然,她是我嫂子。
买子陷入沉思,黑脸上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
见买子在嫂子身上停下话题,似有所悟,说你也恋过我嫂子。
买子摇摇头,脸上的红晕渗得更透。他站起来,往外走着,说林小青,谢谢你对我的评价,从来没有人这么评价我,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子。
买子走后,小青的烦闷和空洞里有了一丝恬淡的情味。这种对话小青在歇马山庄很少有过,它好像与乡村土地不很谐调,有着金属样的光泽,使小青有机会在寂寞中领略一分刺激。
后来小青知道,买子找自己的整个一席对话都是为了她的嫂子;后来小青知道,就是这样孤寂中的一席对话,使她后来走入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买子和月月
离家一周的国军背着一旅行袋中草药走进家门时,一家人争先恐后向他表示欢喜,母亲一边锅上锅下忙着,一边说什么会开这么长时间,天天望,都快把人急死了。平素在家很少说话的小青,嗷一声跑出,夺过国军背包说,怎么像个偷地雷的?月月压一盆水端到院里石台上,让国军洗脸。其实国军刚一走进门口,月月就发现他瘦了一圈,腰围明显变细,下颏由方变失,上面刚割完韭菜似的长满胡茬。月月什么也没说,月月没说一方面为了瞒过婆母;一方面为了掩饰心中的凄苦,她有感觉,一旦由自己说出国军的消瘦,她会流出眼泪。月月沉默不久,就开始说国军的瘦,说你准是不舍花钱吃饭就瘦成这样,看裤带都松了。月月眼里真的有泪。月月说完话就去帮国军搓背,全不顾公公、婆婆、小青和火花的眼目。月月在看到火花那双小眼睛时,手上的动作更柔更欢,手在盆与背之间舞动,溅到盆外满院水花。
林治帮一个人在屋里默看电视,他已从一家人厨房里的忙乱中感受到儿子的回来,但他一直没动。退下位来,在村人面前的确掉了村干部的威风、威严,在家里边做父亲的长辈人的威严永不能失却。国军洗完身子,走进屋来,说爸,我回来了,算是礼节性的报到。林治帮没有言声。见父亲无话,国军站一会儿返身要走,林治帮开口说话,月月对你到底怎么样?国军一激灵,心底翻了个劲儿,以为父亲知道自己有病,他支吾说,挺好呵。你瘦了,国军不吱声,林治帮说,你爸退下来,她可不能借由当你使威风,咱林家人没根底可不能受欺。国军终于明白父亲的意思,说月月不是那种人就转身离屋。
因为一周的奔波愈加平添了颓丧的心绪,也因为父亲那句对儿子备加关心的忠告,国军心情一直不畅,月月几次用手抚弄他的身体都被他轻轻推下。国军不想和月月亲密是不愿把心情搞得更糟,而月月却以为丈夫对她的变化有所察觉。直到被她再三抚弄国军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