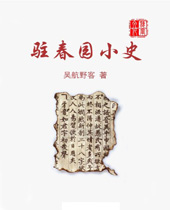克格勃全史-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马尔博罗,布兰特就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政治观点鄙视不已。据马克尼斯说,
“他对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说,他……认为政治话题根本不值得一谈。”
布兰特最感兴趣的艺术史, 作为一门课程, 在六十年代初才在剑桥开设。而
1926年,他考入剑桥时,没有一所大学教授艺术史。至于库尔托尔德学院(布兰特
后来曾任该院院长)则成立于1931年。布兰特考取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并得
到了数学奖学金——这对一个主要天赋都在美学和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成
功。然而数学毕竟不能使他如醉如痴。1927年6 月,即第一学年末,当他以“良好”
的成绩通过数学课程第一部分考试后,即决定转向钻研外语,因为这已同他喜爱的
欧洲大陆艺术和文化相距不远了。1928年,布兰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课
程的第一部分考试,而且法语(自幼他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都得了高分。
1930年,布兰特又以“优秀”功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二部分考试,并拿到了毕
业证。1928年5 月他被选入“传道者”协会,毫无争议,正是协会的同事、著名数
学家阿利斯特·沃斯顿(后来成为海军部的技术军官,同时也是克格勃的间谍)第
一次使布兰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并促使他走上了深入钻研之道。布兰
特的共产主义观点开始逐渐地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许多同他打过交道的人
都很同意年轻历史教师斯蒂文·兰西门对大学生布兰特所做的评价:“看上去他总
是过于自满。但同他打交道却使人感到愉快。”
在诱使布兰特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的过程中,伯吉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
时,即1930年10月,伯吉斯在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上大学,而布兰特也在那里搞
学术种研工作,正是布兰特在两年后介绍伯吉斯进了“传道者”协会。这段时期,
布兰特因对“写生和普桑(法国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一一译注)理论史”研究
卓有成效,而被选进特里尼蒂学院的科学委员会。人们经常看到新任的科学委员会
委员和新来的“传道者”形影不离。
二人亲密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性关系在起作用。布兰特在生理上更狂热地
追逐年幼的伙伴中。而伯吉斯在择偶方面却比较审慎,也许就是他使布兰特摆脱了
心理上的某种束缚, 把他带进了无产者同性恋的圈子, 使他享受到了与那些人的
“肮脏”关系所带来的快感。一但还应该说,那时真正吸引鲍尔和布兰特的主要是
伯吉斯的才智、优雅的谈吐和宽阔的眼界。加龙维·里斯与伯吉斯第一次见面时,
他简直被镇住了。伯吉斯既能够把自己对艺术的执著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学说有机
地联系在一起,又能把这种学说与他到剑桥帮助组织的公共汽车司机罢工有机地结
为一体。1972年,也就是布兰特的公开叛变被揭露的前七年,他曾经公开反对那些
企图贬低伯吉斯在剑桥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出众才能。
“我认为需要提请注意饰是,他不仅是一个我所打过交道的、在智力上最发达
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勉力十足的活生生的人。”
与约翰·科恩福特或詹姆斯·克拉格曼(剑桥大学生中两位最著名的党务活动
积极分子)相比,他的兴趣范围要宽广得多。虽然他倔强而又固执,但这并不妨碍
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并且关于任何话题他都能谈出自己有趣而独到的见解。
为使布兰特确信,他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体现在为共产国
际做出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最终为克格勃效力,体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
中,伯吉斯竭尽全力地对布兰特施加影响。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以用他最喜爱的克洛
德·科克伯恩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你的行为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言语相一致
的时刻到了。‘这就是所谓的‘真情时刻’。”
这个时刻的真正到来是在1933年。那时,伯吉斯受杰里的“与反法西斯‘五人
组’团结起来”的理想所鼓舞,也着手建立了剑桥“五人组”。布兰特在其1933年
(这是他仕途的转折时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1933年秋,剑桥突然之间就传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间我是不会记错的,
那时我由于免修秋天的课程,正好在休假。待一月份(1934年)回来时,我发现几
乎我所有的年轻朋友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剑桥一夜之间似乎换
了一副模样。”
布兰特那时还不能公开谈论剑桥的“巨变”是如何影响他的。伯吉斯那时宣称,
“真情时刻”业已到来,布兰特应将自己全部力量献给反法西斯的共产国标秘密斗
争。1933年秋天的学期末,伯吉斯在罗马与正在休假的布兰特见了面,当时布兰特
借宿在罗马一所英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埃利斯·沃特毫斯那里。沃特毫斯房东并不清
楚布兰特与伯吉斯所从事事业的性质。可是他说,在伯吉斯到来之前,“他们的谈
话从未涉及政治。但这却是伯吉斯唯一想谈的东西。他在政治上是个行家里手。布
兰特也竭力不落后于他”。很可能,就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伯吉
斯把布兰特吸收进了旨在协助共产国际进行反法西斯秘密斗争的“五人组”。
除布兰特之外,伯吉斯“五人组”活动初期的最大收获,就是把特里尼蒂学院
的学生唐纳德·麦克林(十八年之后他被迫逃往莫斯科)争取到手。麦克林的父亲、
唐纳德·麦克林爵士是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人,是长老会的律师和自由党派的政治
家。1932年猝死前,他曾担任拉姆齐·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之职。对
唐纳德爵士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崇高的道德准则,基于此种原则,他把儿子
送到了格列舍马学校,校长埃克斯对每一个新生都要灌输“真诚、坦率、诚实、纯
洁、艰苦以及爱劳动”的思想。为了保持纯洁、防止孩子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早期
性试验,每个男孩子的裤袋都被缝上。格列合马学校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
诗人的奥登,1934年写道:“我反法西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中曾经推
行这种法西斯制度。”
麦克林对这些制度的反应倒没那么强烈。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他恨(或是不太
喜欢)自己的父亲或那所他学习过的学校。他赞成学校搞橄揽球赛,因为在竞赛中
获胜就可获得进入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的权力,当然这不如在大学里获得学位那么声
名显赫。中学毕业时,他是一个以思想纯洁而获得好名声的学生。但与菲尔比和伯
吉斯不同的是,他早在中学就初次认真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他的校友,后来
成为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和党史学家的诺尔曼一约翰·克拉格曼说,他在格
列合马学校入党是为了气恼那些领导。在中学时代,麦克林就过着双重生活,他向
父亲隐瞒了他已不再信仰上帝的真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越来越左。如果1931
年他没有入党的话(也就是他成为特里尼蒂学院学生前),那么可能就是在大学一
年级时他入了党。 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的, 是外语专家、他的朋友克鲁格斯。而
“猛兽”伯吉斯毫无例外地又成了两性同体的麦克林的第一个情人。把麦克林从性
问题中解脱出来之后,伯吉斯又企图在其他方面占有他。后来伯吉斯曾讥笑麦克林
说,“他那硕大的,虚胖的,白白的,象鲸鱼一样的身体”能够给他带来某种快感。
而事实上,麦克林高大魁梧、强壮有力,并与伯吉斯一样十分英俊,令同性、异性
都十分迷恋。
伯吉斯同时还为麦克林在政治问题上指点迷津。很可能就是在、1933年秋那个
学期中,即伯吉斯去罗马会见布兰特前不久,他成功地将麦克林吸引进了自己那个
即将投入反对国际法西斯秘密战中的秘密小组。1933年,麦克林对剑桥大学一家主
要的学生刊物进行了采访(这家刊物曾在一篇文章中好奇地暗示过麦克林在性和政
治中的双重生活方式)。采访一开始,麦克林就首先声明,他过的不是双重生活,
而是三重生活,然后他就不无幽默地依次描述起这三个角色来。他刚开始扮演一个
爱美的同性恋者:“我刚穿上绒布短裤,你又打来电话……下次约会你一定要来我
这儿,到时会有奇花的海洋。所有人的穿着打扮似在神话中一样……”;然后他又
扮演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汉:“刚要吃煎牛排,就听见你在大叫。大家欢聚一堂,
还有非常美丽的服务小姐暗送秋波”;最后扮演的是一名深深迷恋于马克思主义的
大学生:“我现在很忙,我想弄清米德尔顿是否是个唯物论者或者仅仅是个辩证者
……关键在此。每个人都应工作。所以我在这里。”
和德国的“五人组”一样。伯吉斯的“五人组”并没有固定成员,而且在人数
上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可能阿利斯特·沃斯顿和詹姆斯·克拉格曼就是首届成员中
的人物。但克格勃并未将此二人与伯吉斯、菲尔比、布兰特、麦克林和那个1935年
被招募的“第五人”等量齐观。
1934年春,伯吉斯更换了研究课题,他将“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换为“印
度士兵的起义”。但伯吉斯在这件工作上已缺乏足够的创作冲动,原因是这种冲动
越来越被反法西斯的秘密战吞噬了。5 月份,即菲尔比返回伦敦来到剑桥后不久,
伯吉斯就搞到了有关菲尔比在维也纳与共产国际地下工作者联络中冒险经历的第一
手情报。当时,伯吉斯对菲尔比大加赞赏,用加龙维·里斯的话说,他的评价之高
甚至使人难以置信这些评价所依据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有可能也是在5 月、在一家
咖啡馆里,伯吉斯与杰依奇见了面,同菲尔比一样,他只知道对方叫“奥托”。伯
吉斯写信给菲尔比,汇报了自己在招募工作中的成绩。菲尔比马上回信并向他表示
祝贺。1934年夏,经杰依奇同意之后,伯吉斯为了护送牛津大学共产党员德里克·
布莱克(后来死于二战)去了趟德国和莫斯科。德国之行正巧碰上了富有戏剧性的
事件的发生。他们还未来得及同年轻的德共党员商量逃往莫斯科的对策,就听到了
枪炮声。这是在1934年6 月30日的“长刀之夜”,这一夜,希特勒与纳粹党中的对
手正在算总帐。
据伯吉斯的一名亲信随员说,伯吉斯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
部主任皮亚特尼茨基,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见过面。此行使他更加坚信他是在为
组织反法西斯秘密战的共产国际工作。但他刚一回国,杰依奇就使他相信,为了进
行秘密战,他应和菲尔比一样从事地下工作,要中断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络。伯
吉斯二话没说就照办了。但就他的朋友们看,他却表现得有些怪诞、有些出格:他
把斯大林归人法西斯独裁者的行列,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未来的预兆”。他甚至在
“传道者”的秘密会上也隐瞒自己的政治信念:
“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有现成的引文、可笑的趣闻、不合时宜的比较或带
污辱性的随机应答。如果协会讨论什么政治问题,他就喜欢用其内容令人费解的隐
喻发言。假若直接让他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就瞪大那双神采飞扬的蓝眼睛、用他那
使人无法反击的满含笑意的目光看一眼提问的人,然后开始讲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
东西。”
杰依奇不仅为伯吉斯规定了几条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而且还要伯吉斯放弃其初期计划中仿照德国“五人组”的样子,建立共产国际支部
的打算。与剑桥每位新招募的学生进行单线联系工作方式的,首先是杰依奇,然后
是马雷。但伯吉斯很瞧不起这种死板的工作方式。他把间谍工作看作是与朋友们一
起干的社会工作。正如菲尔比后来所承认的,正是伯吉斯坚持要在我们所有人中保
持联系,也正是由于这种执拗,几乎导致了菲尔比在1951年的覆败。
按杰依奇的提示,麦克林与伯吉斯同时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1934年6 月,
麦克林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那时,他的愿望是要么去苏联教英语,要么留在
剑桥着手哲学博士论文工作。他把博士论文题定为“吉恩·凯尔文活动的马克思主
义分析与资产阶级的兴起”。但他这年夏天并没有着手这项工作,而是对母亲说,
他想试试能否到外交部任职。麦克林夫人很高兴,但却想知道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是
否会妨碍他的打算。”你可能以为我像风信标一样打转转、绕圈子,——他回答—
—实际上,我不久前就不再干那些事了”。第二年几乎整整一年,他都泡在离不列
颠博物馆不远的课外老师那里,准备1935年8 月的入外交部考试。成绩自然又是十
分优异。后来麦克林讲述了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被问及在剑桥所表现出“共产主义
思想”时的情景:
“突然给我提这么个问题;是说谎呢还是放肆地兜圈子?我决定兜圈子。‘是
的、——我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并且我还不彻底放弃这种思想’。我
想我的诚实会令他们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对我直点头,然后是彼此笑了笑。最后考
试委员会主席说:“谢谢,就到这里,麦克林先生。”
1935年10月,麦克林第一次踏入了外交部的大门,成了皇室外交机构的新成员。
从那时起,他也就成为“五杰”中打人政权核心的第一位人物。
伯吉斯为获取国家机密,耗费了大量时间。1934年末,他的研究工作停止下来,
他决定离开特里尼蒂学院。离开剑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他大学同学的母亲当财
政顾问。这位朋友就是“传道者”协会的战友、后来成为议员的维克多·罗特希尔
德。伯吉斯与杰依奇经常在咖啡馆会面,两人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在预计的较长
一